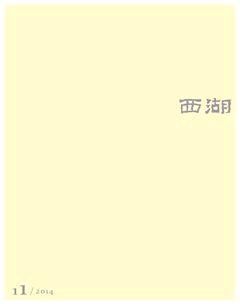無(wú)處逃離(創(chuàng)作談)
池上
大四那年,我迷上了十字路口的紅燈。紅燈一亮,人們就不得不停下來(lái),等待似乎成了唯一可做的事情。我常常站在等待的人群中,看橫向的那條馬路。馬路上,行人來(lái)去匆匆,他們的每一步都在訴說(shuō)著他們很忙,整座城市都很忙。當(dāng)然,在他們的臉上,我看不到大喜或是大悲,因?yàn)闊o(wú)論是喜是悲都是需要時(shí)間以及情感的積淀的,因此,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張張符號(hào)化的木然的表情。
我喜歡這種表情。它使得每個(gè)人看上去都驚人的雷同,但事實(shí)上,假若可以剝開(kāi)它,直擊其背后,我們便可以曉得這是個(gè)多么虛假的表象。它更像是一種留白,你可以盡情想象隱匿于每張表情下的不同心境、不同經(jīng)歷,乃至不同的人生……然后,綠燈亮起,想象結(jié)束,我從那個(gè)世界跳轉(zhuǎn)回來(lái),繼續(xù)前行。
也有例外的時(shí)候。譬如,對(duì)面的那家店鋪,一面長(zhǎng)長(zhǎng)、寬寬的玻璃櫥窗內(nèi),擺放著各式精致的展示品。這個(gè)時(shí)候,我總是會(huì)停下來(lái),看櫥窗里的展示品,也看櫥窗里的自己。櫥窗里的自己,一樣的漠然、麻木,一樣的不帶任何色彩。但是,同先前的想象不同,我是清楚鏡中人的喜怒哀樂(lè)的,特別是煩惱,那么多的煩惱,它們?nèi)缬半S形,在我的周?chē)h來(lái)蕩去。
煩惱之一,便是工作。那時(shí)候,我剛大學(xué)畢業(yè),工作還沒(méi)有著落。所學(xué)的師范專(zhuān)業(yè)是僧多粥少,且原本只需要學(xué)校直接聘用的程序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類(lèi)似于公務(wù)員考試的那種方式。實(shí)際上,我更擔(dān)心的是今后的生活狀態(tài),我不像有些人那樣能很快便融入一種新的氛圍,我還是個(gè)孩子,還沒(méi)有做好成為社會(huì)人的準(zhǔn)備。但我知道,這些都不足以成為理由,沒(méi)有人會(huì)因?yàn)槲业目謶侄陨岳斫馕遥乙膊豢赡芤虼硕惠呑痈C在學(xué)校或者家里,徹底和社會(huì)脫節(jié)。可是,我畢竟還是恐慌的,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下午,我就對(duì)著那面玻璃櫥窗,一遍遍地問(wèn)自己的影子。櫥窗內(nèi)的影子冷冷地看著我,沒(méi)有回答。
不久,我的生活發(fā)生了變故,我的姑父去世了。姑父是個(gè)體育老師,平常打球、游泳樣樣在行,身體自然好得沒(méi)話說(shuō)。可是,諷刺的是,姑父卻死于心肌梗塞。他在一家理發(fā)店里理發(fā),從發(fā)病到離世僅僅只用了幾分鐘。姑父死后,成了一個(gè)樣本,被放在報(bào)紙上的一個(gè)角落里,標(biāo)題上寫(xiě)著《“秋老虎“來(lái)勢(shì)洶洶,謹(jǐn)防心臟病來(lái)襲》。
姑父的死,對(duì)于我而言,打擊太大。姑父還那么年輕,況且他人又那么好,不論是誰(shuí),只要是他能幫上忙的,他從來(lái)都是那么熱心。我們?cè)跉泝x館里同他告別,看他被推進(jìn)爐子,像任何沒(méi)有生命的東西一樣在里頭燒得呼呼作響。等出來(lái)時(shí),他已經(jīng)成為了幾段骨頭。悲傷讓我只覺(jué)得心很痛,眼淚卻意外地只是一小行,很有規(guī)律地流下來(lái)。然后,我聽(tīng)到了旁邊的哭聲,哭聲是那么悲戚,那么哀痛,那是我的姐姐,也是姑父的獨(dú)生女兒。她本來(lái)就很瘦弱,我很懷疑她能否支撐到把姑父送上山。
從殯儀館回來(lái),我看開(kāi)了許多。我突然發(fā)覺(jué),這世界上很多東西真的是可以看淡的,也必須看淡。死亡,將現(xiàn)實(shí)血淋淋地撕開(kāi)來(lái),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我們離死亡很近,只不過(guò)在一線之間。我開(kāi)始不在意那些細(xì)小的波瀾,甚至連先前一直困擾我的問(wèn)題也變得無(wú)足輕重起來(lái)。
日子卻還在繼續(xù)下去。姑父死后的第六個(gè)秋天,杭城的氣溫依舊逼人。有一天,我從家里的窗戶(hù)上往下望,看到梧桐樹(shù)葉雖然仍舊發(fā)綠,但總歸有幾片在慢慢轉(zhuǎn)黃了。這種黃是那么細(xì)微,細(xì)微得讓人不容易察覺(jué)。我猛然想起了姑父,姑父也是在這樣的季節(jié)里,像一片梧桐樹(shù)葉一樣,來(lái)不及說(shuō)聲再見(jiàn),就掉落了下來(lái)。你以為他還是綠色的,等撿起來(lái),才驚覺(jué)他早已泛黃了。我還想起了姑父死后的那段日子,我試圖改變自己,把一切都看淡、看輕。但是這幾年里,我又在做些什么呢?是的,這些年來(lái),我順利地通過(guò)了學(xué)校的考試,有了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可工作并沒(méi)有讓我的煩惱減少多少,我依舊很煩:為學(xué)生,為教學(xué),為科研,還有數(shù)不清的各級(jí)各類(lèi)比賽……
生活就像是個(gè)“困”字,現(xiàn)實(shí)如同四面高墻牢牢地將我擋住,讓我無(wú)處逃離。有時(shí),我甚至想,不如找處山林隱居了吧。但也只是想想,現(xiàn)代社會(huì),連珠穆朗瑪峰都有移動(dòng)信號(hào),哪里還有一處清靜的地兒呢?我們的生活早已被微信、微博、QQ圍堵了,比較贊同的還是少林寺的一個(gè)和尚同我說(shuō)的一番話。和尚告訴我:心若靜了,哪里都是靜的。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大隱隱于市”的另一種表達(dá),只是,身處在這樣的一個(gè)社會(huì)里,我很難確定是否有這樣的一個(gè)人。我所能確定的是,大多數(shù)的人,像你,像我,大概不過(guò)是另一個(gè)阮依琴,想走出去,但終究是逃脫不了現(xiàn)世的這個(gè)“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