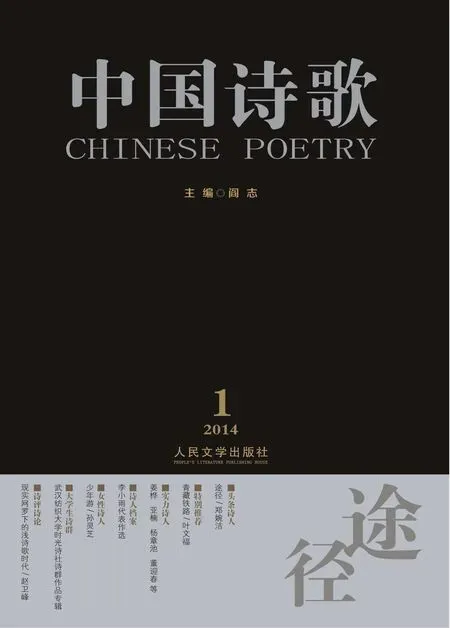現實網羅下的淺詩歌時代
2014-11-17 07:58:51趙衛峰
中國詩歌
2014年1期
關鍵詞:現實
趙衛峰
親密的接觸,反映了詩歌寫作在對現實的中庸式和解、自嘲自秀自虐的誤解、極端化的美化與惡化甚至自我矮化的曲解中,將現實環境、日常的自然生活在以為然的默認中推到了中心位置。
1
當代詩歌對日常生活的擁抱和對社會環境變化的及時表達一度拓展了詩路,隨著這種如膠似漆關系之遞進,世紀之交以來的詩歌卻未出奇出新,它從緊張到松懈后安然進入到一個普遍的擱淺——輕淺狀態。其淺,卻又在多方合力普及的過程中、在“貼近現實、日常審美、表達多元與多樣以及文化發展”等幾乎不容置疑的普識前提下顯得眾望所歸、堂而皇之、合情合理和理所當然。
階段視之,表面的繁榮似乎顯而易見——
廣泛普及。詩陣地、作者與讀者及創作數量同步劇增,刊物擴容、選本、比賽和獎、民刊盛行、自主出版物層出不窮,網絡平臺難以計數,詩活動日有發生……顯然,今天之“普及”受傳播的牽引度極大,與昔日民歌運動、朦朧詩潮相較更自動和互動。大眾在普惠的傳播的引力下持續寫作興趣與信心,遠離或不在意往昔之主流關注,因為“自己”及“現實”的林林總總本身就夠眼花繚亂了。若將“現實”喻為水庫,如果突然斷水,估計太多的詩人會一下子茫茫然不知下步該往哪里。
百花綻放。與往昔相比,作品數量大躍進,詩作為精神的自我表達與平衡工具的實在與實用性讓詩歌群眾有所感覺,并在快餐式的隨意消遣中身體力行,讓人在飽滿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中國新聞周刊(2024年18期)2024-06-07 22:40:49
文苑(2020年11期)2021-01-04 01:53:20
人大建設(2019年12期)2019-05-21 02:55:32
語文世界(初中版)(2016年6期)2016-06-29 22:44:39
現代計算機(2016年12期)2016-02-28 18:35:29
發明與創新(2015年25期)2015-02-27 10:39:23
中國衛生(2014年12期)2014-11-12 13:12:38
杭州科技(2014年4期)2014-02-27 15:26:58
新東方英語(2014年1期)2014-01-07 20:01:29
雕塑(1999年2期)1999-06-28 05: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