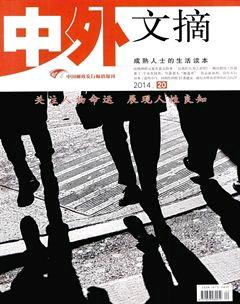哪國教師工作最累?
高佩菪
6月25日,經合組織(OECD)公布了對34個國家、地區教師工作時長的調查結果,發現很多國家的教師都面臨著工作超時、過度勞累的問題。不過,各國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不盡相同。
英國:“熊孩子”催生“幽靈教師”
在英國教師與講師協會(ATL)報告的描述中,“幽靈教師”是一群臉色蒼白的生物,他們每天被困在學校長達10小時,疲倦不堪地面對趴在桌上打瞌睡的學生喋喋不休。
英國《衛報》稱,如今的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形形色色的強化班、補習班,當然,還有永遠對付不完的作業和考試。據0ECD統計,英國教師每周工作46小時,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多9小時。其中,只有20小時是在教室里度過,其余都用來從事非教學活動,盡管教學助理和行政人員人數眾多。“事實顯而易見。英國教師工作時間比其他國家更長。還被政府要求付出更多,雖然政府從4年前就承諾減少官僚主義。”全國校長協會的秘書長羅素·霍比告訴英國《獨立報》。
盡管英國教師人均年收入3.46萬英鎊(約合人民幣40萬元),相對價值超過美國、法國、意大利、瑞典和澳大利亞等國,仍有74%的人認為他們“與其他專業人士相比收入過低”。只有35%的英國教師認為他們的工作被社會重視。受政府委托分析OECD調查結果的倫敦大學教育學院稱,英國教師對工作的滿意度,其實已高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31%。在瑞典、法國和西班牙,這一比例已下降至10%以下。據《衛報》分析,英國是最累的歐洲國家之一,超時工作越來越成為文化的一部分。
英國《每日電訊》報則認為,將教師逼成“幽靈”的,除了無處不在的加班文化,還有在課堂上搗亂的“熊孩子”。該報稱,在英國,學生濫用毒品、酒精,毀壞公物,盜竊,毆打同學等都不太可能面臨嚴厲的懲戒,如果教師阻止學生破壞教室或搜查其違禁物品,甚至可能面臨起訴。40%的英國課堂氛圍相當糟糕,教師得隨時做好準備,應對學生的口頭攻擊和惡作劇。在這樣的巨大壓力下,英國教師患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很高。OECD的報告還發現,很多教師得忍受學生嘈雜的“背景音”,其中21%不得不在課堂上花相當長時間等學生安靜下來,因學生打斷授課,浪費了大段時間。
英國全國教師聯合會秘書長克里斯汀·布勞爾告訴《每日電訊》報,OECD的調查結果十分明確,“教師工作難以負載且不可持續,教師認為社會低估了他們從事的具有挑戰性的工作”,這是一個“人人擔憂的問題”。“我們的孩子理應擁有熱情、精力充沛的老師,政府是時候解決這些緊迫問題了。如果不這么做,毫無疑問,教師會進一步短缺,這顯然不利于教育。”布勞爾說。
日本:大量瑣事耽誤教學時間
每天早上6點,京都教師考特尼·科珀諾爾就看到他的同事準時抵達學校,晚上9點前絕不離開,有時甚至會通宵工作。除了周末和上下班通勤時間,他們每周工作60~65小時。
一開始,科珀諾爾懷疑同事只是在他面前假裝好好表現,但很快他就意識到,日本人“臭名昭著的工作習慣”在教育行業也不例外。據日本Wide Island View網站報道,無償加班、沒有周末在日本司空見慣,日本職員面對同事的時間遠比家人多。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日本3700名中學教師、校長接受了OECD的調查,他們每周平均工作53.9小時,是OECD國家平均水平的1.4倍。
其中,日本教師每周花在課上的時間只有17.7小時,比平均水平19.3小時還要低。不過,他們對學生進行課外輔導的時間為7.7小時,是平均數的3倍,花在文案工作上的時間也是平均水平的兩倍。
日本特殊的教育體制導致了這一結果。為了滿足董事會與學校之間“信息共享”的需求,教師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撰寫每周課程計劃和學生成績數據(必須提交給校長審查),完成對學校生活各個方面的調查評估,向董事會匯報學校活動的情況。除教學外,指導俱樂部活動、參加示范課程、開會、準備學校活動等日常事務,也占據了日本教師的大量時間。
此外,許多學校教師崗位被削減,或教師退休后沒有新進人員補充,也讓學校工作人員數量捉襟見肘。科珀諾爾工作的學校中,一年級的英語和音樂教師便由一人兼職。在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中,為保住珍貴的工作機會,許多教師認為,自己應該比同事工作時間更長,以保持“競爭力”。
據OECD調查,日本教師對于課堂組織能力和教學技能的自我評價,也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超過80%的受訪者表示,由于工作安排得太密集,很難有時間接受培訓,培養教學技能和處理其他事項的能力;無法通過教學促進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文部科學省官員向NHK承認,由于承擔的指責過于廣泛,日本教師很難專注于教學和專業能力的發展,聘用更多教師,是改善教育狀況的必要措施。
澳大利亞:降工資加任務,政府“逼走”教師
幾乎每個周末或假日,南新威爾士州教師聯合會的發言人鄧肯·麥克唐納總能在學校停車場看到教師的車,有時,連校長都會工作到深夜。蒙特莫倫教師希瑟·道格拉斯經常從早上8點開始工作,幾個小時得不到休息,有時甚至來不及吃午餐。OECD的研究結果發現,澳大利亞教師每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2.7小時,還要額外花7.4小時完成管理工作。此外,澳大利亞班級平均人數為24.7,比平均數字24更多,明顯高于芬蘭的17.8人。與許多國家相比,澳大利亞的教師更多地生活在農村地區,教學經驗較少。
澳大利亞教師的不滿情緒,要從2012年一項頗受爭議的法案說起。
據澳大利亞《時代報》報道,2012年6月,政府決心改變長期實施以工齡計算教師薪酬的方式,轉而進行績效考核。如果教師能達到教學目標,提升授課水平,就能拿到相當于年薪1.4%~10%的績效薪酬。這樣一來,能拿獎金的人數比例明顯下降。同時,中學教師被要求每周增加l小時的授課時間。在隨后而來的大規模抗議、罷工潮中,許多人離開了教師崗位。新南威爾士州的教師聯合會表示,聯邦政府“毫無疑問”應該對教育改革負責,該舉措對教師和學生都產生了負面影響。
從積極的一面看,OECD的報告發現,澳大利亞的校長有著高度的自主權。但麥克唐納說,這只是政府將擔子丟給了民眾。“他們讓公眾相信有危機,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是給校長雇傭和解雇教師的權力。但這并不是解決方案。”他說,澳大利亞擁有世界一流的公共系統,只是需要更多的資源。
(摘自《青年參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