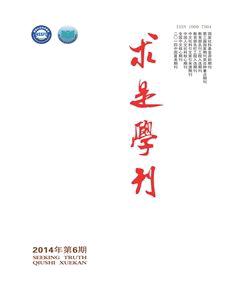美國當前對馬來西亞宗教外交的重點
王琛發
2012年1月,美國公布國家安全新戰略,強調美國雖然面臨預算壓力,但國家還是要努力確保原有軍事超強地位,同時其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以實現“再平衡”。但美國外交從來強調的不是軍事威懾力量,也不僅是軟實力,而是“巧實力”,因此,奧巴馬第二任期內進一步落實“重返亞太”戰略布局至今基本不變,包括它對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實施宗教外交作為具體實踐“巧實力”的重要環節,也肯定不變。而結合著馬來西亞的國情,其重心顯然放在占有馬國人口比例大多數的穆斯林,一邊添加從公共外交制造的軟實力影響,一邊則繼續表示關注馬來西亞宗教間的不平衡,包括馬國伊斯蘭教主流以外的分支所受的對待,并且以“宗教自由年度報告”等形式繼續向馬國政府施壓。其政策的意圖顯然易見,它表現在大使館重視主動與地方宗教領袖直接交流。而奧巴馬至今也許考慮到各方面因素,未對馬國總理2010年提出的、基于伊斯蘭教義中“正確的平衡”的“中庸”外交政策,做出公開積極回應。
一、背景:尋求美國重返亞太的更大發揮
美國爭取東盟以促進“再平衡”亞太地區的外交思路是否維持下去,可以從希拉里·克林頓國務卿卸任前訪問東盟諸國所作的“未來承諾”中了解到。希拉里于2012年11月下旬展開任期內最后一次亞太之行,訪問澳大利亞、新加坡、泰國、緬甸和柬埔寨。她于11月29日在新加坡管理大學演講中提及,21世紀歷史將主要在亞太地區書寫,美國要加強與亞太國家的接觸并塑造這里的未來。[1]而東盟對美國的重要,可以參考繼任國務卿凱利在2013年9月27日總結其參與東盟部長會議之行的看法,他認為東盟諸國一直處在亞太地區架構的中心,而東盟組織也是美國“再平衡”美方資源以及投入亞太地區的戰略中心。他說:“奧巴馬總統特別關注東南亞是由于東盟現在意味著6億人口和2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美國目前在東南亞的投資又比在中國的更多,而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已成為從反對危險資源擴散到反海盜等一切方面的重要合作伙伴。”[2]其大勢背景正如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中所概括的那樣,未來,亞洲不僅會成為世界最大產品和服務輸出地,還將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地,由于亞太一些海域存在島嶼、水域的爭奪,美國認為“這些沖突即使僅限于本地區范圍,也會波及全球經濟”。
從美國國內情勢現實考量,奧巴馬作為第二屆總統,他的任期已經是走向“圓滿”實施政策,大可以不必擔心未來自由選舉前景,拜登副總統也不可能自己為競選下任總統做準備,他們兩人擁有更多自由發揮的空間,可以更激進地推動政策,執行行政。然而,靈活性也可能遇上約束,因為新政府太激進,也可能給未來的新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或其他候任國會議員帶來后遺癥。而且,總統任期一旦進入最后兩年,甚至在黨內,民主黨的國會議員也不太可能人人愿意義無反顧去支持奧巴馬的政策,他們必須考慮自己會否消耗政治資本和選民票源,可以預見,奧巴馬總統可能會如同許多二任總統遭遇過的制衡,在2014年中期以后,更難獲得國會通過爭議性政策;由是,奧巴馬政府要能樹立權威,與其在內政上與各方回旋,倒不如在國際事務上達致更大的成就,以期正面影響其國內事務的貫徹。這時,最有可能的做法是試圖架設其第二任期外交政策議程,一方面將之鎖定在肯定、維護與延續第一任期外交政策的說辭,另一方面則必須要在肯定美國經歷十年對外戰爭以后,能夠讓大眾接受交代的同時形塑未來可持續的議程。這整套外交議程的主干就在于如何以各種步驟進一步實現美國“再平衡”亞太地區的戰略。正如上述所說,美國政府基本責任是維護國家以至所有單獨的美國公民在東盟地區的根本利益,也就是經濟利益;因此,現在的政府更專注于貿易政策和外交架構,這將使得政府進一步加強“巧實力”的綜合應用。
另一方面,也必須注意美國外交思路一直以來深受建構主義自20世紀90年代盛行以來的影響,側重將民族/國家行為視作政治精英的信念(beliefs)、認同感(identity)和社會規范(social norms)的綜合互動,不認為民族/國家行為是實力與實力對比的硬性變量;像亨廷頓晚年越趨保守而強調美國內部的民眾與社會必須重新美國化,以及美國學術界對外重視“認同”或“族群建構”的研究,以至出現“軟實力”或“巧實力”的觀點,都是應和這套思路的盛行而衍生的各種說法。美國正在阿富汗大規模撤軍,又見中東地區“茉莉花革命”的未見其成而先見其亂,都可能推動奧巴馬政府深入檢討過去的反恐戰略,以及催促政府思考如何對待穆斯林占主流的各個國家。但是,美國在尋求保護美國利益的最佳途徑的同時也必須堅持美國價值觀的崇高,甚至要傳播和推動其他國家民眾的美國認同,其原則基本上是不會變的。這樣一來,美國重回亞太進行其“再平衡”,在重視東盟的軸心作用之際,更需關注馬來西亞、印尼、文萊三國,其大部分國民都是穆斯林;泰國、緬甸、老撾、菲律賓、柬埔寨、新加坡也都有相當數量的穆斯林。美國要注重東盟穆斯林與國外穆斯林的聯系,也要注重泰國、緬甸、菲律賓等國出現穆斯林分離主義傾向。尤其注意到文萊宣布在2015年實行伊斯蘭法會否造成鄰國尾隨。另外,美國也需要照顧到國內各基督宗教教派的感受,尤其關注他們海外傳教的自由,以及關注東盟教友如何應付宗教生活。
在東盟國家之間,馬來西亞總理納吉自2010年起,明顯提倡根據伊斯蘭教實行Wasattiya(正確的平衡)外交原則,并于2012年在馬國召開大會倡辦成立“全球中庸運動基金會”,認為應該推動世界上的政府和非政府單位合作,警惕與防范各大信仰被利用來作為提倡極端主義和暴力斗爭的根據,并提出穆斯林可行使民主、公義,關照全人類福利,并以寬和態度對待其他宗教信徒,已經獲得聯合國大會秘書長潘基文、東盟秘書長蘇林,以及英國首相卡梅倫等人表態認同。[3]如此一般的表態,顯然也符合美國對于促進馬國宗教自由的愿望,引起美國關注與設法善意回應。
二、特征:宗教人權理念服從現實需要
美國行使宗教外交,主要有《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可依,這是以國會代表國民決策的權力,為政府評論他國宗教人權以及涉入他國宗教事務賦予法理根據。在美國宗教組織的原始立場,這項法令源于美國基督教福音派游說國會的努力,最終是要通過國家權力保護美國教會海外傳教活動,允許美國依照本國法案,跨海過問他國的宗教人權,同時也保護與美國教會組織擁有共同信仰或利益一致的非美國公民“教友”。但是美國是個提倡宗教自由的國家,所以《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宗旨目標是普遍適應于各種宗教組織,旨在“譴責侵犯宗教自由,推動及協助他國政府促進宗教自由這一基本權利”,法案起草人也說“法案是以行動回應侵犯宗教自由的臺基”[4](P179)。
《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案》的直接影響,是法案賦予美國政府過問他國人權事態的外交憑據,尤其是有利于美國消除國內各教會到世界各國布道的障礙,也有利于美國根據各國的宗教事件判斷美國對待他國的態度,包括根據法案,接受國內外宗教組織投訴,這些記錄出現在當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中,美國也會將一些國家列為“特別關注國家”或者列在“觀察名單”中,以此說明美國對待相關國家的可能變化,包括懲罰政策或進行“人道干預”。
在美國《馬來西亞2012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中,馬來西亞顯然不是一個絕對宗教自由的國家。《報告》第一頁即指出:“有許多相關宗教的社會虐待和歧視的報道,都涉及宗教歸屬的議題、信仰問題或實踐方式,包括童婚的報告據說是伊斯蘭教批準的做法。據此,民間社會組織不斷批評這種做法。”[5](P1)但其接下去的陳述則說:“使館代表繼續保持與政府以至各宗教團體領袖們之間的積極對話,包括那些沒有受到政府正式承認的宗教組織。國家大使也到全國各地參訪與會見各宗教領袖,強調宗教自由的重要,以及強調宗教互相之間寬容也很是重要。”[5](P1)
《報告》談到“未受到馬國政府正式承認的宗教組織”時說:“政府對宗教集會采取了若干限制,并拒絕一些團體的注冊。而宗教團體要獲得注冊,才能取得政府撥款或其他利益,而這又掌握在內政部底下的社團注冊官手里。這個部門并沒有固定的政策或透明的規章去決定一個團體可否注冊。不少宗教組織無法注冊以后,解決難題的方式,是根據馬國公司法令注冊。其中例子包括耶和華證人和后期圣徒(摩門教)耶穌基督的教會。根據公司法注冊,賦予些微的宗教自由保護,但排除了政府的資助。”[5](P3)在現實中,這一類的組織,包括上述兩個來自美國的組織,多數都是無法以社團名義集會,于是就采取“公司”舉辦活動,或售賣各種靈療、輔導、宗教性質產品的方式,在馬國延續。
《報告》也提到了,馬國政府對作為屬于大多數國民的主流信仰的伊斯蘭教也有所控制,包括什葉派在內的許多馬國伊斯蘭小教派,都面對暗中監視、逮捕、思想改造等方式。《報告》指出:“官員在聯邦和州各級政府的層次監督伊斯蘭宗教活動,有時影響講道內容,使用清真寺傳達政治信息,限制了公眾的表達,并防止某些阿訇到清真寺講話。”[5](P3)《報告》也說,官方所設立的馬來西亞伊斯蘭促進局(JAKIM)則每周在其網站上發布指南,指導政府雇傭在聯邦直轄區、沙巴砂拉越、馬六甲以及檳城駐清真寺的穆斯林神職人員,在星期五祈禱集會應談論什么議題;2012年3月,JAKIM拋出的主題是,“穆斯林必須明白猶太人是穆斯林的主要敵人”;11月,JAKIM又發布了講道討論指引,要大家議論猶太種族的“卑劣本質,并表示“以色列是悍匪的國家”。[5](P12)
盡管如此,《報告》羅列出上述幾個問題以及其他更多一系列問題,都是僅做事件陳述,并沒有做出正面或負面的判斷式反應,也沒有上升到突出表示“關注”或“譴責”。按《報告》的陳述,在發生其中羅列的一系列事件的同年間,美國在馬來西亞的大使是很積極地造訪各方的。《報告》最后一章《美國政府》的整段文字做出如此陳述:“使館代表在維護宗教自由方面,一向對政府官員和宗教團體領袖,都保持著積極對話的姿態,這也包括那些不是由政府正式承認的宗教團體在內。大使也在同一年內的不同時間會見了各州統治者,都在談話中強調了寬容和相互理解的重要。大使也邀請多個穆斯林非政府組織領導人,主持了和他們討論宗教寬容的圓桌會議。大使并在9月參觀了砂拉越伊斯蘭信息中心,以強調美國支持中心促進相互宗教團體成員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盡心盡力。使館的計劃還包括由美國穆斯林社區領袖和阿訇在馬來西亞各地巡回演講,與智庫組織或宗教與民間社會領袖舉行圓桌會議,推動不同信仰間對話,以及借助電視等媒體訪問以突出宗教寬容。使館亦安排參觀美國伊斯蘭教育,并在齋月期間主辦了數次開齋晚宴。美國政府還資助公民社會團體補助金以及提供非政府機構的交流補助費用,以促進宗教寬容,尊重多元、人權和開放態度。”[5](P14)
從美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的官方網站貼掛的上述《報告》的內容,可以發現,美國對馬國宗教外交的態度,是公開表態美方詳細地關注馬國發生的一切涉及爭議的宗教課題;但是,同樣在美駐馬使館的官方網站和面子書上,出現了系列的穆斯林友好活動,包括節誕賀詞,以及《報告》上所謂的美方使館政策行為,可以發現美國在馬來西亞的外交是立足于現實考量,也真的是很“建構主義”的,側重希望影響政治精英信念(beliefs)、認同感(identity)和社會規范(social norms),從而影響民族/國家行為轉向美國希望見到的演變。
尤其是在2014年7月8日,大使館發出它對馬國其他族群節日的祝賀。馬國各報章發送了使館此前送達的奧巴馬致全球穆斯林賀信。奧巴馬在賀詞中提到,過去四年來,他都在白宮設立開齋宴席接待那些有信仰的美國穆斯林,他們都是些企業家、社會活動家、藝術家。奧巴馬的賀詞提到穆斯林過開齋節的宗教價值時說:“這個月也提醒我們,自由、尊嚴和機會,是全人類的不可否認的權利。我們反思這些普世價值,當著整個中東和北非許多公民繼續爭取這些基本權利,百萬計的難民遠離自己的家園,我們紀念齋月。美國隨時與所有那些正在努力打造所有人類同在一個世界書寫自己未來的人站在一起,實踐他們的信仰自由,免于恐懼的暴力。”[6]解讀其賀信全文,除了是面向穆斯林精英示好,也還是在繼續著2010年5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中以“普世價值”應用為美國持久國家利益以及核心戰略意義兼及戰爭手段的立場。該份文獻說明:“從過去到現在,我們的價值始終是我們最寶貴的國家安全資產”,“我們不懈支持普世價值。這樣的支持,將使得我們和敵人有分別,和敵對的政府有分別,以及有別于其他同樣想要擴大影響的潛在競爭對手”[7]。
重讀美國重視對馬國穆斯林,特別是重視使館直接與其中精英保持籠絡態度,其演變之背景與由來卻是美國一度曾經為了“國際恐怖主義”與馬來西亞有過缺乏民間大肆報道的溝通。21世紀初,美國中央情報聲稱馬來西亞的穆斯林社會一直是促進國際基地網絡成長的避風港,提供基地組織集會、碰頭、轉移地下資金,購置所需裝備,并計劃9·11恐怖襲擊。而且,自1985—1998年受過蘇哈多政權鎮壓的阿卜杜拉·蘇卡(Abdullah Sungkar)和阿布·巴卡爾·巴塞爾(Abu Bakar Basyir)也被發現在馬來西亞找到避風港。當他們在蘇哈托政權垮臺以后回到印尼,他們培植的“伊斯蘭祈禱團”各個分支的觸角已經連接到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和菲律賓,在那里他們招募新軍,并由財政健全的幌子公司長期支持,很多這類幌子公司也都是設立在馬來西亞境內。[8](P427-465)雙方處理穆斯林的“極端主義”課題,一直到2009年達到最明顯的進展,是美國和馬來西亞政府同意在“共同法律互援事項條約”(MLAT)的框架下,相互合作主導馬國國內反恐措施,如采集證據、送達文件、執行搜查和扣押、定位和識別犯罪嫌疑人及犯罪地點,并凍結和沒收相關者財產合作。[9]這是一種得來不易的關系,再加上美國在馬來西亞的當前戰略目標并不單純是“反恐”,首要目標還是尋找“再平衡”的重要立足點。于是美國當前在馬來西亞的政策趨向就顯得更注重“公共外交”理念的發揮——政府對民間、民間對民間,主要還是向不同的穆斯林社群溝通示好。
三、現實:還是在應用巧實力爭取美國利益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再平衡”戰略要取得絕對進展,當然不能只靠宗教外交。事實上,美國與此同時也正在通過其軍隊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軍事演習,加強他和傳統軍事盟國的關系。美方在當前采取的姿勢可能表現為在本區域參與或發起更多軍事訓練和演習,但更能從根本上表達美國軍事能力的前沿,是在那些長期同盟和軍事伙伴關系的國家,如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新加坡和印度,通過各種方式提供更多軍事支持和增強互相操作與多邊合作的機會,最近的表現是在澳大利亞達爾文成立的2500人海軍分遣隊,以及為在新加坡駐扎的部隊增加4艘瀕海戰斗艦。
在增強美國在本區域綜合實力的議程上,美國重視的是一系列涉及各領域合作的溝通與協議。除了希拉里離任前訪問東盟時先訪問澳洲以重申雙邊在東南亞地區的合作力量與合作利益,美國也通過不斷參與亞太地區多邊國際組織,積極參加東盟地區論壇和東亞峰會,以及大力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即TPP),重新塑造其影響力籠罩的亞太地區合作伙伴關系,加強聯系東盟與南亞國家。
如上所述,這是奧巴馬的最后任期,美國國民希望他果敢推出較好的經濟政策,美國工商業界也有理由期待他在第二任期有更積極的國際貿易政策,這也推動他必須設法在國際外交這個環節發揮更大成就,以維持國內支持及保證國民對他兩任總統的積極評價,同時留給民主黨繼續主政的機會。可是,奧巴馬的國際外交也可能遭遇到很“現實”的問題。其他政府可能正在等待未來的美國總統,他們針對著爭議性質或者較棘手的議題,可能會期待奧巴馬的繼任者更適合自身利益。這樣一來,在此同時,奧巴馬二任外交的特色也可能會表現在加重爭取各國“友誼”和“民間支持”,加強美國長年累月注重的通過使館和其他渠道進行的公共外交。美國在馬來西亞會注重向各派系伊斯蘭組織對話;同時,也是要說明穆斯林信仰的教義和美國政府提倡的“普世價值”可以交融,這有利于防范政治極端或反美勢力借用教義反美,減輕美國進入亞太“再平衡”的阻力。
然而,馬來西亞的穆斯林不是鐵板一塊。在馬來西亞眾多穆斯林組織之間,某些傾向自由主義的穆斯林團體,可能不一定茍同官方,卻又比官方的穆斯林機構更愿意親近美國;也有像伊斯蘭黨那樣強勢的反對黨,在全國擁有眾多反對現任政府的支持者,其黨中又有些人認為基于穆斯林團結可能應和現在的執政黨有某種程度合作。還有一些穆斯林組織,是美國不能溝通爭取也不想節外生枝的。因此,這就構成美國必然既走向主流穆斯林組織,與其對話交誼,又會有如《馬來西亞2012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中說的那樣,也會朝向“政府不承認的宗教組織”互相積極對話。在此情況下,馬國總理納吉提出類似中華傳統“中庸”定義的Wasattiya外交,并以英文moderate表達其理念,雖說和美方的“反恐”等立場有極大對話空間,但奧巴馬不曾代表美方高度回應,不見得是不知道或不以為然,其中可能涉及情勢與時宜的考慮。
參 考 文 獻
[1] Hillary Rodham Clinton, Delivering on the Promise of Economic Statecraft. at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in Singapore, November 17, 2012,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11/200664.htm.
[2] John Kerry,Remarks at the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9/214868.htm.
[3] Najib Razak, Global Movement of Moderates, Kuala Lumpur: Global Movement of Moderates Foundation,2012.
[4] Tare Lindholm, eds., Facilitating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A Deskbook, The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
[5] 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2012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6] President Obamas Message to Muslims on Ramadan,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of THE WHITE HOUSE,July 8, 2013.
[7]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0.
[8] Abuza, Zachary , “Tentacles of Terror: Al Qaedas Southeast Asian Network”,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4, No.3,2002.
[9] Malaysia-US Treaty Takes Effect, The Star, 23, January, 2009.
[責任編輯 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