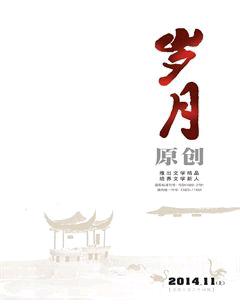剝落的日子
付大偉,本名付杰,85年生人,客居濟南。文字散見《山花》、《西湖》、《文學與人生》、《野草》、《西部散文選刊》等刊。曾獲首屆浙江作家網青年文學獎提名獎、第二屆“孫犁文學獎”。
余暉傾斜,Z城像片干面包,表面抹滿金黃。陽光泛著古銅色,攆著車跑。我多么鐘情向晚曖昧的天幕:她離我越遠,我便越難過,好像沖動是體內的鬧鈴,離別變得分秒必爭。最后的吉光片羽灑下來,不過是施舍。回想在辦公室的一天內,你拒絕了多少自然的饋贈,高尚得像位隱士——大多數人滿足于蝸縮在屬于自己的時間里,他們身邊環繞著一排排自己說不清,而又面無表情的省略號;又像蒲公英般敏感,隨便一陣風的理由,就將復雜的表情吹散在數個房間里。
當頭頂上空無限大時,深感黑夜就像一位智者的親臨。他飛馳的智慧代表了時間,人們在他壓迫式的“盤問”下,焦慮地燃起了街燈,望著光縱橫的流水線,開始反思內心的虛實。黑夜,開始逃離,讓所有赤裸的心安睡。發生這一切的前幾個小時,黃昏里的最后幾分鐘,我把脖子習慣性地扭向窗外。每當想看最后一眼,可巧,方向盤都準確地拐向南方(我住的方向)——它再沒有一席之地。一排排高大的建筑瞬時簇擁眼前,紛紛阻擋迎接目光的夕照。建筑像彼此吸引的矩形磁鐵,靠得很近,有種說不出的曖昧。樓有間隙,透射過來的纖弱,被鋒利的樓影攔腰斬斷,車疾馳,把碎撕成碎。
大街小巷里彌漫的暑蒸,隨風而行,像大朵的云飄來飄去,撞上,軟塌塌的,沒有生命危險,卻溫柔得要命。臨窗倚靠,一個給身體放松警惕的時刻,我不合時宜地想到了半年前的遷移。說不清是以什么身份,依靠腳下的路而熟識的意象重新變成一個內在記憶。生命中的某個雪天,T城漸行漸遠,微縮一團,在一個人的自我取暖中慢慢融化。
我無法不成為自身的律師。直至今日,我仍一直浪漫地辯解:T城,只是我走失的第一個情人。清楚一點說,即是我對美好事物認知過程的一次失手,也許更會蔓延到將來。我們于某日林間漫步,濃濁的氣霧令我慌亂中錯認了她的手,撞至纖細的樹精,方呼是樹影婆娑的錯。這種荒唐而不失妙趣的想法只要存在一天,就證明我還沒走向衰敗。管他呢,我固執地認定:一個沒有幻想的異鄉人,其身體的鐘擺始終在理想和現實間做機械流浪,永遠沒有歸期和情愛。
冬季來臨。流動,比守住她的愛情更艱難。
我回憶起,我是在一個炎炎夏日突然決定留下來堅守T城。堅守,對身邊人說,不過是個謊言和措辭。信誓旦旦的第二天我就無比難過。看似堅決的背后——臉部的某條神經卻背叛了現場。那塊本來平靜,卻倏然不息止跳動的肌肉,令我不得不背過身去,做最后自我征服式的內心獨白和宣言。這個背景下,誕生的是一個復雜的還在發育的夢;裹挾了理想、愛情、盲目、虛榮和掙扎的夢;讓你在一瞬間純粹,熱血澎湃,而數小時之后茫然不知出路的夢。這個臭小子曾一度把它與世隔絕了,今天拿出來,很難找到新鮮不至于重復的激情。同學們作鳥獸散,我留下來準備過冬。仔細想想,他們跟我一樣,表完態,就把自己扔進一條坑道,干凈利落,吹響沖鋒號。此時,年輕執意要與霸道和勇敢這類詞走得很近,才能證明它珍貴的“第一次”。
從一條不知名的小街上采購。不遠處的工棚外,一群有說笑的工人盤腿坐在瀝青路面上打撲克,為一張小丑、國王的牌吵得面紅耳赤。印象中,像他們這樣在T城建設的工人似乎早已被定位為“鑄在混凝土套子里的人”。于是,每逢遇見,我都想上前捏捏他們粗壯的胳膊、腿肚子,心想那一定是最堅硬和最忠實的部分。那骨子里酸溜溜的,揮之不去的體味,也固守在這軀殼里,有了形狀,連同這座城市里的其他味道,一起發酵。發酵,還有我的,混在一起,一天比一天濃烈,沖得我頭昏腦脹。
一個恍惚的下午,我被一片落葉準確擊中,真疼。它經過一個春天的孕育,一個夏天的成長,已經變得足夠肥厚寬大。我嘲笑它貪婪,汲取了太多的養分而身形臃腫。我漸感到:落下,只是一個清心寡欲的物理變化,下落,則需要承受滯空帶來的負重和喪失誘惑的失落。冥冥中,這片落葉其實并不屬于時間,只屬于自身有限的空間。
始終要持個態度留在T城。我試圖從身邊的世界挖掘根源,發現正如那些光怪陸離的生活澆筑到某個華美的房間,人們都會報之艷羨那樣,我為此萌生出原始的沖動和狂喜。及至離開,都無法肯定自己是失落還是慶幸。坐在我所謀求的辦公室內,像其他人一樣享受著空調和寬敞明亮的環境。室外,鞍山西道已在眼前蒙了一層浮動的蒸汽。酷熱和焦灼,讓我仔細感知著自己目前的位置、準確的坐標——對樓人的方位在一片朦朧中已辨別不清。也許,他們也在試圖將我看清,而我已經沒有時間觀察他們了。一期期的選題、策劃、編輯任務已把我的精力榨干,我需要證明:一個舉無輕重的打工者,在這座繁盛而暗朽的城市里,在精神層面和物質層面上,我所想抵達的一切。于是,整個夏季太漫長了……
我住在前一棟樓的投影里。前一棟樓里住滿了鴿子。它們自覺地聚集在這待拆的只剩骨架的居民樓內。一個不知名的邋遢的男人在早晨常來投食,他們成為好朋友。樓影扁長,陰翳,顏色青灰,我近距離觀察過這種色調,試圖努力在自己的畫作里搜尋。我記得,畫面里呈現的灰是高級灰,一種區別于惰性的黑色漸變的活躍色彩,干凈,靈動。為畫而畫,為美存在。而識別眼前的灰,我竟糊涂了。這種灰有像漩渦一樣的拖曳力,深幽,溺于準確的坐標中;邊緣規整鋒利,有切膚之感;大面積的傾斜猶如四方杯中搖晃的灰咖啡。我把這種感受與來訪者分享,(事實上,只有一位從京城趕來探望的同學),他簡潔總結道:“這間屋子寒氣逼人,你需要在陽光下成長。”為此,他甚至熱心地給我買了個電熱煲,鮮紅色的外套,置在房間里格外扎眼。望著這點紅,每每在晚間回家時感到熱血涌動。從另一種角度看,生命終于有點哲學味道了。
雪夜,像某個不鋪張的節日,悄然降臨。那時節,寒氣比任何時候來得都急,它們被推搡到一處狹窄的胡同內,三竄兩跳地直灌入一幢如同冰窖的六層小居民樓。沒有爐火和暖氣,我只得把窗子緊閉,玻璃面上爬滿汽化后朦朧的遺痕。我的房間,直沖過道住著兩個廣東女孩,她們咿咿呀呀的語言和在空中比劃著費解的手勢令我茫然,但友好。因為畢業創作,她們夜間回來很晚。笨重的油畫板敲擊墻面的沉重的“咚咚”聲,經常把我從美好憧憬的幽夢中驚醒,并漸漸成為習慣。
在一個個寂靜的雪夜里突然醒來,那雙無所事事失眠的眼睛成為黑色壁壘里最為吊詭和憂郁的鏡頭。
我望著窗外紛繁凋落的雪花,深感那是大自然自我凈化時一種過剩的浪費。它們在夜間鋪天搶地地灑滿人間大地,或融化,或殘積在地球一層薄薄的人類文明上,最終都消失于無形的白晝。我開始擔心,我所度過的那些堅守的日子,那些為美好期冀而做出的努力,也最終在絆扯中走向剝落。
我急切地拉下燈線,掃視間,驟然發現昏明之間唯一與往日不同的是,床尾又散落下許多墻皮,潔白的墻面終于在時間的軟磨硬泡中破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