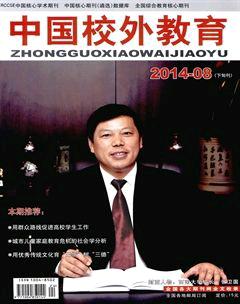淺談林則徐
劉黛軍
林則徐,出生在儒學(xué)世家,接受父母啟蒙教育的士大夫,被稱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宦海浮沉,他“經(jīng)世致用”,憂國憂民。對(duì)于林則徐的評(píng)價(jià),各家所持觀點(diǎn)不盡相同。蔣廷黻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中對(duì)其有“兩個(gè)林則徐”的觀點(diǎn),根據(jù)此說,談幾點(diǎn)看法。
林則徐評(píng)價(jià)〓《中國近代史》林則徐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關(guān)于林則徐的評(píng)價(jià),各家所持觀點(diǎn)也不盡相同。《清史稿》評(píng)價(jià)林則徐“才略冠時(shí)”,并認(rèn)為如果廣東事務(wù)始終依靠林則徐,“潰裂當(dāng)不至此”。蔣廷黼先生在他的《中國近代史》一書中認(rèn)為:
“林則徐實(shí)在有兩個(gè),一個(gè)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gè)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gè)林則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戰(zhàn)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
真的林則徐是慢慢地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后,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shí)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
蔣先生認(rèn)為,林則徐盡管內(nèi)心認(rèn)識(shí)到西方的強(qiáng)大,但卻不公開提出國家的改革,因?yàn)樗ε隆扒遄h”,他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yù)與時(shí)人奮爭(zhēng)。
關(guān)于蔣先生的這個(gè)觀點(diǎn),我有自己的看法。林則徐的所作所為反映出的個(gè)人品性,他從政開始所實(shí)施的政策,都可以證明他不是一個(gè)畏懼“清議”、懼怕公開施行改革的大臣。
首先,是堅(jiān)定的禁煙決心。縱觀林則徐與鴉片的“斗爭(zhēng)”過程,我們看到的是他對(duì)鴉片的深惡痛絕與禁絕此物的決心。“道光十三年四月(1833年5月),林則徐與陶澍合奏,主張嚴(yán)禁鴉片;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七(1838年6月28日),向道光帝提出了禁煙六策:收繳煙具;限期禁吸食鴉片;加重開館興販罪名;嚴(yán)厲查處失察的官員與親人;七月(8月),與湖南巡撫錢寶琛、湖北巡撫張?jiān)浪陕氏葒?yán)禁鴉片,搜繳大量煙土、煙具;八月(9月),上《錢票無甚關(guān)礙宜重禁吃煙以杜弊源片》,指出鴉片泛濫對(duì)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破壞,以及各級(jí)官吏的包庇,使禁煙流于空文;九月初十(10月27日),再次銷毀大量煙具、煙土;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1839年3月18日),與鄧廷楨、怡良傳訊行商,并發(fā)給諭帖二件,責(zé)令鴉片販子繳煙,要求它們具結(jié),宣布區(qū)別‘良夷‘奸夷的政策;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虎門銷煙開始。”從政過程中,他始終沒有停止對(duì)鴉片的禁絕,搜繳、上書、銷毀,利用一切可以的方式。對(duì)待鴉片,他顯示出自己強(qiáng)硬的一面。
其次,不畏皇權(quán)。“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833年12月23日),不顧道光帝責(zé)備,他奏請(qǐng)緩征漕賦,“為民請(qǐng)命”;十二月二十五日(1834年2月3日),作《答陶云汀宮保書》,表示愿對(duì)違例請(qǐng)緩征承擔(dān)責(zé)任。”可以看出,林則徐對(duì)于皇帝并不是“愚忠”,并不是盲目地遵守皇帝的政令,他“愛民”“愛國”,作為一名士大夫,他更多的是對(duì)于國家與人民的責(zé)任。
林則徐禁煙的堅(jiān)定決心與對(duì)皇權(quán)無畏的品性,得以證明他所支持的不是某個(gè)人的朝廷,而是整個(gè)中國。只要相信自己的措施有利于國家,無畏皇帝的權(quán)威。正因?yàn)榇耍艺J(rèn)為他是不會(huì)因?yàn)閷?duì)于“清議”有所顧忌,而束縛住自己的思想與行為。
再次,是前期的治國改革措施。1840年鴉片戰(zhàn)爭(zhēng)之前,林則徐實(shí)施了一些有利于國家的改革措施。道光四年(1824年),黃河高堰決口,嚴(yán)重影響漕運(yùn)。出任江蘇布政司的林則徐贊同“以海運(yùn)代替河運(yùn)”的看法,經(jīng)過磋商,最后由他本人擬稿奏,七月,林則徐接命負(fù)責(zé)海運(yùn)。
道光十二年(1832年),林則徐主持壬辰科江南鄉(xiāng)試監(jiān)臨,看到科舉制度弊病后,對(duì)同考官校閱章程和士子應(yīng)試規(guī)則進(jìn)行修改;道光十七年三月初五(1837年4月9日)任湖廣總督,后整頓鹽政,反對(duì)私鹽充斥湖廣地區(qū)。不管是對(duì)于經(jīng)濟(jì)還是教育問題,林則徐盡力改革,使其對(duì)于國家的發(fā)展與人民生活的提升有所幫助。
所以,針對(duì)蔣先生認(rèn)為“真正的林則徐”是認(rèn)識(shí)到西方的強(qiáng)大,卻因害怕“清議”而不公開自己像西方學(xué)習(xí)的觀點(diǎn),我認(rèn)為是值得商榷的。對(duì)于皇帝,他直言不諱,對(duì)皇權(quán)尚且不畏;削職期間,盡管奕山主和,林則徐依然向他提出軍事上防御英軍的建議。他并不是一個(gè)因輿論而左右自己的臣子,并不像蔣先生所說“最缺乏獨(dú)立的,大無畏的精神”。前期治國措施可以證明他存在對(duì)于弊政的改革意識(shí)。
而且,林則徐確實(shí)在向西方學(xué)習(xí)。“林則徐在奉命赴粵查辦海口事件、在辦理夷務(wù)過程中及事后都十分重視探訪‘夷情,掌握‘夷情,認(rèn)識(shí)‘夷情,根據(jù)‘夷情采取馭夷、治夷、籌夷對(duì)策和措施。”“他招致一批有才干的人物……延請(qǐng)一些留心海防事務(wù)的學(xué)者……商議探討洋事。又指示通事、買辦、引水等和外國人直接往來的人員,隨時(shí)報(bào)告他們的動(dòng)向……為了探求西方國家的情況,他下令搜集外國人在廣州、沃門用中文出版的各種刊物,包括傳教小冊(cè)子,并打破天朝的‘禁區(qū),招集通曉英文的翻譯人才入幕,組織翻譯外國人出版的書報(bào)……”這是蔣先生所說的“真正的林則徐”,他看到了差距,他盡力向西方學(xué)習(xí),盡管他沒有提出更加深刻的學(xué)習(xí)西方的改革措施。
不可否認(rèn),自前期林則徐的改革措施就沒有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變革,主要在于經(jīng)濟(jì)建設(shè)與教育方面,而后向西方學(xué)習(xí),也只是學(xué)習(xí)先進(jìn)的器物,沒有提出清廷制度的改良措施。但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思想的開放應(yīng)是循序漸進(jìn)的,處在不同時(shí)間階段的人對(duì)于世界與知識(shí)的看法和了解會(huì)有一定的局限。林則徐代表的是士大夫階級(jí),從小在儒學(xué)的熏陶下成長(zhǎng)起來,要他從文化與自己所處的整個(gè)環(huán)境背景中否定自己,是存在困難的。在此,我認(rèn)同蔣先生“文化搖動(dòng)等同于士大夫飯碗搖動(dòng)”的觀點(diǎn)。
總的來看,林則徐身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之后的洋務(wù)派、維新派以他為基礎(chǔ)。作為一名傳統(tǒng)的士大夫,他維護(hù)朝廷統(tǒng)治,將“國強(qiáng)、民安”視為一生追求;他不困頓于皇帝的統(tǒng)治,不作“愚忠”之臣,直言不諱,敢想敢為,不因?yàn)椤扒遄h”而束縛自己的作為;主動(dòng)向西方學(xué)習(xí)科技,根本是為了清廷實(shí)力的增強(qiáng),不被外來力量欺辱。對(duì)于林則徐的局限性,我們應(yīng)是包容的態(tài)度:儒學(xué)傳統(tǒng)根深蒂固,個(gè)人力量無法與時(shí)代抗衡……我們不能要求一個(gè)剛剛接觸到外國先進(jìn)器物的人,已經(jīng)知道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人,再更進(jìn)一步地在全社會(huì)提倡改革;同時(shí),作為當(dāng)事人,之前處于“天朝自居”的社會(huì),信息閉塞,對(duì)西方并不了解。認(rèn)識(shí)的過程需要時(shí)間的沉淀,盡管與時(shí)間相伴的是恥辱、血淚。
參考文獻(xiàn):
[1]趙爾巽.《清史稿》卷三百六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97.11498.
[2]蔣廷黼.中國近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6.
[3]林慶元.林則徐評(píng)傳·附錄.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382-386.
[4]林則徐.答奕將軍防御粵省六條.
[5]中國近代史組.林則徐詩文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鄭劍順.林則徐對(duì)“夷情”的探訪及認(rèn)識(shí).河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6, 33(2).
[7]楊國楨.林則徐對(duì)西方知識(shí)的探求.endprint
- 中國校外教育(下旬)的其它文章
- 表演專業(yè)臺(tái)詞教學(xué)的拓展與深入
- 外科護(hù)理學(xué)教學(xué)中如何提高學(xué)生學(xué)習(xí)興趣
- 基于“學(xué)習(xí)共同體”理論的教學(xué)實(shí)習(xí)模式
- PBL教學(xué)法應(yīng)用于護(hù)理醫(yī)學(xué)化學(xué)教學(xué)改革中的體會(huì)
- 構(gòu)建發(fā)展性教學(xué)評(píng)價(jià)體系促進(jìn)思想政治教育發(fā)展
- 關(guān)于做好高校藝術(shù)設(shè)計(jì)專業(yè)班主任工作的幾點(diǎn)體會(hu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