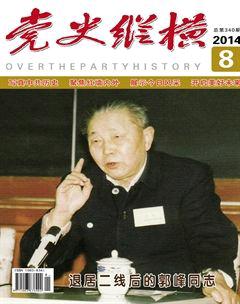國共重慶談判的大背景
張家康
日本投降蔣介石措手不及
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后,美英蘇三大國就醞釀著早日結束亞洲的戰爭,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1945年7月16日,三大國在德國柏林郊外波茨坦召開會議,通過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其主要內容是:日本無條件投降;實施《開羅宣言》,促進日本民主化;日本不得有軍火工業;在日本的占領軍待新政府成立后撤出日本。但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聲稱“決心戰至最悲慘的結局”。因此,哪一天能結束戰爭,誰也不敢貿然預言。
蔣介石就對即將到來的勝利一點精神準備都沒有,甚至還在蘆溝橋事變八周年發表紀念文章說:“以八年戰斗的經驗,我可斷言,敵國民眾在軍閥驅迫欺騙之下,是只認得力量,不認得是非,也不知道利害。”號召全國軍民還要有長期作戰的精神準備。
美國總統杜魯門早就想盡快地結束戰爭。7月21日,他在得知美國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后,對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心中終于有了底。8月6日晨8時,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騰空而起的耀眼的蘑菇云也驚醒了斯大林,他立即于8日命令對日宣戰,蘇聯紅軍隨即出兵東北。驕橫的日本軍閥還是不害怕,一點投降的跡象也沒有。9日11時30分,美國又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廣島和長崎遭受滅頂之災,令長居深宮的日本天皇害怕了,迅速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
勝利來得太突然了,蔣介石真的措手不及。此時,國民黨軍事主力偏處西南,日軍仍然占領自東北至廣東的大片中國國土,受降接收的問題已迫在眉睫,廣州、長沙、武漢、南昌、九江、安慶、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鄭州、洛陽、青島、濟南、北平、天津、山海關、承德、赤峰、多倫、古北口、張家口、歸綏、太原、包頭、石家莊等戰略要點的接收,對蔣介石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可要命的是,他的主力部隊距這些地方都太遠,如果不能及時運兵接收,近水樓臺的共產黨就會去接收。
杜魯門在回憶錄中,對蔣介石當時措手不及的情形,說得最為明白。他說,當時“蔣介石的政權只及于西南一隅,華南和華東仍被日軍占領著,長江以北則任何一種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沒有。”“事實上,蔣介石甚至想再占領華南都有極大的困難。要拿到華北,他就必須同共產黨人達成協議,如果他不同共產黨人及俄國人達成協議,他就休想進入東北。”
然而此時的中共,與1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120萬人,民兵也有220萬人,在19個省內有19塊解放區,面積約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中國共產黨密切關注著抗戰勝利后的中國局勢。8月10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關于日本投降后我軍任務的決定》,明確指出:日本投降后,國民黨一定向解放區進攻,和我們就接收問題,有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他指出:
目前階段,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敵偽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體情況發動進攻,逐一消滅之,猛力擴大解放區,占領一切可能與必須占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并放手武裝基本群眾,不應稍存猶豫。……將來階段,國民黨可能向我大舉進攻,我黨應準備調動兵力,對付內戰,其數量與規模,依情況決定。
毛澤東態度明確,語氣堅定,對抗戰勝利后將要出現的情況,已是洞若觀火,胸有成竹。8月13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社論中,再次明確地提醒全黨,“蔣介石在挑動內戰”,并斬釘截鐵地表明了應對的方針:“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內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衛,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權利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
與此同時,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發布命令,號召各解放區抗日部隊向日偽軍發起猛烈進攻,命令附近的目偽軍在限定的時間內繳出全部武器,如拒不投降,立即予以消滅,八路軍、新四軍將接收其所占的城鎮和交通要道。延安總部又連續發布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區武裝部隊向敵偽所占地區和交通要道展開積極進攻,包括要求冀熱遼解放區等地的部隊向東北進軍,迫使日偽軍投降。
蔣介石急了,慌忙以最高統帥的名義給八路軍發出強硬的命令:“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當然,蔣介石也最清楚,八路軍、新四軍是不會買他的賬的。現在對他來說,時間是最關鍵的問題。他想起,3年前曾向周恩來提出過與毛澤東相會在西安;共產國際解散后,他又致信毛澤東,希望“面談一切問題”。二次相邀,都因種種原因而沒有實現。現在只有裝出一副謙恭的樣子,再次邀請毛澤東來重慶,以談判拖延時間。
這在他授意張治中給胡宗南的密電中,表現得最為露骨和明白:“目前與奸黨談判,乃系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復淪陷區中心城市,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作具體談判,如彼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事實也是如此,就在蔣介石向毛澤東發出邀請之際,上海、浙江的漢奸武裝,搖身一變為國軍,阻止新四軍的進入。廣州等27個戰略要點,除張家口、古北口由八路軍解放,多倫、赤峰、承德為蘇軍和外蒙古軍占領外,其余的戰略要點,多由美國搶運的國軍所接收。
赫爾利愿以國格擔保
抗戰勝利了,戰后中國能否實現真正的和平,一直是美國關注的焦點。抗戰以來,美國基于其在遠東的利益,不斷地調整對華政策。而其對中共的認識,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邁克爾·沙勒以1941年為界限,分析了美國對中共的認識。他說:
在1941年以前,美國官方對中共的觀點是誤解與敵視的大雜燴。政府中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亞洲農民的感染力感到迷惑不解,固而有時把中國共產黨稱為“土地改革者”的政黨。那些專家還認為所有的共產主義運動都直接或間接地被蘇聯所控制,因此,都是莫斯科的傀儡。在1941年以后,當一批極有才華的美國駐重慶使館的外交官廣泛地報道了中共解放區的情況,以及中國共產黨自己開始同美國人交上朋友以后,這些粗淺的看法才漸漸轉變了。
中共也有意與美國接觸,讓美國了解中共,也使中共了解美國。1942年5月下旬,周恩來在重慶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誠懇地希望美國軍事代表團和美國記者去延安參觀訪問。他還委托斯諾將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業績的資料帶給羅斯福的顧問居里,并附信一封,表明中共堅持抗戰,反對內戰的態度和決心。信中還說,中共領導的軍隊盡管已經兩年多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任何補給,在裝備上遠遜于國民黨軍隊,但卻牽制著日本在華兵力總數的將近一半。所以,同盟國提供給中國的援助,理應有堅持抗日的八路軍、新四軍的一部分。
1943年1月,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兼中緬印戰區司令政治顧問約翰·謝偉思最先提出,美軍應向延安、華北和西北抗日根據地派出觀察組。在他看來,要真正了解共產黨,“只有到延安和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去,才能取得第一手的材料。”之后不久,另一位美國外交官戴維斯也在一份備忘錄中,呼吁羅斯福總統派軍事觀察員去西北、華北。
與此緊密呼應的是,美國在華最高長官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也多次要求羅斯福總統致函蔣介石,就向中共控制地區派遣美軍觀察組的事與之交涉。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明確表示出對國共關系的關切,一再提出美軍觀察組的問題。蔣介石這才勉強同意向延安派駐美軍觀察組。7月22日,美軍觀察組一行9人在組長包瑞德上校的帶領下,由重慶飛往延安。自此,中共與美國官方有了準正式的外交接觸。
中共對美軍觀察組的到來,表示出熱忱的歡迎態度,黨政軍的高級領導人積極參與會見和談話。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談話中,希望美國運用其影響制止國民黨發動內戰。毛澤東還向謝偉思提出這樣的要求,考慮到戰后美軍觀察組的撤消,美國可否在延安設立領事館。所有這些都表明,共產黨不是象蔣介石所妖魔化的那樣,是些蠻不講理的“紅頭發”野人。
觀察組基于所見所聞的大量事實,給華盛頓發去許多報告,其主要內容是,美國應該全面支持國共兩黨,而不是片面地支持國民黨,這樣就有可能促使國民黨實行改革,實現國共合作,以推動中國政治向著組成聯合政府的方向發展。這些報告通過新聞媒體的報道,在美國產生出“激動人心的影響”。美國朝野無不反對中國內戰,美國政府從維護自己的戰略利益出發,力主調停國共兩黨的沖突,以共同一致地對付共同的敵人日本。
1944年10月,在蔣介石的一再要求下,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被召回國。隨之而來的赫爾利,先是美國總統特使的身份,后又繼任美國駐華大使,其在華的主要使命之一,仍是調處國共兩黨的關系,繼續中共與美國的對話。11月7日,赫爾利飛往延安,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會談,力促國共軍事力量的統一。
赫爾利在延安向毛澤東表示:如果蔣介石表示要見毛主席,我愿意陪毛主席去重慶,討論增進中國人民福利,改組政府和軍隊的大計。我們將以美國國格擔保毛主席及其隨員的安全。顯而易見,赫爾利是在用激將法,目的是促使國共高層坐下來和談,其用心是無可厚非的。正是出于對赫爾利的尊重,周恩來才由延安回到重慶,使已中斷的國共談判又重新開啟。
1945年2月13日,赫爾利陪同周恩來面見蔣介石。蔣介石拒不接受中共的意見,反對成立聯合政府,國共和談又陷入僵局。距此半年的時間,抗戰全面勝利,蔣介石慌了手腳,已全力支持蔣介石的赫爾利建言,鑒于斯大林的揄蔣抑毛的公開態度,大可不必擔心蘇聯的介入,可以放心大膽地邀請毛澤東來重慶談判。無論是否接受,毛澤東都要陷入兩難之中。如果拒絕,則表明毛無和談的誠意;倘若真的來了,我們則以時間爭取空間,利用談判的機會,將國軍運往華北、華中等地。赫爾利的建議恰中蔣介石的下懷,這才連發電報,催促毛澤東早目成行。
斯大林兩次來電催促
蔣介石最擔心蘇聯出于政治信念的立場,會全力支持中共,使其日漸坐大。1944年3月,在中共代表林伯渠將來重慶談判時,他的這種擔憂便在日記中表現出來:“(1)受俄指使偽武裝歸誠中央,待取得合法地位與發言資格以牽制中央之外交政策,而后奪取中央政權。此其陰謀之一也。(2)在此一時期內使中央承認其軍隊并賦予其一方之任務,待占平津或東北,乘機突變割劇地方,設立偽組織而作俄國之傀儡,以排除美英在東亞之勢力也。”
蔣介石哪里知曉,其實斯大林對毛澤東有著很深的誤解。抗戰初期,當毛澤東提出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斯大林就十分不滿,惟恐這種“獨立自主”無邊無際,以至得罪國民黨得罪蔣介石,影響到蘇聯的戰略利益,于是派王明回國監督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王明有此尚方寶劍,坐鎮武漢,背著毛澤東,常以中央的名義發指示,公然與延安分庭抗禮,擺出一副取而代之的架勢。如果不是毛澤東在全黨的威信,如果不是黨內同志多對教條主義深惡痛絕,如果不是任弼時及時地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黨內的真實情況,王明準會象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那樣,穩穩地實現第二次奪權。
赫爾利在確立“扶蔣反共”政策后,曾專程去莫斯科探聽虛實,沒想到一向出言謹慎的斯大林,竟會毫無掩飾地告訴這位美國人,中共并非真正的共產黨,也不認為毛澤東可能奪取政權。當談到蔣介石能否吞并延安時,赫爾利發現斯大林竟然無動于衷。相反,斯大林贊賞蔣介石是“大公無私的愛國者”。
斯大林一直過高地估計國民黨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中共的力量,甚至認為戰后的中國只能承認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只能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來實現中國的統一。共產黨只有妥協,避免內戰,建立以蔣介石為領袖的聯合政府。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談話中還說:戰后我們曾邀請中國同志到莫斯科來,討論中國的形勢。我們直率地對他們說,中國同志應設法和蔣介石達成妥協,他們應參加蔣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軍隊。
1945年2月初,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在蘇聯克里米亞海岸的雅爾塔舉行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其中重點討論蘇聯出兵東北對日作戰的問題。斯大林答應出兵東北,但是卻提出有損中國領土主權的先決條件:承認外蒙獨立;大連商港國際化,蘇聯有優惠權利;蘇聯租借旅順為海軍基地;中東、南滿鐵路由中蘇共管。這就是《雅爾塔協定》。斯大林十分清楚,這個協定是背著一個主權國簽訂的,它還必須要得到中國的承認。6月12目,蘇聯大使彼得羅夫會見蔣介石,提出以《雅爾塔協定》為前提,磋商締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并且捎來斯大林的口信,希望在7月1日以前,中國的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到莫斯科締結條約。
蔣介石當然不滿意《雅爾塔協定》,更不愿外蒙從他的手中分離出去。可是,蘇美以強凌弱,斯大林又變幻無常,已不容蔣介石猶豫。都說弱國無外交,只有忍,蔣介石無奈派出宋子文、蔣經國、卜道明等赴莫斯科談判。會見中,當蔣經國對外蒙獨立表示出不同意見時,斯大林說:“倘使你的國家有力量,自己可以打倒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于廢話。”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之后,蘇聯表明只支持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斯大林兌現了承諾,在美國向日本長崎投放原子彈的那天,100多萬蘇聯紅軍在總長5000多公里的戰線上同時發動進攻,鐵流滾滾,摧枯拉朽,盤踞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受到致命一擊,日本的崩潰已是不可逆轉的定局。
中共對蔣介石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在蔣介石第一封電報發來時,據1945年8月17日《解放日報》,中央在致徐冰、張明電報中指出,“請毛往渝,完全是欺騙”。中共中央還針對來電,以朱德的名義公開提出6點要求,其中包括“國民黨在接收日偽投降與締結受降后的一切協定和條約時,必須事先與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換句話說,這些要求如不能實現,那么,毛澤東的來渝談判也就成為不可能。
對于國共重慶談判,斯大林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表示了明確的態度,支持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否則一旦打起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斯大林還說,中共的武裝斗爭是沒有前途的,應該同蔣介石達成協議,解散軍隊,加入國民政府。在蔣介石給毛澤東發來第三封電報時,斯大林也發來了第二封電報,再次催促毛澤東成行,指出,蔣介石已再三邀請你去重慶協商國事,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味拒絕,國內、國際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內戰真的打起來,責任由誰承擔?斯大林還在電報中擔保:你到重慶同蔣介石會談,你的安全由蘇、美兩家負責承擔。
和平民主已成時代關鍵詞
抗戰勝利前夕,國共兩黨幾乎在同一時期召開了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七大從4月23日開至6月11日,國民黨六全大會則是從5月5日開至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提出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爭取人民的自由,實行農村改革,發展民族工業,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團結知識分子,爭取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的解放和發展,建立和平、獨立、民主的外交等。
提出“民主的聯合政府”,顯然是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挑戰,國民黨六全大會很快就作出強烈的反應,堅決拒絕中共建立聯合政府的建議。決定于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蔣介石還在政治總報告中說:“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滅共產黨!日本是我們外部的敵人,中共是我們國內的敵人!”
從1945年1月以來,國民黨軍隊一直沒有放松對中共武裝力量的壓迫和打擊。據萬仁元、方慶秋主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機密作戰日記》披露,國民黨第二戰區1月發生戰斗12次,2月發生戰斗19次,3月發生戰斗18次。如果說1至3月份是小規模的戰斗,那么進入4月,國民黨軍便有大部隊的作戰,投入的兵力都是師、團的建制,軍事沖突日漸升級。到了7月,戰火越燒越旺,大小戰斗竟達80多次。第二戰區是這樣,全國其它戰區的形勢也是大同小異,內戰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國共之間劍拔弩張的形勢,嚇壞了中間人士,他們擔心大規模內戰的發生。以褚輔成為首的7名參政員于6月2日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希望國共繼續商談,從速完成團結。中共中央十分體諒褚輔成等的良苦用心,于16日復函,懇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倘因人民渴望團結,諸公熱心呼吁,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并立即實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則敝黨無不樂于商談。”電報還邀請他們前往延安一敘。
于是,褚輔成、黃炎培、冷通、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6位參政員(王云五因病未能成行),于7月1日從重慶飛抵延安。他們受到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林伯渠、吳玉章的熱情接待,“彼此都十分坦誠,十分懇切”,并達成《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6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雙方取得兩點共識:一,停止進行國民大會;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
中共中央對和平表示出積極的態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協,并準備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只要國民黨改變反共政策,可以考慮承認“獨裁加若干民主”的解決方式。中共中央還提請美國注意:“認為蔣可以打敗日本,統一中國,但結果會與其希望相反。日蔣如決戰,蔣必再敗;目如撤退,蔣必內戰,統一無望。美只有扶助中國民主力量,才能戰勝日寇,制止內戰,取得戰后和平。”“制止內戰,取得戰后和平”,正是國人企盼已久的心聲,中共對于和平談判,已經發出了十分明顯的信號。這樣,中間力量才得以從中斡旋和游說。
1945年8月5日,中國民主同盟發表《在抗戰勝利聲中的緊急呼吁》,提出“民主統一,和平建國”的口號,民盟政治報告認為,抗戰勝利后,是“中國建立民主國家千載一時的機會”,民盟的任務,“就是研討怎樣把握住這個干載一時的機會,實現中國的民主,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
黃炎培從延安回到重慶后,與胡厥文、章乃器、施復亮、李燭塵等共同籌備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宣稱:愿“以純潔平民的協力,不右傾,不左袒,替中國建立起來一個政治上和平奮斗的典型”。主張對美蘇采取平衡政策,對國共取調和態度,要求政治民主、經濟和思想自由。第三黨負責人章伯鈞向記者發表談話,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黨治,實行民主,給人民以民主權利,并承認現有一切抗日民主黨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成為戰后中國的關鍵詞,蔣介石正是接過這些口號,作為邀請毛澤東來渝的重要理由,他在給毛澤東的電文中就有:“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
然而,蔣介石怎么也想不到毛澤東會慨然成行,更沒有料到毛澤東到重慶后,長袖善舞,異常活躍;會客訪友,如魚得水;媒體會面,妙語解頤。不僅一掃幾十年來被妖魔化的形象,更有一首《沁園春·雪》,在山城刮起不大不小的旋風,展現出毛澤東文人政治家、政治家文人的神采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