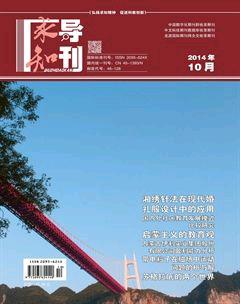啟蒙主義的教育觀
杜道琛
我們對于外界可感事物的觀察,或者對于我們自己知覺到、反省到的我們的心靈的內部活動的觀察,就是供給我們的理智以全部思維材料的東西。這兩者乃是知識的源泉,從其中涌出我們所具有的或者能夠自然地具有的全部觀念。
一、引言:啟蒙主義哲學的幾個基本看法
活躍于啟蒙運動之中的哲學家,包括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和狄德羅等,紛紛基于當時的社會環境,論述并發展了自己的思想。在這個部分中,筆者對這些思想進行了一下整理比較,就他們對世界的認識進行一個小綜述。
霍布斯認為,現象是人們認識的原則,而人們通過本能獲得作為知識開端的現象。“如果現象是我們借以認識一切別的事物的原則,我們就必須承認感覺是我們借以認識這些原則的原則,承認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從感覺獲得的。” “知識的開端乃是感覺和想象中的影像,這種影像的存在,我們憑本能就能知道得很清楚。”霍布斯不認為這個世界上真實地存在上帝、靈魂等,“真實存在于我們以外的世界上的東西,是引起這些外觀的那些運動。”他也不認為這些觀念真實地存在于我們的心中,他認為“沒有什么觀念是從我們心里產生并且居住在我們心里的。”他認為這些觀念其實是由人們的抽象思維對可見事物的觀念進行推理得來的。霍布斯公開聲言“哲學排斥神學”,其無神論思想在當時獨樹一幟。
洛克認為,知識是建立在經驗上面的,經驗來自于對外部世界的觀察和對自己內心世界的觀察,“我們對于外界可感事物的觀察,或者對于我們自己知覺到、反省到的我們的心靈的內部活動的觀察,就是供給我們的理智以全部思維材料的東西。這兩者乃是知識的源泉,從其中涌出我們所具有的或者能夠自然地具有的全部觀念。”也就是說,對外界的感覺和對自身的反省是知識的兩個來源。
孟德斯鳩認為,“由事物的性質產生出來的必然關系”就是法,“法就是這個根本理性和各種存在者之間的關系,同時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產生和存在都是必然的,存在著一個“根本理性”可以被認識,并以此作為自然法供人們所遵循。將人的自然本性看作社會的根本法則,并試圖從自然因素中尋找決定那個社會制度的原因,產生了“地理環境決定論”。
伏爾泰認為,這個世界需要一個上帝,“運動并不是憑自身而存在的;因此必須求助于一個最初的推動者……整個自然界,從最遙遠的星辰直到一根草芒,都應當服從一個最初的推動者。”但是,應該說,伏爾泰的上帝并不是最高的精神實體或基督教中的人格神。在運動原因方面,上帝實際上是一個邏輯上的假設,在社會生活方面,上帝是一個必要的信仰對象。因此,世界是一個可以通過邏輯來進行認識的世界。
盧梭認為,存在著“自然狀態”和“社會狀態”兩種狀態,并且認為二者具有矛盾,“自然狀態”是解決不平等問題需要回溯到的狀態。“自然狀態”是某種邏輯上的“假設”,通過剝離人的社會屬性,可以認識到決定人本性的自然規律。
狄德羅認為,世界中的各個現象是相互聯系的。“如果現象不是相互聯系著,就沒有哲學。”他認為,對世界的認識“有三種主要的方法:對自然的觀察、思考和實驗,觀察收集事實;思考把它們組合起來;實驗則證實組合的結果。對自然的觀察應該是專注的,思考應該是深刻的,實驗應該是精確的”。
綜上,啟蒙主義哲學家,在對世界的認識上具有如下基本看法:
(1)世界是可以被認識的。
(2)支配世界的是自然力量而非超自然力量。
(3)嚴格運用“科學方法”(如邏輯的“假設”)可以解決研究領域的基本問題。
(4)通過對世界的不斷認識實現對人類的教育,使人類不斷得到改善。
二、自由的培育
1.以自由、平等為目的教育
在整個啟蒙運動過程中,自由、平等、人權等概念成為了哲學的要求。
在當時,與自由相對的是教會、宗教審判等;與平等相對的是貴族、教職人員等;與人權相對的是宗教審判、巴士底獄等。
不過,以上所述均為對表面現象的描述。而其實質,則是17~18世紀的啟蒙哲學家,由于反對脫離實際的形而上的束縛而要求自由,由于反對建立在形而上基礎上因此越來越容易造成惡果的宗教、政治制度而要求平等,由于反對形而上的思維方式和形而上的制度造成的懲罰而要求平等。
霍布斯認為,一切人生來平等,在自然狀態下,人人欲保持個人的自由,但是又欲得到支配旁人的權力,二者的沖突造成了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霍布斯認為,通過社會契約,人類給自己加上了約束,使我們從愛好給人自由和愛好支配旁人的混亂中得到自我保存。這實際上是在說,被稱為“利維坦”的主權在創造時所憑的是協定和盟約,而非“我們要造人”的神的命令。霍布斯認為,“對運動不存在外界障礙,是謂自由”,專制的主權者通過保留自然狀態下人人持有的自由,可以獲得懲治權。
洛克對霍布斯的“自然狀態”的自由表示認可,但是洛克不認可君主制。洛克認為政治是對“自然狀態”下人人作為自己訟案中的法官造成的弊端的救治手段,但是當君主作為爭執的當事人時,此時他既是法官又是原告,這就不構成政治了。他因此提出立法、行政、司法幾種職權應分離,并認為這種制約與均衡是自由的保證。
孟德斯鳩也認為,權力分立是實現自由(或者說是政治自由)的保障。孟德斯鳩探討的自由不再是自然狀態下的自由,而是在一個有法律的社會里的自由。“在一個有法律的社會里,自由僅僅是:一個人能夠做他應該做的事情,而不被強迫去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權力分立的制度原則是實現上述自由的途徑,決定制度的完整面貌的因素是“地理環境”,“不同氣候的不同需要產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產生了不同種類的法律。”綜上,孟德斯鳩認為,在由地理環境決定的政治制度中,權力的分立可以為自由提供保障。
伏爾泰的社會政治學說也是以自然法為基礎的,他認為自然法就包含在人性之中,但是他認為社會和國家并不是由于契約而是由于暴力產生的,軍隊的出色領導在必然的戰爭中自然而然地獲得了越來越大的權力,君主的權力因此建立起來,國家也逐漸產生。他認為一個公正的秩序應該建立在自由、平等和財產的基礎上。伏爾泰在社會政治理論上認為自由是人的天賦權力。他認為自由就是“試著去做你的意志絕對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種權力”,同樣,平等也是人的天賦權利,“一切享有各種天然能力的人,顯然都是平等的;當他們發揮各種動物機能的時候,以及運用他們的理智的時候,他們是平等的”。在他看來,有完善的憲法和法律并且實行權力分立制度,能夠為自由和平等提供保障。
盧梭區分了“自然狀態”和“社會狀態”,他認為“自然狀態”下的不平等微乎其微,而在“社會狀態”下,一切不平等都會被放大。盧梭同意契約論,也認為人生而平等,但是他想尋找一種真正的合法的社會契約,以此來取代以往以犧牲人的自由平等為代價的社會契約。“尋找出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維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并且由于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樣地自由”,其要旨在于“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全部都轉讓給整個的集體”,他認為“惟有服從人們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在這兩個層面上,盧梭認為法律不僅保障公民的權利平等,而且是自由的基石。
狄德羅強調,“世界是強者的家”。不僅如此,狄德羅用進化論的思想反對當時盛行的“預成論”。在自然中,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沒有完全的重復,一切都在不停地生滅之中。
綜上,啟蒙主義哲學家都認為,人類社會的改善需要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要承認人生來具有的自由。
(2)要承認人生來具有的平等權利。
(3)制度(政治制度)是出于保護自由、平等權利的產物。
(4)制度的完善有助于自由、平等的維護。
(5)對自由、平等的認識和對制度的改善需要理性,作為個體要接受這些概念需要教育。
2.科學與自由的教育方法
(1)科學方法。用科學的方法解決教育領域的問題,與之相對的是神學的方法。
神學的方法是因襲式與定義式的疊加。天主教會有自己的圣人體系,并且對學術問題有自己的擇分,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只在講述與記憶的過程中,需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在理解、講述與辯論的過程中,不需要也不被允許自己解釋。神學的教育內容確立了當下的合理性,確立了當下一切事物的合理性。而科學的方法首先對自由有了要求,在這個過程中,自由表現為哲學上的懷疑。狄德羅臨死前說:“邁向哲學的第一步,就是懷疑。”其次,要運用理性去肯定理性。在這里表現為盡可能弱化神的能力。再次,相信理性的力量。認為學習、觀察與獨立思考是可以提出改進性意見的,對“更好”有所追求,并相信這個追求是由人來實現的。
洛克認為,教育的過程就是對人自身稟賦的塑造。強調要將良好和真正的本原植入孩子的心智之中、自身之中,雖然高度主觀抽象的人喪失了自然的規定性,但這也意味著人通過教育能夠重新獲得好的規定性。“形成良好的習慣、產生對自己尊嚴和名譽的意識、具備真正的德性和仁愛之心,面對一定的外部環境和條件,能夠自然而然地產生某種情感,做出某種行動”。通過這種“習慣成自然”的方式培養出來的人,才是脫離了抽象空洞的自我。而養成這種習慣的方式,是通過反復的實踐活動,使人的身體和心智自身獲得某種確定的形式。
(2)自由方法。用自由的態度看待教育,這個問題的核心是對教育的解釋權的問題,以及教育與需求的問題。在啟蒙主義思想家那里,表現為教育是為了使人相信神、相信當下還是教育是為了使人認識到自己的自由與平等權利并努力達到自由、平等。洛克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于要孩子學會運用自由,出于自己的合理選擇而做出自愿的行動,而不是消滅自由。“幼童一心要表現出他們是自由的,他們的好的行動源于他們自己,他們不受限制、完全獨立,這與成人當中的最驕傲者一樣。”因此,洛克主張利用孩子的興趣和對自由的愛好,讓他們積極、主動地學習。
3.世俗世界與神圣世界并存的教育基礎
在啟蒙主義時期,教育的基礎包括對兩個世界的描述:
(1)自然的世俗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們通過自身的經驗、理性認識世界,人對自己負責。這個方面的代表是洛克。洛克認為,人類所有的思想和觀念都來自或反映了人類的感官經驗。他拋棄了笛卡爾等人的天賦觀念說,提出了“白板說”,認為人的心靈開始時就像一張白紙,而向它提供精神內容的是觀念。觀念分為兩種:來源于感官感受外部世界的感覺和來源于心靈觀察本身的反省。洛克強調這兩種觀念是知識的唯一來源,并將觀念劃分為簡單觀念和復雜觀念。我們唯一能感知的是簡單觀念,而我們自己從許多簡單觀念中能夠形成一個復雜觀念。
(2)超自然的神圣世界。啟蒙主義的神圣世界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基督教世界,而是啟蒙的基督教世界。人們認為宗教必須自然化,“自然”的理性和諧共存。一些啟蒙時期的哲學家認為否認上帝存在是不合乎理性的,因為這個世界太有條理了,因此不可能沒有上帝的存在。即承認人們需要去認識上帝,并應當把世間的事物當做上帝的創造,但是同時強調對上帝的認識和對上帝創造物的認識應依據自身的理性。
伏爾泰從自然神論出發,認為上帝在創造了世界并對世界實施了第一次推動后就不再干預世界,世界就按照自身的規律運動著。
綜上,在一個主要由自然與人決定的世界內,用科學的方法去教授“自由”,教育才具有自由的性質,才具有維護自由的能力。
三、自由的歷程
1.自由與教育的關系
(1)接受一種反接受的觀點——自由與教育的矛盾。這個問題涉及的實質是教育的合法性問題。一是,一個個體憑什么可以教育另一個個體;二是,施教者的教育內容是如何確立的。第一,如果啟蒙主義哲學家希望教授一種自由,那么這種愿望終究是他們的而不是被教育的孩子的。不過,由上面的敘述可以知道,在啟蒙主義哲學家那里,“自由”往往是“自然”的內在要求和表現形式。所以在這里需要討論的是,人類是否必須遵循“理性的自由”。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根據啟蒙主義哲學家的權利觀點,沒有人可以強制別人選擇理性與自由;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這將意味著酒精與香煙等一切會使人遠離理智的行為都將是不合法的。第二,假定我們相信人類必須遵循“理性與自由”,那么我們該如何確定教授的內容呢?這個內容有兩個基本假定:一是被教育者是非“自然”的,并不天生地具備理性與自由,或者,理性的自由被在某種程度上蒙蔽了;二是不具備自由能力的人可以學著接受理性的自由。如果我們放棄對這兩個假定的討論(這兩個基本假設一旦進入討論就將否定教育的全部意義),那么作為無法完全達到自由與自然的人(否則這一目標也就不值得追尋了),必定無法具備教授自由的能力(自然神論者認為這一能力屬于自然神論意義上作為第一推動力的上帝),因此,對自由的教育只能是限制性教育,也就是說,通過自己能夠肯定的自由的否定層面上,告訴被教育者我們如何不自由,從而使受教育者具備追求自由的渴望,并具有追求自由的勇氣和能力。
(2)理念的自由與自由的真理表達——自由與教育二者之間的相互要求。這個問題要討論的是教育與自由是否是內在的互相要求。如果教育脫離了自由,教育將喪失存在的價值。當教育脫離了自由(理性、自然)時,我們將不具備討論、選擇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這個時候的教育不過是告訴你哪些事你必須做、哪些事你不能做、哪些事是什么樣的,你無需知道內容的真偽。在筆者看來,這不過是一個建立在極權主義的法律內的法令宣讀,既不具備教育的形式,也必將喪失教育的目的。并且很顯然,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教育者還是受教育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人的意義,他們淪為法律的工具。這就更無從談起平等與權利了。因為我們甚至不能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在受同樣的法律約束。如果自由脫離了教育,自由作為目的性的內容就將喪失。上文討論過,在啟蒙主義哲學家看來,自由是目的,自由的價值在于對自由的追求和追求自由的過程,對于個體來說,我們很難達到絕對的自由,個體感受到的自由其實是作為整體的社會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不斷實現的改善。教育是社會性追求的實現方式,而作為社會性的追求,自由要想延續下去,就內在地要求教育的存在。
2.對真理的信仰
(1)以個體的形式存在的真理與信仰——自由的真理與自由的信仰。具有理性的個體,自然地具有自由。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理性進行選擇,他們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真理與信仰到底具有什么意義、具備什么狀態。自由的個體互相之間都是平等的,“一切享有各種天然能力的人,顯然都是平等的;當他們發揮各種動物機能的時候,以及運用他們的理智的時候,他們是平等的”,因此,沒有個體可以否定另外的信仰,而同樣具備理性的個體,他們選擇的真理,內在上必定具有普遍性。
(2)以單純的形式存在的教育與信仰——真理的教育與信仰的教育。上文論述過,教育是追求自由的方式,自由是教育存在的內在意義。在這個層次上,真理的教育,就是不斷認識自由的過程;信仰的教育,則保障了教育仍然在自由的軌道上。以追求真理的方式追求自由,就是指不斷地確認自由的新的內涵。從啟蒙時期的“自然”“理性”開始,自由無論從實現自由的手段上(科學技術的進步)還是對自由的認識和訴求上(社會科學的發展),都得到了更深刻的發展,這都得益于對真理的追求。如果沒有信仰的教育,也就是說假使沒有使自由變成一種穩定的訴求,那么教育很容易走向沒落,也就是說越來越喪失對自由的熱情。當個體無法確立自己的信仰時,施教者和受教育者都將不再對“以后”這個概念具有控制性,也就是說,再也無法突破現實,悲劇者可能直接被現實的力量所束縛(出于當下既得利益的考量,這是必然的)。
四、小結
啟蒙主義時期對自由、平等的認識是深深地立足于當時對世界的認識和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的。這些觀點通過教育的形式發展到現在,不僅使自身越來越豐富,也使教育的目的越來越純粹(即追尋自由),方法越來越人性(依賴于科學和社會科學)。考量自由與教育的關系,二者內在的必然需求,要求我們即要更加努力地研究“自由”這一概念的新內涵,也要更加注意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參考文獻:
[1](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M].賀 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2](德)胡塞爾.第一哲學[M].王炳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3](德)卡西勒.盧梭問題[M].王春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4](德)康 德.論教育學[M].趙 鵬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法)盧 梭.論科學與藝術[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
[6](法)盧 梭.愛彌兒[M].李平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7](法)盧 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8](法)盧 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M].李常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9](英)洛 克.基督教的合理性[M].王愛菊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10](英)洛 克.政府論(下)[M].葉啟芳,瞿菊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
[11](英)洛 克.教育篇論[M].熊春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英)洛 克.人類理解論[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13](英)洛 克.理解能力指導散論[M].吳 棠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14](英)洛 克.政府論(上)[M].瞿菊農,葉啟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5](英)羅 素.哲學問題[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16](英)羅 素.西方哲學史[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17]渠敬東,王 楠.自由與教育——洛克與盧梭的教育哲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18]易紅郡.盧梭關于愛的教育的論述及其啟示[J].云夢學刊,2000(03).
[19]農玉紅,李茂君.論盧梭的自然觀[J].文學界(理論版),2010(08).
[20]張志偉.啟蒙主義的精神和它的難題 [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0(02).
[21]祝 賀.天性與習慣:盧梭的教育“矛盾” [J].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10(06).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