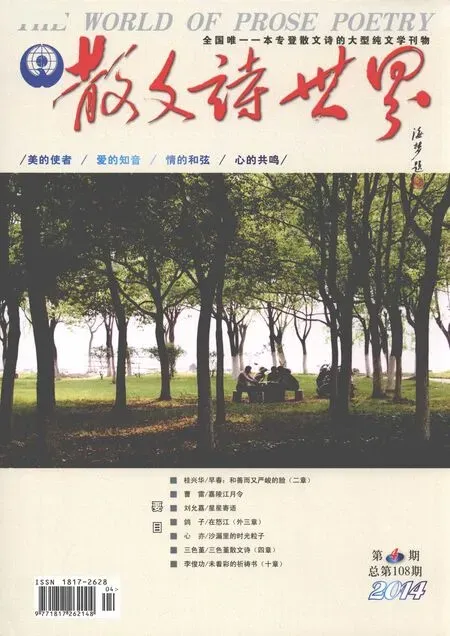未著彩的祈禱書 (十章)
河南 李俊功
未著彩的祈禱書 (十章)
一匹駿馬迎面而來
河南 李俊功
寒風途徑的路上,十二月的煙塵消散。
驚喜的鼓聲漸次放大。
一匹駿馬迎面而來。
濺起的冰霜和泥屑,破碎,滾落。給一分一秒的吉祥開辟通道。
在駿馬的奔馳中昂然抬頭。——時間充盈著無限的熱度。
原野仿佛跟緊它的腳步,迅跑。
誰將埋葬最后的憂傷、苦痛,從貧窮而致的自卑中出脫?
鼓翼的信念,乘著一匹奮蹄的駿馬迎面而來。
這個突然晴朗的天氣
一張白紙上寫下動感的冬天。
輕輕傳出神的絮語。
說著突然晴朗的天氣,透明陽光像鄉村明亮的慈善。
醒著的光芒,含滿了誰的望眼中晶瑩的淚水。
拿下心上的石頭,和寒夜的冰雪。
昨天、今天,以及隱藏的灰暗情節,全然照射,你頓然屬于陽光的輕松,開出日子的鮮花。
多少奇幻的場景在擴大?
天地一色,流動的溫暖,點燃了無數次萌芽的好夢。
這是嶄新的陽光,閃爍的長劍劃碎了久遠的迷霧。
能夠讀出通靈植物的甜香味,讀出妙曼音樂的七彩光。
學會包容,拒絕自私的有心人正把晴朗的陽光帶進長遠的腳步,
帶進遭遇冰霜的揚塵土路。
在西砦村看見五百年老槐樹
它孤獨,站在街道中央,磚垛和柴草一側。
臥著一只白狗,不動不吠。
仿佛上個世紀的一陣風。
晴天。
夏的熱浪在路上,悠長。
我撫摸傷痕累累的結疤,無言。
我撫摸朽腐的部分枝干,無言。
我在青翠的眾多綠葉上傾聽它奔跑的腳步,似乎颯颯有聲。
我看到它斜身,仍然指向當空的陽光。
競相閃爍
滿空星辰此時是我的,我仰望,它們俯身。
凝定,持久,內部的光芒,足夠看清我的一切。
我不比它們任何一顆明亮。
但我看見光,接受光,融化光,視作萬古經卷。
我要安放內心。我要按捺狂躁。阻止灰暗。
曠野,我的孤獨疑問,沉悶傷痛,更有我的蒼涼悲憤,我只需要這些冷靜的夜光,利劍一樣,佩戴我的獨思獨存。
競相閃爍,夜色不寒。
飽覽這無邊星輝,我鋒芒在握,頓然,心如曠野之廣大。
冬雨或者七步村
雨綿綿。
十一月的七步村被一首千古吟誦的絕句淋濕;
被遠道而來的一群人往謁曹植墓的探奇目光淋濕。
碑亭依然,文字清晰:明朝成化六年夏天,黃河決口,曹植墓所在的土岡被大水包圍。到了冬天,大水退去,土岡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洞穴,穴中有石門,從外面閂住,正中豎一石碑,上刻魏曹植之墓。
時間和話語,是這塊碑刻的所有證明。有關的事件凝結著一場薄霜,一層層揭開,有些難度。
誰能完整地想象出七步成詩中的一幕幕話劇,誰能傾聽到七步之下那些微土的連續呻吟?
所有讀碑的人仍然在讀,所有企圖破解謎團的心思仍然在醞釀,所有人的視線仍然在碑刻和陵墓之間游弋。往事本就如此,以及濫施的權力,經風歷雨,更多時候就是一堆不解的黃土。
涼意濃濃,如一個人蒼涼而匆促的一生,細雨密集,一層層鋪展在七步村一個隱秘的古墓上。
無聲,卻一再砸疼迎風的面龐。
似乎是悲惋的印痕。
無 題
其實心情是有標題的,正如遠野獨自品讀邈遠云空的粗大泡桐樹。
正如舞動大地,謝絕悲嘆的率性小草。
枝葉披覆:
袒露靈魂的彩衣。
——這些虛神靜思的樹木和花草。
我再一次看到它們!
窮人的海棠花
窮人的海棠花,照舊在春天里開放。
躲藏在破舊的瓦屋和庭院散亂的農具背后,像仍然躲藏在上幾個世紀。它們開放,卻不曾開口說出三里崗村繁華的張氏莊園勾檐斗角、御賜匾額、高樓亭榭和舞動彩緞在1966年一陣陣風暴的瞬間毀滅或消散。
以及無法復活眾人口上斷續的神話。
由于遺忘,造就了海棠樹年年的萌綠、綻放。
這兩株自京城貴人府邸移栽的植物,過去是狀元府的照耀,現在生長在雞鴨豬狗的糞便喂養的硬土里,生長在柴草的炊煙紛落的煙塵和兩位老年夫婦嗆出的連聲咳嗽和昏花的眼神里。
它們開著和300年前一樣的花朵,白色的花朵鑲著一絲絲紅色的花邊。
淡淡的香氣飄蕩在兩個老年夫婦粗布衣的皺褶,和甘受寂寞卻十分平靜的皺臉。
還有高堂之上摔碎的一片片印刻著各式鳥獸的瓦當和雕工殊異已經殘損的楠木花格子帷床,在陪伴著它們。
它們開在窮人的庭院,依然開著和300年前一樣的花朵。
一切皆成幻象,而兩株海棠樹顯得異常真實,像這家夫婦的貧窮一樣真實。
它們穿越三百年流云,守望著一家人的貧窮。可是,
沒有誰能阻止得了,窮人的海棠花,照舊在春天里的開放。
風中的琴韻
逝去的風聲有再來的時候,那跨越了一滴淚的大海,跨越了心情的幾度度無眠的夜。
昨日一只斷線的風箏,在奇幻的空中脫落。
她的玉石的面龐上閃著暗含的淚光。
苦衷是一塊原始的封土。撕碎的旦旦書信,在命運的波浪上起伏。
鏨子鑿空夢想。
如果斷裂的琴弦上有風聲嘯傲。如果腳步合拍于哭泣的琴韻。如果一席話是一只渡船。
在尋找。那個完整的自我。
聽到逾越心胸的一陣狂風。
把她壓抑的淚水吹散而去吧,
能夠細細打量她暗藏的善意和美好的眼神。
她有著干凈的身體,素凈的企望。
見 面
你孤獨,像一只瑟縮的冬天小鳥。
久已聽命于擺布的口,連聲說著不,說著出逃。天氣轉冷,你奔行而來,有淚,遠離哭泣,有恨,遠離狹隘。
苦礬澄清著愛。盈溢著。似乎冒著熱氣。
敢于透露的隱秘痛苦,多像燈光閃爍的西河路,一路伴行著敞亮與超脫。
把之前的苦難、負屈和恓惶歸零,什么也沒有,開辟你自己,
你終于能夠走出別人手指和嘴巴的壓力。走出一場情感的霧霾。
在持久地傾聽
俯身于苦累大地 堅執于等待
旱地的麥子 認定了土的命和土的深厚
需要幾場酣暢的雷聲
需要雷聲里的透雨漫流
我不是路過,我是故鄉的一株久旱的莊稼
我正經歷著和它們同樣的渴望,但遠涉一條與它們遙遠不同的路
閃電與貧窮是可以澆灌的水。它們也許品質相同,好似一畦畦意志里
種植的鐵的種子 悄然生發的
光的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