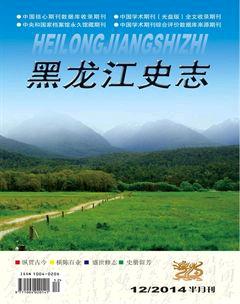淺議嘉靖時期閣權的畸變
李佳檜 耿濤
[摘 要]內閣是明史研究的焦點問題。嘉靖朝是明朝內閣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把握此時內閣的變化顯得格外重要。閣權的發展是有很強的時序性和延續性的,故此要著重把握閣權畸變的原因是什么,在畸變之時與其他權力的關聯及影響又是什么。
[關鍵詞]閣權;嘉靖;相權;皇權
內閣是明朝在特殊歷史時期和條件下的政治產物,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內閣首輔為首的“閣權”力量。嘉靖時期,閣權與皇權對立又統一的特點尤為明顯,在皇權的干涉下,閣權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對于閣權本身,對皇權,對明王朝的走向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本文由閣權的本身性質及其與皇權、相權的關系著手,深入挖掘其畸變的含義和影響。
一、閣權與內閣職能
首先我們要明確關于閣權的概念,以往我們常常將閣權看做是擁有的政治權力或者政治職能。然而,這種對“閣權”的解釋很難準確的描述出內閣固有的政治權力和政治職能,而針對于一些閣權的“有權”和“無權”的論調都是不足以昭示其本質的。那么,到底什么是閣權呢?在我看來閣權包括了協調皇權和下層官員之間真空地帶的中介功能;在皇權的授意下代為行使一部分權力的輔政功能;以皇權為中心進行一定的延伸和擴張的功能;針對國家內政的紕漏進行補過的功能。可以看出,閣權的范圍是皇權決定的。這注定了閣權是一個變量,在不同條件下有著不同的職能。相比較而言,內閣的政治職能則是比較固定的,因為內閣的政治職能是內閣制度誕生之后作為一個政治體制所本身固有的權力和責任,很明顯這些權力和責任也是皇權所賦予的。兩者在某種程度上有些類似但絕對不能等同論,因為閣權在有些時候更可以理解為內閣的權勢。
嘉靖早期,出現了皇權空虛的情況,楊廷和為首的閣臣開始了所謂的閣權擴張,內閣之權看似遠遠的蓋過了其本身的閣能,有人認為這是閣權的擴張的表現,但閣權的擴張是獲取了六部的行使權還是竊取了部分或者完整的皇帝的裁決權?對此問題是不能忽略皇權的的地位的,正所謂“政歸內閣”,如何歸?為何歸?這些都不能脫離皇權的存在單獨談論的,皇權為了維持自己穩固的地位會根據自己的需求和境地時刻調整閣能的范圍。故楊廷和的閣權在此時并不存在著真正意味上的擴張,因為內閣本身的閣能在限制著閣權的蔓延,我們姑且只能認識這種類似擴張的現象是一種閣權失控的表現。
閣能是閣權的上限和下限,閣權只有在這個范圍內才可以發揮著它應有的作用。如果超越了這個限制就會崩盤,這也是楊廷和閣權的曇花一現的原因。嘉靖時期內閣首輔毛紀曾說:“國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誠內閣職業也。”[1]表面上看內閣要“參預機務”,籌劃政事,但真正決策的是皇帝,而不是內閣,最大限度來講,內閣只是皇帝決裁的主要影響者。在這樣的閣能受限的情況下,閣權是無法得到發展的。
閣權要以閣能實現為基礎,原因很簡單,一旦權力失去了執行力,它的存在感就幾乎不存在了。而閣能的轉化又有著諸多因素的限制,內閣功能的轉換又不能完全按照預期的最佳方式進行轉化,它的轉化不僅有時序性還有漸進性。故此,在談論閣權或者閣能之時不能單獨片面的擇取一段歷史或者歷史的一點進行單獨討論,要對其發展的延展性和后續性進行分析。
閣權是明代極權統治下的產物和標識,但不代表他就代表著極權,相反,它被極權所閹割,受到打壓和排擠,其閣能的本質又限制著它必須服從于皇權,這種若即若離的奇特現象貫穿了嘉靖王朝乃至明王朝始末。
二、閣權與相權
關于閣權和相權的關系有人認為內閣制是洪武苛政之反正,是傳統宰相制的變相回歸。“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散其權于諸司,為后世慮至深遠矣,今之內閣,無宰相之名,而有其實,非高皇帝本意”。[2]嘉靖二十年,嘉靖帝在諭旨中直接稱呼夏言為“首輔”、“元臣”。甚至在朝臣奏疏等文書中,稱首輔為“丞相”、“宰相”。也有人認為閣權不過是“司內外制而已”,黃宗羲曾說道:“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必自援而后擬之,可謂有實乎?”那么閣權到底是相權的復活還是僅僅是一種類似于相權的畸變呢?嘉靖時期胡世寧說道:“不知自何年起,內閣自加隆重,凡職位在先第一人,群臣尊仰,稱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薦引,隨事附和,不敢異同。”[3]看起來閣權尤其是內閣首輔作為傳統相權的復歸是無可厚非的,但我們忽略了一個詞,“自加”,這說明內閣是在一點點的加強的,不像相權在一開始的地位就已經很高了,也就是說閣權是一直處于發展的道路上的,它無限的接近相權卻最終伴隨著大明的滅亡而壽終正寢,閣權最后也沒能達到相權的高度。只能說閣權是傳統相權意識的復蘇,而不是相權的復歸。
楊廷和集團權勢的膨脹,也就是政歸內閣,就是閣權復張的具體表現。但楊廷和本身并沒有能力和野心來駕馭如此龐大的閣權,很多人都慣于放大楊廷和閣權,卻忽略了國中無主不代表國家機器的不運行,楊廷和一己之力是無法阻止一個國家的正常運轉的。他更無法取代皇權的存在而單靠閣權的能力來操控一切。王其榘先生論道:“楊廷和等不是善于權衡的政治家,而是迂闊不化的儒生,仍然堅持如初,以至君臣之間的矛盾因此而日趨尖銳[4]”。楊的舉動更多展示的是他作為一個儒生的堅持,而不是體現了他的閣權有多么的龐大,楊廷和集團所采取的“維權”舉動,比如排擠,孤立,暗殺等等并不隸屬于閣權的范圍,而且這其中很多都不是合理的。故此與其說楊的閣權是相權不如說他的閣權由于己身利益的需求所產生的畸變現象。楊廷和現象的出現恰恰是正、嘉兩帝更易時產生了真空期,這才使得閣權很自然的填補上了皇權的空白。可以說這是一種無意中的“擴張”。而且就在楊集團勢力最輝煌的時候,所擁有的權力和以往的宰相還是差了很多。
皇權與相權一度是中央集權斗爭的焦點,但兩者是都無法完全攫取到中央的權力的,這兩者無論誰都會在過于集權后喪失穩定性從而失去本來的權力,故此兩者不得不形成了兩者互相拉鋸的局面。直到朱元璋廢相制,一度出現了空前的權力集中,但很快,內閣的出現填補了相權缺失后的空白,繼續了與皇權的拉鋸戰。但兩者在中央權力所占比重完全是不一樣的,閣權是遠遠不能與相權相比的。相權在某些時刻是可以脫離皇權而獨立存在的,然而閣權是一刻不能離開皇權的。內閣不過是皇權用來總攬大權的一個工具,而相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決策和行政機構。
三、閣權與皇權
隨著中國中央集權即皇權高度集中,內閣作為其物化的表現,并沒有完全按照皇權意愿行動,相反,反而給皇權以一定的束縛,這種互相牽制的局面在嘉靖朝十分明顯,但內閣的性質注定了它在行使它的政治權利時候必須要過問皇權,而皇權也需要這樣一個機構來幫助他實行它的權力,這種統一的局面于嘉靖朝亦十分明顯。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問題,離開了皇權,閣權的價值就不復存在,所以一些閣權取代皇權的論調我覺得是有失偏頗的。讓我們繼續以楊廷和為例,閣權對于皇權是有先天依附性的,所以在打壓嘉靖皇權的時候楊廷和并沒有僅僅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也是依靠了皇權的,只不過依靠的是過時的,極不可靠的孝宗皇權,楊廷和試圖在取得張太后以及宦官的聯合之后來遏制嘉靖,但很可惜,這個聯合是十分脆弱的。李洵先生認為楊廷和與舊貴族勢力的代表張太后的結合“只是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更多的是暫時性。”[5]隨著世宗即位,新繼皇權逐漸的穩定,楊的閣權勢力很快就受到了打壓,最后在大禮儀之后悻悻致仕。皇權也隨之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為什么說閣權強大和個人因素關聯很大呢?這也是和皇權密不可分的,在世宗解決了大禮儀事件之后,皇權開始由弱轉強,為了獎賞在大禮儀之爭幫助過世宗的張璁,桂萼等人,世宗對其大力提拔,其中張璁更是成為了新任的內閣首輔,這樣,以張璁為首的閣權勢力又開始復蘇。這一切的原因只是因為嘉靖皇帝的個人愛憎,這一點在嘉靖后期更為明顯。張璁得勢之后,嘉靖日益感到權相的崛起對其帶來的危害,夏言也就在此時得到了嘉靖的關注,在張璁倒臺之后,夏言自然而然的成為了嘉靖的頭號寵臣,亦成為了內閣首輔,后來的嚴嵩情況也大致相符。這就說明了一點,在皇權處于一個穩定的情況下,其對閣權的控制是絕對的,閣權是毫無抵抗力的,嘉靖時期首輔的更迭很明晰的解答了這一觀點。
臺灣學者林麗月先生認為:“嘉靖以后,內閣權力有急速的發展,發其端的是張璁,集大成的是張居正。”[6]這種高速的發展恰恰也是建立在對皇權的絕對服從之下的,內閣并沒有發揮其原有的政治功用,這本身就是一種畸形的發展。我們也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閣權強大的內涵是什么?閣權之所以會強大完全就是因為皇權的支持與許可,而大多數所謂的閣權擴張和發展不過是閣權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比如皇帝不上朝等等)部分的竊取了皇權,代皇帝執行權力。也就是說,無論閣權再怎么強大,它的權力范圍都是涵蓋在皇權的能力范圍之內的,這也注定了內閣作為皇權統治國家的一個政治工具的作用,也注定了閣權在發展的道路越來越脫離它本來的面目。
明孝宗曾經有言“吾不能自治,誰能治吾”,[7]這段話準確地概括了明代皇權的極度膨脹。李渡在《論明代監閣二元互制中樞行政體制》一文中認為:考察明代閣權與皇權的關系,主要應從兩個方面來加以把握和理解。第一,閣權就其權力性質而言,完全依屬于皇權。閣權只有通過皇權的批準或與皇權相結合才會具有政治功能,閣權不過是皇權的外延和擴張而已,這種權力屬性決定了內閣大學士對皇帝的政治依附關系。第二,內閣大學士通過“票擬”、“面吩”、“密揭”等形式,參與中樞決策,因而閣權在國家權力體制運作機制中體現了一定程度的決策權。但這種決策權在取得皇權的支持后,就可以影響甚至左右政局的發展。如萬歷初年,明神宗“虛己委居正”,“宮府一體”,閣權遂與皇權結為一體,張居正得以充分發揮“元輔”作用,推行其改革大計,因此閣權的主要政治功能是提高和強化專制主義皇權的統治效能。這段話深刻地揭示了內閣與皇權的內在統一性與皇權對內閣的絕對控制權。
在嘉靖不問朝政之時,閣權也沒有發展到“尾大不掉”之勢,這就是皇權發展到一個高峰的具體表現,這也充分說明了皇權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牢牢的把握了國家的行政、軍事、經濟大權,處于一種絕對主宰的存在。而內閣本身具備的補過功能日漸喪失,與皇權日趨合流的閣權隨著皇帝自律性的下降,更是促進了皇權的日益膨脹。有人說明亡于嘉靖,之所以這么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閣權與皇權關系的變化,皇權幾乎沒有了約束,前面也曾說過,權力的過于集中會喪失穩定性從而丟掉原本的權力,所以當中央集權崩盤之后,大明避不可免的走向了滅亡。
在多種因素的促使下,閣權脫離了預先的軌道,這種畸變的閣權也讓大明的發展愈加沉重。明初的那種“罷朝閑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的皇帝與閣臣和諧共處的氛圍已成為了海市蜃樓。閣權的畸變推動了極權統治的發展,也注定了其本身的可塑性、軟弱性和依附性。
綜觀上述,閣權的畸變對于明王朝來說無異于一個導火索,它對皇權制約性的下降使得皇權無限制的膨脹,為明的覆滅埋下了伏筆。閣權的畸變也不是一個瞬時的過程,是有著一個很長時間的積累的過程,其影響是有著時效性的。內閣在與皇權的斗爭中“失敗”了,不得已作出退步,無論這種畸形的權力形勢影響是什么,我們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離開了皇權,所謂的閣權也就不復存在了。而自嘉靖開始,閣權的畸變導致了中央權力機構十分不明確而且自相矛盾,這也許就是嘉靖直到明末政局不穩定的另一個因素。
參考文獻:
[1]徐溥《請視朝疏》,見《明臣奏議》卷8
[2]張廷玉《明史》卷210《趙錦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3]張萱《西園聞見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
[4]王其榘《明代內閣制度史》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85頁
[5]李洵《下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頁
[6]鄭欽仁等著《中國文化新論》制度篇《立國的宏規》(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版第107頁
[7]談遷《國榷》北京:中華書局1958
作者簡介:李佳檜(1989-)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人,女,漢族,歷史學在讀碩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化史,北京聯合大學;耿濤(1989-)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人,男,漢族,歷史學在讀碩士,研究方向:遼金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