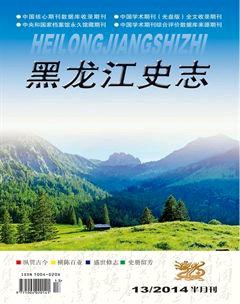“拮據”的“皇帝”婚禮
[摘 要]1922年12月1日溥儀舉行大婚典禮,當時媒體對此事大肆渲染,一時“宣統大婚”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媒體對于結婚當天情形的報道很多,可是輿論只看到光彩的表面,很少有人了解到“拮據”的溥儀籌錢的辛酸,他向民國政府討要積欠多年的“優待費”,變賣歷朝遺物寶物,通過別人救濟等來籌集婚禮費。作為一個“皇帝”,這應該是溥儀的不幸,可是他應該認識清楚當今的局勢,現在已經是民國了,他已經不是錦衣玉食的皇族,現在應該丟掉“皇帝”的外衣,安心做一個民國的公民。
[關鍵詞]溥儀;經費;優待條件;民國
近些年來,對溥儀的研究大多關注于出宮時候的他,對于溥儀在京時的第一次婚禮,大多只記述在著作當中,沒有單獨成篇。經作者對相關報紙的查閱,發現其中對于這次婚禮的報道相當豐富,本文嘗試談談民國媒體眼中溥儀的婚禮“盛況”。
一、被圈出的一后一妃
1922年12月1日(農歷10月13日)溥儀“皇帝”舉行婚禮,這一天北京城沉浸在一片喜慶的氣氛中,“好事者多拼一夜不眠,沿途趕看熱鬧”,“入京賀喜者甚眾”,清朝的遺老遺少齊聚北京。1922年3月13日《申報》報道:“溥儀決定聘榮源之女為正妻,端緒之女為妾,本年十一月結婚(十二日下午四鐘)”,溥儀一筆圈一后一妃。
1921年年初,溥儀剛過十五周歲,太妃和王公大臣們就把結婚一事提上日程,但是這對于溥儀來說只是成人的標志,經過這道手續,別人就不能把他像個孩子似的管束了。這次選后采取看照片的形式,經篩選,陽倉扎布之女、衡永之女、榮源之女和端恭之女成為皇后候選人。最后由溥儀親自圈定了一后一妃。
對于這次后妃選定,起初,“太妃為溥儀擇配也,萬薦其侄女為后。同時溥儀生母——載灃之妻亦以其侄女薦,雙方相持,太妃大怒”,經過多方調解,決定皇后由溥儀自擇。溥儀年少氣盛,且略識新文化之皮毛,“自言吾寧取貧家女重學識,不重門閥,于是遂選定散秩侍衛榮源之女。”太妃指的是端康太妃,福晉指的是敬懿太妃。可這件事據溥儀自己回憶,當時要“皇帝”“欽定”人選,溥儀看到照片第一眼相中端恭之女文繡,在文繡的照片上畫了一個圈后。端康太妃不滿意,理由是:“文繡家境貧寒,長得也不好,而她推薦的這個是個富戶,又長的很美”,隨后改成婉容,讓溥儀在婉容的照片上又畫了一個圈。這樣一來,敬懿太妃不同意了:皇上畫過圈的人,怎么能嫁給平民百姓呢?所以溥儀又在文繡的照片上畫了一個圈,就這樣溥儀一筆圈定了一后一妃:婉容為“皇后”,文繡為“淑妃”。
二、繁瑣的婚前禮儀
選定后妃以后,接下來便是這三大禮儀。三大禮儀的時間安排是:納采禮10月21日;大徵禮11月12日;冊封禮11月30日。
1、納采禮:即送定親禮。《大公報》報道:熱鬧的很。“是日之采禮秩序,大略如下:(一)侍衛官馬隊約六十匹,其裝束與現時陸軍軍官等,每伍約隔兩三步,按轡徐行;(二)大點儲備處,軍樂隊約有五六十人;(三)內務府軍樂隊兩隊;(四)黃緞繡金之清國龍旗兩面,縱橫約有一丈二尺;(五)彩亭十二個,均以黃綾繞之,亭之中有黃綾包兩三個;(六)誥敕亭兩個,內有誥敕數事,均以繡黃綾被之;(七)彩禮亭十二個;(八)大彩四個,其式樣與小彩亭略同;(九)良馬三匹,一系白色,飾以金雕鞍,其兩匹,均棕色,飾以銀雕鞍。”清朝侍衛和民國陸軍軍官,中西軍樂隊夾雜在其中,后有清朝龍旗迎風飄揚,“全無時代不同也”。
十一點鐘,“天使到門,榮公及其子在門外鵠立,樂隊在左邊侍立,其他中西音樂會樂隊則入內矣。清慶王手持一旌式之物,即圣旨也。到門,榮公等跪接,同時內城衛隊舉槍致敬,天使入內后,一切馬亭旗傘羊酒亦入內,少時天使出,仍持旌式之物以行,榮公等跪送,如儀時十一鐘二十分也”,“天使”指溥儀的儀仗隊。清朝跪拜禮、衛隊舉槍致敬、中西音樂隊奏樂,真是中西合璧,好不熱鬧。
2、大徵禮。“這項禮節也是送禮物給新娘和她的家人,不過這次禮物較納采禮更為貴重。送給皇后的是黃金一百兩、白銀一萬兩、金茶器一、銀茶器二、銀碗二、緞二百匹、配備鞍轡的馬二匹。送給皇后父母的禮物是:黃金四十兩、白銀四千兩、金茶器一、銀茶器一、緞四十匹、布一百匹、配備鞍轡的馬二匹、朝服二襲、冬服二襲、帶一。送給皇后兩個弟弟的禮物(其中一個只十歲)是:緞八匹、布十六匹及文房四寶一套。后邸的仆役也共占‘恩澤,賞四百元給他們去分配。”禮節和納采禮差不多,只是禮更貴重。
3、冊立禮。上午巳時,“先由內府華將皇后名號,鐫制于金冊上,更鑄金寶一顆。(即印)屆期請清帝升乾清宮寶座,御覽冊賓,頒降冊立皇后恩旨一道。派親王或內府大員二人,為正副欽使,恭將冊寶,送至后邸。”“皇帝”“欽使”將金冊送到皇后的府上,擁有金冊金寶后,婉容就成了真正的“皇后”。這是三個禮儀當中最隆重的一個。
這些禮儀,對平頭百姓來說可謂盛況,但是相對于以前的皇帝,溥儀的婚禮未免簡單了許多。
三、隆重的婚禮
11月30日大婚吉期。這天黎明文繡先入宮,晨三點多,迎親隊出發,中西混搭的隊伍又一次出現在北京城。市民們相互招喚著:“走,瞧小皇上娶娘娘去!”連電影也把溥儀結婚當作廣告,以招徠觀眾。迎親隊伍到達“后邸”時,“皇后”的父親、兄弟已經在門口等著了,“后之父兄隨大使后入內,鳳輿亦一同入內,約十五分鐘之久,即出帽兒胡同東口”。晨四點多,“鳳輿入宮,各儀仗兩旁分立……鳳輿抬入,自兩路北行,入乾清宮。”“皇后”降輿后,先越過一個大火盆,然后由福晉等攙扶前往坤寧宮,在坤寧宮前又越過一付馬鞍,然后入宮至東暖閣與早就在此的溥儀舉行典禮。二人坐到“龍鳳喜床”上,喝交杯酒,吃子孫餑餑,舉行“合巹宴”:主菜燕窩,用它擺字,兩個大金碗,一碗是燕窩紅雙喜字金絲鴨,一碗是燕窩紅雙喜字八仙鴨;四個大金盤,一盤是燕窩龍字拌熏雞絲,一盤是燕窩鳳字金銀肘花,一盤是燕窩呈字五香雞,一盤是燕窩祥字婚姻占樣如意。之后二人入洞房。
12月3日乾清宮受賀。滿蒙王公、內務府大臣、內廷行走大臣等清朝遺老穿清制禮服,如驚蟄后的蟲子成群飛向北京;民國政府的文武官吏則穿民國大禮服前來祝賀,另外還有外國公使夾雜在其中。他們中間有些是代表政府的,有些是懷著依戀舊主的心情,以私人身分前來叩賀的。鄭孝胥在日記中記載“12月1日,皇上大婚吉日”,12月3日午后,“王聘三,陳容民,宋澄之,章一山,王雪澄,余堯衢,吳寬仲來,行大婚慶賀禮,靜海諸生王俊卿,陳楷亦來,隨同行禮。”據溥儀回憶當時“民國派來總統府侍從武官蔭昌……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剛才那是代表民國的,現在奴才自己給皇上行禮。說吧,跪在地上磕起頭來。”這真是有些滑稽。
這天溥儀收到的賀禮,內務府印行的“紅冊”記載,有王公、宗室、帝師、內務府官員和舊臣,還有民國要人、社會名流等。如大總統黎元洪在紅貼上寫:“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贈宣統大皇帝。”禮物共八件:瑯器4件,綢緞2件,帳1件,對聯1副——“漢瓦當文,延年益壽;周銅盤銘,富貴吉祥。”前總統徐世昌送賀禮2萬元,還有許多貴重物品,包括28件珍貴瓷器、一張名貴的龍鳳地毯。基督將軍馮玉祥送了一柄白玉大喜如意。……“文圣”康有為送銀元1000元和磨色玉屏、金屏、拿破侖婚禮時用的硝石蝶以及一幅親筆對聯:“八國衣冠瞻玉步,九天日月耀金臺”。溥儀的堂兄弟、英文伴讀溥佳送一輛自行車等。
四、排場背后的“拮據”
婚禮的場面很是壯觀,可是排場背后的“拮據”只有溥儀自己清楚。1922年12月3日“曹锳來京嫁女,妝奩不亞溥宅”。民國交通總長葉恭綽去年嫁女,“妝奩至一百五十二抬之多,而此次清室則只有六十四也”。光緒大婚時典禮經費四百萬元,其后不足加增至五百萬元。溥儀之貴還不如民國官員,更比不上他的祖輩。當時遺老回憶:“溥儀所行的系清朝的末運,結婚又在下了臺之后,當時不同往日,就限定他的所謂內務府極力撙節,不得超過三十萬元”。可是不管是五十萬還是三十萬,對于今日的溥儀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數目。那么他的婚禮經費從何而來呢?
大婚吉期剛定下的時候,大總統徐世昌在位,同意給予經費支持。但是直奉戰爭爆發,總統徐世昌被逼退居天津,溥儀大婚的經費就此擱置。黎元洪上臺后,對這位“遜帝”大婚依然給予支持。但是當溥儀向他討要“優待費”的時候,民國財政部對于這一要求發來一封頗含歉意地信,說“經費實在困難,以致優待費不能發足,現在為助大婚,特意從關稅內撥出十萬元來,其中兩萬,算是民國賀禮”。(優待條件第二條曰“大清皇帝辭位之后,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后改為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溥儀以為自己有每年四百萬兩的“優待費”為護身符,結婚經費不是問題,直到此時他才明白“護身符”沒有用,北洋政府的國庫比起內務府的府庫好不到哪兒去。
大規模的婚禮籌備工作已經收不住轡頭,溥儀不得不另覓它法:向銀行抵押宮中珍貴文物。這是由內務府堂郎中鐘凱提出的。金盤、金瓶、金盒、金碗、金壺、金手爐、金如意、金葫蘆以及珍珠、翡翠和珊瑚制品等共千余件,裝了40多箱向英國匯豐銀行抵押換錢。一開始說是抵押,后來因為超期變成了“押死”。報紙對于“清室”抵押寶物籌辦大婚經費大肆批評,但是這恰恰反映了“小皇帝”生活的拮據。
遺老遺少效忠進貢,七湊八搭加起來有二十多萬元。這些人里面有姓名可舉得,如徐世昌二萬元,張作霖一萬元,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各一萬元,張勛一萬元,陳伯陶一萬元,陳望曾、戴培基、陳汝南、羅元燮各一千元,廬寶鑒、蘇志綱各五百元,陳應科二百元,曹受佩、賴際熙、馮溥光、章果各一百元(陳望曾至章果十一人,共五千六百元,是托陳伯陶由香港帶京代交的)。還有陳夔龍、李經義、李經邁、劉翰怡等,本來各送一萬元,后來不知怎樣,每人減半,只送了五千元。最奇的,有一位商人梁創,系永安公司的總理,不知怎樣心血來潮,也托陳伯陶代送了五百元。
當宮中還沉浸在婚禮的歡樂中的時候,忽然傳來了國會議員鄧元彭提出取消“優待條件”的噩耗。鄧提出:中華民國為共和國體,一切人權平等,再無特殊階級。“以民國而又帝室,已為憲法上之變例”“同一國家之內,固不容有二種之最高尊高”,“優待條件”允許溥儀退位后,不廢尊號,但是“帝王二字,乃代表一國之尊稱,而國家須有土地人民主權三要素始算成立,試問今日之皇室能有乎?論土不過宮禁,論人不過家族,論權不過庭幃,國家資格既失,即帝王之稱號當廢矣”,取消“優待條件”。既然“優待條件”從來沒有被很好的執行,所以取不取消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溥儀“皇帝”可以認識到這樣一種事實:相對于“拮據”的“皇帝”生活,不如順應世界潮流,放棄帝王的生活,做一個普通的民國公民。
參考文獻:
市隱:《溥儀婚禮紀》,上海《申報》,1922年12月5日。
《溥儀婚禮紀》,上海《申報》,1922年12月3日。
《宣統帝婚禮》,《盛京時報》,1922年12月8日。
《清帝納采》,天津《大公報》,1922年11月15日。
《清帝納采志盛》,《盛京時報》,1922年10月25日。
《大婚寫真》,天津《大公報》,1922年12月4日。
《清帝冊后》,天津《大公報》,1922年11月18日。
愛新覺羅·溥儀著:《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1964年3月。
張驥良著:《溥儀終結一個時代的人》,北京市:中國盲文出版社,2008年。
莊士敦著,秦仲龢譯:《紫禁城的黃昏》,李敖出版社,1988年4月30日。
莊建平著:《稗海精粹——落日殘照紫禁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
孫喆甡著:《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傳》,北京·華文出版社,1990年。
作者簡介:馬少萍(1989-),女,河南省濮陽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2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