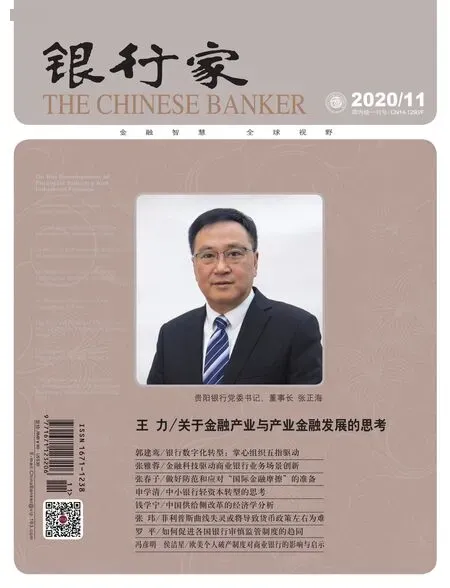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構想
熊園

隨著中國地位的不斷提升,經過多年的努力,人民幣國際化已有了長足進展:截至2014年上半年,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規模突破12萬億元;2013年年末起,人民幣持續位居全球十大支付貨幣之列,并超越歐元成為傳統貿易金融領域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貨幣;覆蓋香港、新加坡、倫敦、法蘭克福、盧森堡、巴黎和悉尼等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全球性人民幣離岸中心網絡雛形初現。盡管如此,在我國金融改革尚未完成、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并不完善、資本項目開放進程相對較慢的情形下,人民幣國際化之路依然任重而道遠。當前,世界經濟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依然較多,中國經濟也處于改革攻堅的新階段,面對國際國內經濟的新形勢,需要從國家戰略高度認識人民幣國際化問題,順應國際貨幣格局的演變規律,處理好與資本項目開放的關系,并尋求人民幣國際化路徑的新突破。
人民幣國際化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推手
以史為鏡,可知興亡。昔日英國和當今美國的崛起之路,無不伴隨著貨幣的國際化。理論和實踐也已證明,一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很大意義上是一國國際地位的表征。因此,中國要想獲得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強國地位,欲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應將人民幣國際化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并統籌好人民幣國際化與“走出去”戰略、“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等其他國家戰略之間的協同效應。此外,從國家戰略高度認識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也是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內在要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戰略部署,明確指出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的可兌換程度,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
人民幣國際化需順應國際貨幣格局的演變規律
回顧國際貨幣格局的演變歷程可知,一國貨幣地位與其經濟實力休戚相關。強大的經濟實力是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先決條件,國際貨幣格局變化過程背后是長時期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但兩者也并非嚴格的對應關系。美國經濟早在19世紀80年代開始就已經開始反超英國,并在20世紀初全面超越英國,而美元直到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之后才最終取代英鎊,奠定其霸主地位。經濟實力之外,政治、軍事、科技等是影響國際貨幣格局的關鍵因素。看美元的經歷,正是依托政治、軍事和科技所建立起來的美國金融霸權,為美元取代英鎊、走向全世界增加了重要砝碼:兩次世界大戰使美國聚集了大量世界財富,奠定了美元背后的經濟基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為構建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提供了制度支撐;科學技術的創新和信息革命的發展,為美元經濟和美國的金融市場提供了技術載體。
至于人民幣,中國外匯儲備規模自2006年起一直居全球之首,經濟總量也自2010年以來位列世界第二,但相比美國等發達國家,我國的政治、軍事和科技的影響力還存在很大差距。同時,我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還很薄弱,集中體現在:全球的股票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股指期貨市場、外匯交易市場和債券市場等依舊是歐美國家保持著絕對領先;國際信用評級體系、支付清算體系、國際信用卡組織、國際清算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決定全球金融規則的機構仍然由歐美國家所把持。由此來看,人民幣國際化的外部條件還遠不成熟,人民幣要想在國際貨幣格局“站穩腳跟”,還需要付出很大努力。
處理好人民幣國際化與資本項目開放的關系
一國貨幣欲實現國際化,資本項目開放是必然的要求,但對于資本項目開放的程度一直分歧較大。國際經濟學界迄今為止,未能從理論上和經驗上證明,資本項目的完全開放對發展中國家利大于弊。英鎊、美元、日元和歐元的發展歷程也表明,貨幣國際化雖然伴隨著資本項目的逐步開放,但并不意味著資本項目必須完全自由化。IMF(2012)統計的192個成員國中,基本上沒有一個國家的資本賬戶是完全開放的,其中有大約75%的國家對資本市場的證券交易、直接投資、不動產交易施加管制,并有專用于商業銀行和其他信貸機構以及機構投資者的特別條款,50%以上的國家對貨幣市場工具、集體投資類證券以及金融信貸施加管制。就連公認的資本項目開放度最高的國家(諸如美國),在不少資本子項目下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限制。
至于人民幣,自1994年以來,我國一直堅持對資本項目漸進開放的方針,有計劃、有步驟地審慎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后,開放步伐有所加快。依據IMF2011年編制的《匯兌安排與匯兌限制年報》,從其中劃分的七大類共40子項(七大類即指資本和貨幣市場工具交易、衍生品及其他工具交易、信貸工具交易、直接投資、直接投資清盤、房地產交易和個人資本交易,我國已經放開的集中在資本市場證券、貨幣市場工具、商業信貸、金融信貸等子項目。其中,基本可兌換指有所限制,但限制較為寬松,經登記或核準即可完成兌換,部分可兌換指存在嚴格準入限制或額度控制)的資本項目來看,截至2013年年末,人民幣資本項目實現了基本可兌換和部分可兌換以上的項目,占全部交易項目的90%,不可兌換項目有四項,僅占10%。隨著資本項目的不斷開放,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得到了極大提升。然而,針對當前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和政治、經濟與金融形勢,當前我國不斷顯現的地方債、房地產泡沫、企業債、影子銀行等一系列金融風險事件,以及匯率和利率形成機制短期內尚難有效形成的事實,資本項目開放作為中國金融體制改革中最為敏感、風險最大的改革,如何穩妥推進資本項目開放變得十分關鍵。我國決策層應提高認識、保持警惕,當前形勢和未來一段時期內都不應追求過快的資本項目開放,應在保障經濟金融安全的基礎上,謹慎對待資本項目開放。
人民幣國際化路徑應尋求新突破
關于人民幣國際化路徑,學界、業界和政界普遍認為應遵循兩個“三步走”策略,一是功能上,采取“計價貨幣-投資貨幣-國際儲備貨幣”;二是區域上,采取“周邊化貨幣-區域化貨幣-全球化貨幣”。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初期階段而言,選擇這一路徑的確為明智之舉。然而,在當前國際貨幣格局正經歷重構之際,人民幣國際化理應尋求新的突破口。
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具備了基本的現實基礎
第一,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美國的量化寬松(QE)政策導致全球經濟的持續動蕩,一再表明當前以美元作為單一主權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已經不再適應全球經濟發展的現狀,多元化國際儲備貨幣已是大勢所趨。第二,我國經濟持續了30多年的快速增長,2010年起已經連續四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經濟形勢錯綜復雜、發達國家經濟復蘇艱難曲折、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放緩的情形下,雖然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但增長動力依然十足,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賴程度將不斷加深,對人民幣的需求將日益旺盛,人民幣成為商業、經濟和金融儲備貨幣的重要性越發迫切。第三,匯率具備足夠彈性和資本項目可兌換,是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重要前提。近幾年來,我國政府一系列的政策安排為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奠定了制度基礎。201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改2005年以來持續升值態勢,雙向波動彈性顯著增強;擴大人民幣跨境使用、利率市場化、滬港通等金融改革舉措也正加速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2008年起,我國央行先后與韓國、英格蘭、歐盟等25個國家或地區貨幣當局簽署的近3萬億元人民幣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證明,人民幣儲備貨幣已經具備了一定規模,這為人民幣最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積累了制度經驗。
值得指出的是,2014年9月12日,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宣布英擬發行人民幣計價的非中國主權債券,計劃規模或達20億元人民幣,并將籌集資金用于英國外匯儲備,這意味著首支人民幣國債即將登陸西方國家。鑒于英國在全球金融系統的重要地位,此舉或將引發示范效應,歐元區、瑞士等其他西方發達經濟體的類似舉措值得期待。這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無疑是重大利好,不但將豐富人民幣的投資渠道和提升人民幣的投資功能,更為重要的是,為人民幣最終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奠定了堅實基礎。
歐洲成為人民幣國際化路徑的突破口
近兩年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明顯提速,其中一個突出特點便是“歐洲元素”頻頻閃現:2013年6月和10月,中國人民銀行先后與英格蘭央行、歐央行簽署貨幣互換協議;歐洲各大金融中心紛紛角逐人民幣離岸中心,2014年法蘭克福、倫敦、盧森堡先后獲準設立人民幣業務清算行,中法雙方也同意就“在巴黎建立人民幣清算和結算安排”進行討論;2014年6月中英宣布人民幣和英鎊可直接兌換,3個月后再次宣布英國將發行人民幣國債;2014年9月,人民幣歐元直接交易正式啟動等。
人民幣在歐洲之所以成為搶手的“香餑餑”,是因為隨著中歐政治互信水平的不斷提高和中歐經貿聯系的日益密切,歐洲的人民幣業務變得大有可為。截至2013年年底,歐盟已經連續10年保持了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且連續三年雙邊貿易額超過5000億美元,中歐亦提出了到2020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萬億美元的目標。而持續疲軟的歐洲經濟,也有賴于中國來加以提振。另外近年來,美國越來越多應用針對金融交易的禁令,利用長臂管轄權頻頻制裁各國金融機構,也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的趨勢。2014年6月30日,美國司法部對法國巴黎銀行處以89.7億美元的巨額罰款(該行被指控2002年至2012年期間為遭受美國制裁的蘇丹、伊朗和古巴三個國家轉移了上百億美元資金),或將成為歐元區“去美元化”的導火索。其中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7月7日召開的歐盟財長會議上,如何提升歐元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問題首次被列為議題;而2014年9月30日,人民幣歐元實現直接交易,在某種意義上或許也是歐盟對美國的有力回應。事實上,自1999年元旦正式流通以來,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并成為了全球第二大貨幣,也是當前美元霸主地位的最有力挑戰者。但經過了近15年的發展,歐元并未對美元構成實質性的“威脅”,世界上大部分跨境貿易仍是以美元計價,全球央行的儲備中美元資產占比超過六成,外匯市場中涉及美元的交易也高達80%。因此,在歐洲“去美元化”的過程中,人民幣在歐洲將迎來新機會。
(作者單位:中國工商銀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后流動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