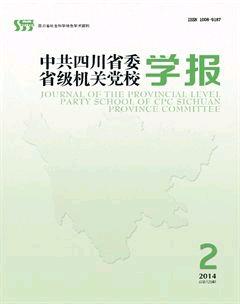社會治理模式變革:基于“和合思想”的思考
〔作者簡介〕
李豐,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講師,博士, 江蘇 南京 210046。
〔摘要〕在前工業社會階段的社會治理中,政府與社會之間是一種統治與被統治的矛盾對抗關系;在工業社會階段的社會治理中,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在形式上是同一的,而現實中則是分立甚至是對抗的。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時代背景下,我們需要建構起一種能包容差異性和同一性的合作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的和合思想,是一種既追求同一性又包容差異性的思想,它強調通過對差異性與同一性的承認和超越來形成新的和合體,這一思想對于合作型社會治理模式的建構與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在思想層面具有明顯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中心邊緣結構;和合思想;合作治理;服務型政府;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D5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14)04-0044-06
“和合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一種文化精神,它不僅能從一個方面分析中心-邊緣結構的社會治理模式失靈的原因,還能夠啟發社會治理模式的變革,進而建構起新的社會治理模式。中心-邊緣結構的社會治理模式,在本質上是一個機械、封閉的結構,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過程中,機械、封閉的特征正是中心-邊緣結構的社會治理模式失靈的根源。和合思想作為一個能夠包容并超越差異性和同一性的思想,具有明顯的開放性,按照和合思想的主張建構起來的將是一種超越“分化觀念”的多元主體合作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
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
在《左傳》所載晏子與齊景公的對話中,景公問晏子:“和與同異乎?”晏子答道:“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執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左傳·昭公二十年》)。在晏子看來,“和”是包含著差別與矛盾的“同”,就像調湯一樣,需要將各種不同味道的食材、作料加以調和,才能成為美味。同時,晏子還將“和羹”的道理引入政治關系之中,認為君臣之間也應該也要有不同的政見來調和治理,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政治清明的目的。可見“和”是一個包含著差異與矛盾,甚至是沖突的辨證統一體。《國語·鄭語》也有史伯關于“和”與“同”的論言,史伯指出:“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在這段論述中,史伯講出了“和”的本質——不同事物之間的相互調和、補充,而不是去除差異后的機械同一。此外,史伯的論言中還包含著實現“和”的方法,即“以他平他”。
《左傳》和《國語》中所包含的“和同”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的先導,影響著其后的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在繼承了史伯與晏子的和同論的基礎上,孔子提出了“和為貴”的思想。他認為:“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在孔子的思想中,“和”既是政治原則,也是人際關系原則。在孔子之后,孟子和荀子繼承發揚了儒家的和合思想。孟子指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在戰事頻繁的戰國時代,要想在群雄紛爭的局勢中立于不敗之地,孟子認為應該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等條件,而“人和”在此三條件中又處于最重要的位置。荀子作為先秦末代儒家,他認為:“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天論》)“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荀子·禮論》)在荀子看來,世間萬物千差萬別,它們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正是出于“和合”的緣故。通過以上分析可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所謂“和合”,就是在自然界、社會、人際關系、心靈和人類文明等諸領域中,有形的和無形的事物之間相互沖突與融合,并最終生成新的事物、生命和關系的過程。
和合思想是貫穿整個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一條思想線索,而非某家某派所特有的。儒家學說在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占據著很大的一部分,以至于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僅僅體現在儒家學說里,是儒家學說特有的思想內容。與這種看法不同,有許多學者也認為和合思想不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某一家某一派的思想。張立文教授就認為:“中華民族的基本文化精神,便是和合或合和,它不是某家或某派的文化精神,而是涵攝儒、道、墨、法、陰陽、釋各家各派的普遍的文化精神。”〔1〕所不同的是“儒家從差別中(社會有等級)求和合,道家從人與自然的分別中求和合,佛學從因緣中求和合,墨家從兼愛中求和合,陰陽學從對立中求和合,法家從守法中求和合,名家從離堅白與合同異中求和合。”〔2〕可見,和合思想在先秦的諸子百家中都有體現,而非專屬于儒家。當然,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總的稱謂,而在實際的研究工作中,絕大部分的學者是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一具體方面或某一具體視角來進行研究的。比如:錢穆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中”,但這個“中”所指的不是折中,“所謂‘不偏之謂中,不偏在這邊,也不偏在那邊,這一個‘大中,是全體……,是一個‘大中至正之中,是一個大局面全體之中。”〔3〕張岱年從哲學的高度出發進行研究,認為中國哲學有六個特色,其中三個為:合行知、一天人、同真善。〔4〕不難看出,在這些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中,雖然研究者們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學科和不同范圍來進行研究,但其中都包含著對“和合思想”的不同表述,這表明“和合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和合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我們今天研究它是為了更好地繼承它、發揚它以及運用它。因此,在當今的社會條件下來審視中國傳統文化時,我們需要有一個發展的觀念,在動態的圖式中來理解中國傳統文化。進一步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需要以中國傳統文化的“轉生”為前提。“這種轉生,是中國傳統文化創造性再生的延續,而不是傳統文化原封不動的單傳;它內在于中國傳統文化人文精神的蘊涵,又超越中國傳統文化人文精神固有的意蘊。”〔5〕為此,中國學者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精神的研究而形成了一門學科——和合學。“所謂和合學,是指在研究自然、社會、人際、人自身心靈及不同文明中存在的和合現象,與以和合的義理為依歸,以及既涵攝又超越沖突、融合的學問。”〔6〕從對和合學的涵義的定義中可知,它是以社會中各領域存在的沖突與融合現象為研究對象,并在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超越的方法與途徑,進而實現推進社會發展的目的。
二、社會治理失靈的思想根源
根據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水平,我們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所走過的歷程分為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階段。前工業社會是一個物質貧乏的社會,人類對自然的認識還處于覺識甚至崇拜的水平上,只能靠使用簡單的技術和對自然資源的直接利用來維持生存。同時在前工業社會階段,家族作為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個人被淹沒在強大的家族體系中,社會呈現出來的是一副未分化的混沌面孔。與社會混沌一體的狀態相對應,社會治理模式與政府行政體制之間也呈現出一種重合的關系,政府體系就是社會治理體系,主要發揮著統治的職能。在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中,政府通過對權力的壟斷來對社會進行統治,除了政府之外的其他社會主體是作為被統治的一方而存在的。前工業社會階段的經濟形態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這種經濟形態中土地是最為重要的生產資料,人們的生產、生活都依附于土地之上。然而,前工業社會中的土地是統治階級的私人財產,主要控制在統治集團的手中。如此一來,統治集團通過對土地的控制而實現了對社會的控制,最終使得人們對土地的依附轉換成了對人——統治者——的依附。從本質上看,前工業社會的社會依附關系是一種充滿張力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此外,我們知道在前工業社會的社會關系中,依據身份的貴賤高低將社會分為若干等級,不同的等級之間有著明顯而確定的邊界,由于這種等級差異而使得——在統治集團內部的不同層級之間是一種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在統治集團與社會之間是一種“異己”的矛盾關系。因此,在統治型的社會治理模式中,政府與社會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和沖突,或者說差異和沖突是它們之間的主要關系。
隨著人類社會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在“主權在民”思想的基礎上,人們建構起了政府壟斷的單中心社會治理模式。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身份差序逐漸被權利平等所代替,人們之間不再是一種高低有別的等級關系,在形式上人人平等。同時,在人民主權思想的指導下,人們通過社會契約中的委托-代理過程創立了得到公認的政府。加之人類社會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被分化為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和日常生活領域,政府成了公共領域的代表并承擔者社會治理的功能。所以,在工業社會的社會治理模式中,人民在形式上擁有主權,在實際上則是政府掌握了社會的治權而成為唯一的社會治理主體,這就造成一種局面——人民和政府之間在形式上是統一的,而在現實的社會治理過程中政府則處于治理體系的中心,人民處于邊緣。如此看來,在工業社會的社會治理體系中,政府與社會之間在形式上是融合統一的,而在實際上卻是分立甚至是對立的。
毫無疑問,中心-邊緣結構的社會治理模式的建立,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動了工業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公共行政學作為一個學科產生以后,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非常了不起的貢獻。在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西方國家爆發過幾次危機,這些危機在中心-邊緣結構的社會治理框架內都得到了比較有效的化解。但是,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面對社會發展過程中所涌現出來的危機,政府顯得有些應接不暇,社會不可治理的問題日益明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擴散就是很好的佐證。之所以這樣,就是因為西方國家沒有擺脫工業社會通過踐行形式理性來追求社會的同一性的思維模式。眾所周知,自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在社會分化的過程中完成的,面對社會分化的事實,管理行政通過對科技理性、形式理性的絕對推崇來追求抽象的同一性,使社會在一切方面都向形式理性靠攏,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導致社會在整體上表現出一種刻板的一致性,在這種情況下所建立起來的中心-邊緣式的社會治理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呈現出形式同一的情況。
啟蒙運動的發生,解構了前工業社會對個人的束縛和羈絆,人類社會從權力主導的階段向權力至上的階段進化。啟蒙運動是對工業社會的啟蒙,它是人類社會從前工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工業化開始前的清道工作。經過啟蒙運動的洗禮,天賦人權的思想得到普遍接受與宣揚,一種“人類中心主義”的精神受到高度的贊頌,一切變化與進步都要服務于人的權利、價值、尊嚴和追求幸福的需要。以至于有人認為現代性具有一種宗教性,其“集中表現為人定勝天的進步觀念和人權。進步觀和人權意味著人的神權,意味著人決心把人變成神,盡管在現實上尚未實現為神,但已經在概念上先行自詡為神,而且以概念作為抵押而預支了神權”〔7〕。因此,在啟蒙運動后的工業化過程中,進步思想成為人們普遍的信仰,形式理性、工具理性作為啟蒙理性貫穿其中。“由于工具理性只關心實用的目的,以及實現目的手段;它把事實與價值割裂開來,消除了思維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屈從于現實并為現實辯護。”〔8〕因此,當科學技術成為社會進步的衡量標準時,人們模糊了對科學技術本來面目的認識,不假思索地將其作為生活的目的甚至全部。科學技術的異化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隨之改變——將自己和他人都看做是工具,結果將科學技術神話、將人物化。啟蒙運動本來就是一場要將人類從恐懼和蒙昧中拯救出來的運動,但隨著啟蒙理性的發展和擴張,技術理性壓抑了價值理性和人文理性,并成為支配人類的強大力量,滲入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正如霍克海姆(M.Max Horkheimer)所說:“技術上的合理性,就是統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異化的社會的強制性。”〔8〕“權利和自由在工業社會的形成時期和早起階段曾是十分關鍵的因素,但現在它們卻正在喪失其傳統的理論基礎和內容而服從于這個社會的更高階段。”〔9〕可見,啟蒙運動之后,隨著人類向工業文明的全速挺進,科學技術變成了統治者人們的強大力量,啟蒙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非理性。而這種“非理性”集中體現在社會、人、思想以及人際關系的形式化和單向度化。
不可否認,工業文明事實上在很多的方面都遠遠地優越于前工業文明,而這一切正得益于對技術理性的推崇與深信不疑。啟蒙運動激活了人的創造性,而工具理性和技術文化迅速發展,推動著人類從落后的農業文明進入發達的工業文明。在工業文明中,科學的管理和社會分工大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人類第一次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豐富的食物、舒適的樓房、發達的醫療、先進的交通工具、神奇多彩的電子世界等等,這一切都得益于技術理性的優異表現。然而,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后工業化浪潮使得社會矛盾和沖突呈現出倍增的狀況,在國與國之間、地區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自身以及不同的文化模式之間……各種矛盾與沖突不斷涌現,社會表現出高度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人類要想繼續很好地生活或生存下去,不可能通過單方面地強調沖突或者同一而得以實現。一方面,由于社會的深度分化,整個世界的復雜化、多樣化已是不爭的事實,若一味地突出沖突與矛盾,人們將有可能在沖突和矛盾的裹挾下走向災難,特別是隨著生化武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發明和運用,其結果對發生沖突的任何一方都是毀滅性的,最終有可能會導致人類文明的倒退甚至世界的滅亡。另一方面,世界本身呈現出的多元化、復雜化與個性化是無法回避的事實,客觀上不具有通過消除矛盾、差異來獲得全面的同一性,進而達到消除沖突的可能性,所以,通過只強調同一而回避矛盾與差異來追求社會發展的思想日益顯得不合時宜。
同樣的道理,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時代背景下,工業文明那種化繁為簡的思維以及形式理性主導下的社會治理模式已經不適應高度復雜和高度不確定的社會現實,使得社會風險四伏、危機頻發。其根源就在于既有的社會治理模式是通過刻意地回避與剔出社會的復雜性和多元性來追求機械的同一性,當社會發展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的情況下,社會治理的思維模式仍然停留在工業社會的話語體系當中,沒有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改變。鑒于這種情況,在后工業化浪潮正洶涌跌宕的當下,我們關于社會治理模式的思考必須要擺脫工業社會話語體系的束縛。進一步說,我們必須要跳出近代以來追求形式理性、科學理性的思維模式去尋求社會治理模式的變革。
三、和合思想對社會治理模式變革的啟示
正如羅伯特·達爾所言:“每個民族國家都包含著許多歷史事件、創傷、失敗和成功的結果。這些結果反過來創立了特殊的習慣、習俗、制度化和行為方式、世界觀甚至民族心理。人們不能認為公共行政學能夠擺脫這些條件作用的影響,或者認為它能以某種方式獨立于和隔離于它在其中發展起來的文化環境和社會環境。”〔10〕在人類社會化工業化的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合思想正具有這樣的思想作用。與西方文化重分析思維的傳統不同,“東方文化基礎的綜合的思維模式,承認整體概念和普遍聯系,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人與自然為一整體,人與其他動物都包含在這個整體之中。”〔11〕而且這種綜合的思維模式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則是普遍存在的,和合精神就是其焦點性的呈現。因為“和合學所研究的和合思維是中國古代哲學基本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和合遂成為中國人把握宇宙、理解人生的一種主要觀念,成為中國人一種基本的思維方式和價值準則。”〔12〕它既承認矛盾與沖突,又力求在承認矛盾與差異的基礎上實現融合,并通過“和合”來實現對沖突與融合的超越。所以,即使在高度復雜與高度不確定的今天,這種“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不失為一種解決問題的好方法。
如前所述,在人類社會開始向后工業社會轉變之后,既有的社會治理模式將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戰,我們不得不對其進行變革,但這種變革需要深入到思想層面。后工業社會是一個高度復雜和高度不確定的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前工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社會治理模式都將難以完成社會治理的重任。我們需要建構起一個能夠包容沖突與融合的、能夠滿足多元化、個性化需求的社會治理模式,這意味著對工業社會的中心-邊緣結構的社會治理模式的解構。根據全球化、后工業化過程中社會的變化趨勢,我們建構起來的社會治理模式將會是合作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由于在高度復雜和高度不確定的社會環境中,政府這個唯一的治理主體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需要所有能夠承擔社會治理任務的主體加入到社會治理體系中。這些新的社會治理主體與政府之間不是“參與”和“主導”的關系,因為如果這些新加入社會治理過程的主體是在政府的主導下來開展治理的話,那在社會治理的關系格局中仍然沒有改變“單中心”的局面,只是政府通過對其他主體的吸納而多了幾個聽話的“幫手”而已。后工業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決定了與之相對應的應該是多元化、個性化、主動型的社會治理模式,而“單中心”的社會治理模式體現出的是一種單一化、片面性的特征,是與后工業社會的情況背道而馳的。因此,多元化、個性化、主動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意味著政府壟斷治理地位不復存在,政府和其他社會治理主體之間的關系隨之由“中心與邊緣”向“中心與中心”演變,所有的社會治理主體之間是平等的合作關系,它們相互為伴、合作共治。
不難看出,社會治理模式從中心-邊緣結構向多元主體合作共治的演變過程就是一個和合的過程。和合思想強調“如只強調斗,或只想調和,都只是一面,不能把一個統一體分割了。事物發展一定是這樣的:在一個和合體中,有沖突事物才能發展;同樣,有融合事物才能發展。”〔13〕合作型的社會治理模式代表的是一個和合體,這個和合體是包含著沖突與融合的統一體——沖突代表著和合體中的多元性,融合代表著和合體中的合作關系。所以,在建構合作型社會治理模式時,既不排斥各合作者所具有的個性,也不刻意強調各合作者之間的機械同一,而是在多元化的基礎上來促成社會的合作共治。合作共治既是對多元性主體的包容,又是對多元性主體的超越。
我們知道,每一種社會治理模式都是與一種特定的政府模式相對應,社會治理模式和政府模式之間是一種相互適應、相互強化的關系。所以,對適應于工業社會的社會治理模式的解構,也意味著要對管理型政府進行變革;同樣,在重構新的能夠適應后工業社會的社會治理模式的過程中,我們也要去思考建構起一種新的政府模式。由于合作型的社會治理是一種去中心化的社會治理模式,政府失去了在中心-邊緣結構的社會治理模式中的核心地位而成為一個合作者和行動者。在中心-邊緣結構的社會治理模式中,政府是唯一的社會治理主體,政府體系幾乎等同于社會治理體系。因此,我們在解構中心-邊緣的社會治理模式時,對管理型政府的變革既是重點,也是切入點。反過來看,我們在建構合作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時,也應該從探索一種本質上全新的政府模式入手,這種新的政府模式不管在本質特征還是在核心價值上都應該比管理型政府更加合理。雖然如羅森布魯姆(David H.Rosenbloom)和克拉夫丘克(Robert S.Kravchuk)所言,管理型政府在實際的公共行政中政府具有管理、政治和法律的職能,但這并沒有反映出它的本質特征。就管理型政府而言,總體上具有三個特征——治理地位的壟斷性、職能定位的簡單化和行政人員的工具化。管理型政府的這些特征,都是在追求公共行政的同一性的過程中形成的——通過政府的壟斷治理,獲得了治理關系上的同一性;通過政府職能定位的簡單化,保證了政府職能的確定性;通過行政人員的工具化,獲得了行政體制的科學性。
管理型政府對同一性、確定性和科學性的追求,是以犧牲多樣性和人為地抹殺矛盾來實現的。主體的同一化排除了多元主體的可能,職能的片面化、確定化排除了靈活多變的可能,行政機制的形式化、物化排除了對治理理念和行政思想兼收并蓄的可能。然而,常識告訴我們,任何與人有關和需要人來完成的事情,都不可能真正地做到同一化,因為人是有意識、意志和價值判斷的存在。從結果看,這種幾近僵化的同一性在低度復雜和低度不確定的工業社會階段是有效的,但是在后工業化正迅猛推進的今天則難以為繼,需要通過政府模式變革來化解這個困局。前面我們論述過,合作型社會治理模式是一種面向后工業社會的治理模式,它是一個和合體。在這個和合體中,既強調沖突和矛盾,又重視融合與與互補,是沖突與調和的共在。
首先,從治權的形式上來看,由于多重治理主體來共同行使治權,那些過去被排除在治理體系之外的主體與政府一樣獲得了治理社會的權力,他們與政府之間不再是“中心”與“邊緣”的關系,而是一個和合體中的共同行動者。這個和合體是由形態各異、職能多樣互補、能力各有所長的行動者構成的,它們之間由中心與邊緣、主導與附屬、主體與客體、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向合作共治的關系演變。其次,隨著治理關系的變化,社會治理體系、政府本身,也不再從屬于過去的科學理性、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各種合作共治的行動者所尊崇的將是一種以實現公共利益為導向、以社會和諧的總體發展為目標的實踐理性。最后,在社會治理關系和主導價值變化的同時,帶來的將是政府角色和職能的變化。在前工業社會政府扮演著統治者的角色,發揮的主要是一種統治職能;在工業社會政府扮演的是管理者角色,發揮的主要是一種管理職能;在后工業化的過程中,政府扮演的將會是合作者、服務者、行動者的角色,發揮的將主要是一種服務的職能。依據新的治理關系、政府角色和政府職能建構起來的將會是服務型政府模式,它是本質上不同于統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的全新政府模式,是一種指向后工業社會的政府模式。
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必然會引起政府角色和職能體系的變換,這是一個解構與重構同時進行的過程。經過政府角色的轉變,政府由管理型政府扮演的唯一治理主體變成互相有別的眾多行動者中的一元。政府在角色轉變的過程中如何來處理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則需要在和合思想的指導下,一方面要正視并明確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行動者之間的個性差異,以此來形成靈活性的、多元化的社會治理,同時還要注重政府與其他行動者之間的在職能上融合與互補。但是,建設服務型政府不應僅僅停留在突出政府自身與其他行動者與合作伙伴之間的差異與融合,而是要實現對不同行動者之間的“沖突”與“融合”的超越。也就是說,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過程是一個和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要建構起一個作為新的和合體的服務型政府。
總而言之,中國傳統文化的和合精神它強調的是一種包容沖突與融合的理念,通過和合的過程來實現對沖突與融合的超越,既不單方面地強調沖突,也不單方面地追求機械、刻板的同一性。“中華人文精神是一種文化會通精神。對待文化學術,有遠見的思想家、學問家們都主張‘和而不同的文化觀,贊成多樣性的統一,反對單調呆板的一致。”〔14〕在這種文化精神和思維模式啟示下進行社會治理模式變革,對管理行政將會是一種本質性的顛覆,建構起來的社會治理模式也將會是一個能夠包容不同的沖突與融合的、能夠滿足多元化、個性化需求的合作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在作為一個和合體的合作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當中,政府模式將從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服務型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既能夠與其他社會主體取得共識,同時又在尊重彼此多元性和差異性的基礎上凸顯出各合作者之間的互補性和社會治理的靈活性,進而在合作共治中超越“差異性”和“同一性”。
四、結語
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時代背景下,政府壟斷的單中心治理模式已然難以很好地承擔起社會治理的任務,究其根源,在于中心-邊緣結構的社會治理模式本身所具有的機械性。“和合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遺產,其包容差異性和同一性的思想主張,對于解構中心-邊緣結構的社會治理模式以及建構多元主體合作共治的社會治理模式而言意義重大。然而,我們需要明白的是,“和合思想”對于社會治理模式的結構與重構的啟示主要存在于思想上的啟發和引導。因此,我們在涉及到具體的社會治理事務時,還需要根據具體的情況來研究,讓和合思想對社會治理的改善具體化,當然,達到這個目的還需要進行長期系統的探索研究。
〔參考文獻〕
〔1〕〔5〕〔6〕張立文.中國和合文化導論〔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18,22,37.
〔2〕〔14〕張立文,包霄林.和合學:新世紀的文化抉擇〔J〕.開放時代,1997,(1).
〔3〕錢穆.中國文化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36.
〔4〕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上)〔M〕.北京:昆侖出版社,2010.序5-8.
〔7〕〔美〕邁克爾·桑德爾.反對完美〔M〕.黃慧慧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9(導讀).
〔8〕王風才.批判與重建〔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29.
〔9〕〔德〕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M〕. 洪佩郁,藺月峰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113.
〔10〕〔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劉繼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3.
〔11〕彭和平.國外公共行政理論精選〔C〕.竹立家,等編譯.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7.160-161.
〔12〕季羨林.季羨林自選集〔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425.
〔13〕李振綱,方國根.和合之境〔M〕.武漢: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287.
〔15〕張豈之.中華人文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7.
【責任編輯:石本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