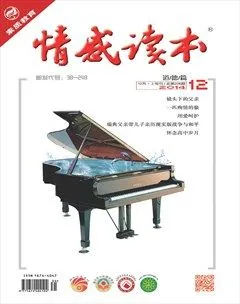父親的借條
馬從春
大學二年級那年,我闖了一場大禍。
事情源于我班的一位同學。男生宿舍樓里,按照學校的管理,一年級新生住在二樓,我們二年級的住在一樓。一天,有一個還不太懂規矩的一年級學生在洗完腳后,隨手往樓下倒了一盆臟水。說來也巧,水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我的那個同學身上。同學被淋了個“冷水澡”,火氣很大,碰巧那家伙也很蠻橫,一來二去,兩個人打了起來。
后來的結果是我同學吃了虧。那家伙是北方人,人高馬大的,我同學身材瘦小,實力懸殊。看著鼻青眼腫的同學,一幫哥們義憤填膺,迅速召開了討論會。大伙兒你一言我一語,最后一致通過:教訓一下低年級的小學弟。理由是高年級的師兄咱惹不起,可不能叫新來的小師弟騎在咱頭上。
后果相當嚴重。或許是因為年輕氣盛,也或許是繁重的學習壓抑太久,最后因演變為兩個班打群架,對方那個惹事的同學被打傷,宿舍樓的公共財物損失慘重,玻璃、門窗、桌椅、床等物品損毀頗多。
學校的處分決定很快做出。根據所犯“罪行”的程度,肇事者分別被處以留校察看、記過、警告等處分,每人罰款300元,用于賠償毀壞的公物。受罰的人中自然包括我。
老實說,我多少有點兒冤。理智告訴我,這件事情不應該去做。那天,我并不想去,我也極不贊同這種武力處理問題的方式。可是,當看著全班所有的男生都出動時,我還是去了。作為一個男子漢,我害怕他們嘲笑我膽小、沒種。
這個處分讓18歲的我寢食難安。從小到大,我一直是品學兼優的“優等生”、父母眼中的驕傲。尤其是那300元,可是我兩個月的生活費啊。
猶豫良久,我還是硬著頭皮回到了鄉下老家。
那是個陽光燦爛的星期天,可我的心情一點兒也燦爛不起來。走到村口,有熟悉的鄉親朝我打招呼:“大學生回來啦。”我強作歡顏,勉強應對。終于挪到了家門口,幾間破舊的草房里,小狗旺旺親熱地迎了出來。家里沒有人,這會兒父母應該在地里干活。
村西邊的坡地里,父親正趕著那頭老黃牛犁田,母親彎著腰,端著一把鐵鍬,吃力地開著墑溝。看到我回來,母親喜形于色:“兒子回來啦。”我點點頭,苦澀地笑笑。父親停住了犁,樹皮般蒼老的臉上露出疑惑:“咦,這個月的生活費不是回來討過了嗎?”
我羞愧難當,臉立馬紅到了脖子根兒,口里吱吱唔唔,說不出個所以然。看到這情況,父親表情嚴肅,默不作聲,母親趕緊拍拍我:“孩子,啥事啊?別急,咱好好說……”
巨大的壓力面前,生來不會說謊的我老老實實地說出了一切。我低著頭,不敢正眼看父親,他是這個家的支柱,向來以嚴厲著稱。在這個貧窮的村子里,我們兄妹幾個都能考上大學,得益于他的鼎力支持和嚴格管教。
沒有人說話,空氣沉悶得可怕。半晌兒,只聽見父親緩緩地說:“你知道,你們兄妹幾個讀書,全家的擔子都在我一個人身上。你的生活費我每月按時供給已很不容易,現在你已經18歲了,懂得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個錢我不能給你,但是可以借給你,你還必須打個借條。家里沒有現錢,下午,我和你媽拉一車稻子去鎮上賣。”
父親的話讓我無地自容。他說得句句在理。是的,我已經18歲了,該能夠為自己的行為埋單。我含著淚花打了借條,第二天返回了學校。
大學畢業后,我應聘到一家著名的外資企業工作。第一個月發工資后,我請假回到了老家。昏黃的燈光下,父親從一個厚厚的木箱子里面,找出那張發黃的借條:“孩子,你理解我的良苦用心了嗎?咱家的負擔重,為了能把你們教育成人,我才用這種方法激勵你。希望你不要怪我。現在你出息了,它也沒用了。”說著,就要撕那張借條。
我早已淚流滿面:“不,爸爸,它有用。這張借條我要好好地保存著,它是我一生受用的財富啊。”說罷,長跪地上,給父親磕了3個響頭。
許震宏摘自《安徽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