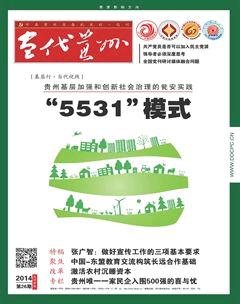貴州唯一一家民企入圍500強的喜與憂
楊柏,資深記者、編輯,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客座研究員。香港經濟導報執行總編輯,曾任中國青年報貴州記者站站長、深圳報業集團深圳商報《經濟瞭望》周刊主編、理論部主任。著有《走進大山》、《迎接挑戰》、《橫向布局中國》等十余部專著。
8月18日,全國工商聯發布2014中國民企500強排行榜,貴州有一家民營企業以年營業額158.7億元,列于第254位,成為貴州此項年年刷新的歷史記錄獎牌的獲得者。最初,在微信上讀到這個消息時,不免有點興奮。于是又找了更多的報道來讀,結果感覺又像兜頭被潑了一盆涼水。
據報道,2014中國民企500強排榜中,企業年營業額在2000億元以上的共7家,2000—1000億元的9家,1000—500億元的27家,500—200億元160家,200—100億元253家。百億及以上企業超過了91%,說明改革開放35年中國民營經濟第一方陣陣容的颯爽。可是如要以行政省為單位領回自己的孩子,你會發現,浙江入圍達138家,位居第一;貴州、吉林,卻都是1家,倒數第一。貴州和吉林與發達地區形成了鮮明落差,凸顯了區域發展的不平衡。
本來一件高興的事,為什么又讓人興奮不起來?想了幾天,我覺得這恐怕首先要從“起得早”與“走得如何”,兩句話中去找某種解釋。從1978年啟動改革以來,貴州至少有兩件“起得早”的事有口皆碑:一是農業改革貴州較早實施了包產到戶。當年池必卿書記的名言:“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上了人民日報;二是20世紀80年代貴州就創辦了中國最早的一個民營經濟改革試驗區。得益于此,貧窮落后的貴州,才一路走來,有了民企入圍500強“摘帽子”的業績。有消息說,2013年,貴州民營經濟增加值突破3400億元,占比43%,對貴州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接近60%。然而,與沿海發達省區比,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
大概于20世紀90年代前后,包括我在內的一群貴州“小老鄉”,曾在深圳聽過老書記朱厚澤講他到浙江考察民營經濟的情況。也有報告表明,2012年浙江省民營經濟創造增加值為22111億元,占GDP的比重為63.8%,其中個體私營經濟增加值20107億元,占GDP的58%。2000-2012年浙江民營經濟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保持在60%-70%之間。從發展速度看,1979-2012年,浙江民營經濟增加值年均增長18.2%,其中個體私營經濟年均增長26.4%,大大快于按現價計算的GDP年均增長速度(18%)。在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下行壓力的弱增長階段,浙江民營經濟,仍貢獻非凡,相形之下,對后來者真是有點醍醐灌頂了。
與浙江相比,另一個有意思的視角是本次入圍500強企業的行業及產業結構。在浙江上榜的138家企業中,大部分集中在制造業領域,其次居于房屋建筑與房地產業,與整個上榜企業涉及的行業產業結構相符。2014中國民企500強營業額上萬億的一共4個領域:分別為:一是制造業,73890億元;二是批發零售業,17234億元;三是房地產,14870億元;四是建筑業,10132億元。與此對應,浙江民營經濟產業結構總體呈現的是“二、三、一”格局,入圍企業經營也多數在制造業,28家在房地產與建筑業,符合也說明浙江經濟正處于工業化向服務業過渡的歷史階段;而貴州唯一入圍的企業是房地產公司,與浙江比,則表明貴州的經濟結構與水平還沒走出“農轉非”的發展階段。同時一個有趣的現象也意味深長,貴州這家入圍企業是在把房地產業包括在內的第三產業里做大的。而今,中國房地產暴利時代已然結束,貴州經濟與房地產、與第三產業如何理清頭緒,勢必會成為一個須著手解決的問題。
按照哈佛商學院的經典定義,產權是企業生理基礎的DNA。我國企業改革,從企業承包開始,一路走來,在所有制上的思路,基本可以解讀為是不斷廢除極左的“一大二公”,通過制度創新,引入民營化基因,使虛擬的產權關系,有了歸屬安排,從而重建了市場基礎,激活了大批企業。有句老話說,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有多成功,一個標志就是看產出多少明星企業。此次500強排名的前7家,營業額總和已達16760億。這個數字,拿到國際上比會超過不少小國家;在國內則超過2013年GDP排名第15名內蒙古及以后的15個省自治區和2個直轄市,約是貴州經濟總量的2倍。可見打造好企業,本是中國夢的一個組成部分。(責任編輯/吳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