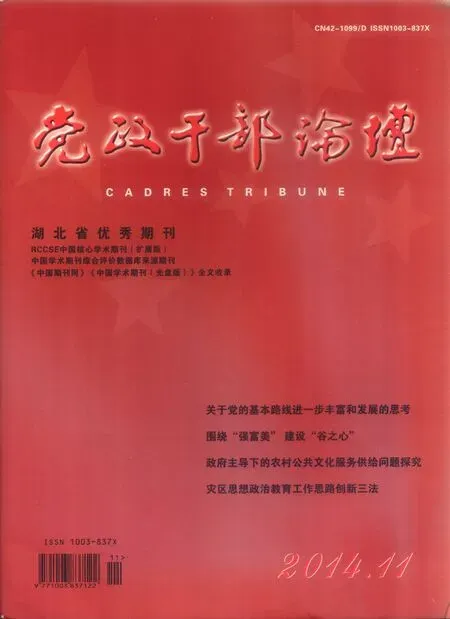領導干部理性應對“鄉愁”的人文途徑淺析
○ 姚 剛
“鄉愁”是人類歷史上的永恒話題,是古今游子的共同心聲,從《詩經·采薇》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到當代詩人余光中的“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或濃或淡的“鄉愁”,伴著人類的繁衍而延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更替,誠可謂“幽幽兮百代鄉愁,凄凄兮游子思歸”。
一、“鄉愁”的歷史演變及現狀
“鄉愁”情懷是傳統社會當權者不可或缺的情感元素,相對于普通民眾的“鄉愁”,崇尚“文以載道”的士大夫們的“鄉愁”更是“迢迢不斷如春水”。他們通過“鄉愁”所展現的家國情懷總是讓人動容,其中蘊含著偉大的精神內涵,穿透時空的力量令人仰止。
自2013年12月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提出“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慎砍樹、不填湖、少拆房”以來,“鄉愁”激起了現代人心靈深處的情感波瀾,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和思考。毋庸諱言,當今社會,淳樸的“鄉愁”似乎不再有傳統的意蘊,便捷的交通工具,縮短了人與故鄉的空間距離,無孔不入的信息技術更是可以讓民眾即刻“天涯共此時”,古人對故鄉的“思而難得”在當下幾乎“唾手可得”。但經濟發展并不意味著精神世界的充實,物質世界的日益豐富卻折射出民眾內心世界的孱弱,現代人似乎在追名逐利的路上迷失了自我,越發疏于對物理家園的依戀和對精神世界的追求。
領導干部群體的“鄉愁”困境較民眾“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似乎在地理和精神層面都難以應對“鄉愁”。一方面他們常任職異鄉,自身的“鄉愁”伴隨著環境的改變而弱化,繁忙的工作事務使他們無暇顧及地理家園和故土。作為城鎮化等社會活動的組織者,老百姓時常把“回不了過去,留不住鄉愁”的矛頭指向領導干部,認為領導干部就是民間“鄉愁”無處安放的“始作俑者”。另一方面,當代中國深刻變革,內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有的領導干部放松了對精神家園的追求,放棄了對理想信念的堅守,或這或那、或多或少、或輕或重地患有“精神空虛癥”,從而淪為“四風”的俘虜。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證明,解決“四風”問題重在建設領導干部的精神家園。領導干部以理想信念為旗,用優良作風打底,才能正風肅紀、取信于民[1]。
“鄉愁”是銘記歷史的精神坐標。溢滿真善美的傳統“鄉愁”,是群眾最現實直接的利益訴求,是提升群眾幸福指數的重要指標,也是弘揚經典文化、延續歷史文脈、推動社會和諧進步的重要基礎[2]。“鄉愁”事關國家未來和文明傳承,如何引領社會回歸傳統“鄉愁”,如何讓老百姓“知山樂水”?這是領導干部需要思考的重要課題。“風成于上、俗成于下”,留住“鄉愁”,領導干部帶頭是關鍵。筆者認為,消除自身和民眾“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的迷茫,領導干部必須理性應對“鄉愁”。
二、領導干部應對“鄉愁”的人文途徑
(一)善待自然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社會發展要遵循客觀規律,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的位置,不能毫無顧忌地破壞自然,致使“鄉愁”無處安放。金山銀山固然重要,但綠水青山更為重要,財富失去可再追求,而青山綠水一去不歸。“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領導干部推進城鎮化建設,要體現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要多點“道法自然”的淳樸,少點“人定勝天”的霸氣,多點對自然的敬畏,少點對權力的放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建設新農村”不應逼農民上樓,城鄉一體化要注意保留村莊原始風貌,農村建設要體現現代骨、傳統魂、自然衣,盡可能在原有村莊形態上改善居民生活條件,盡可能減少對自然的干擾和損害,不要讓城市化變成鋼筋水泥化。“禮失求諸野”。山水民間有著豐厚的道德積淀,不要讓現代化的車輪繼續碾壓蝸居在山水民間的“鄉愁”。
(二)正視變化
歷史上的每一次人口遷徙與社會變遷,其背后都無不隱藏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鄉愁”,遠的如秦人戍邊、客家人南遷,近的像走西口、闖關東、知青下鄉、民工潮等,這些打上時代印記的“鄉愁”情思,是中國人對時代變遷與鄉土傳統所進行的長期追問和深邃審視,反映了社會的現實狀態和文明進程。歷史車輪從不倒退,人類文明大步向前。以人為本、中國特色、科學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領導干部應理性對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鄉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領導干部要積極面對“鄉愁”的時代變化,既不能因為追求家園的改變而放棄對“鄉愁”的內心堅守,也不能因為堅守“鄉愁”而拒絕接受家園的有益改變[3]。“凡益之道,與時偕行”。飛速變化的時代需要領導干部有堅強的內心和主動的擔當,具有“笑看庭前花開花落,靜觀天邊云卷云舒”的豁達心態,做到“臨厲害之際不失故常”。“鄉愁”的回歸恰似“霧霾”的治理,是一個長期復雜和曲折的漸進過程,這就特別需要領導干部有很強的思想定力。
(三)品讀經典
精神家園是領導干部安身立命的思想基地、奮發進取的動力源泉[4]。精神家園一旦迷失,其危害性或許遠大于地理“鄉愁”的消逝。領導干部對精神家園的追求和向往,很大程度上可以代替朝思暮想的故鄉,從而在“有家歸不得”的苦悶里獲得解脫。要留住領導干部的精神“鄉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一面永恒飄揚的旗幟,而經典文學無疑是一個有益的補充。古云:“讀詩使人靈秀,讀史使人明智。”經典文學“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具有“泰山遍雨,河潤千里”的力量,每每“以金科玉律之言,作暮鼓晨鐘之警”,助我輩“以圣賢之智慧濟世利人,以先哲之格言鞭策啟蒙”。捧讀經典才能擇善而從,才能感知到人性中對于精神家園的向往和追求,才能讓中華傳統文化的接力棒接續傳遞。
(四)守望故鄉
“一別多少年,青磚黛瓦翹首望。熟悉的鄉音,猶在耳邊說滄桑”。如此“鄉愁”,曾讓多少游子黯然銷魂。故鄉是人們生于斯、長于斯、學于斯的地方。“誰不說俺家鄉好”、“月是故鄉明,人是故鄉親”、“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金窩銀窩不及家中的草窩”,這些耳熟能詳的民間俗語,記載了人們對故鄉的贊美和懷念。故鄉是精神漂泊者心靈的歸宿,沒有“鄉愁”的人身后或許一無所有。當有人做了壞事或犯了錯誤時,最后悔的話莫過于“對不起曾經養育自己的那塊土地”。古人的“鄉愁”有的令人羨慕,有的令人惋惜,劉邦歸鄉時唱出了“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的千古名句,而項羽則因“無顏見江東父老”敗亡。故鄉既是人生的起點,某種程度上也是人生的歸宿。“鄉愁”是現代人心靈的一劑撫慰藥,是每一位異鄉者心靈之“根”的所在和精神的歸宿。守望故鄉就不會迷失方向,留住“鄉愁”才能識得進退、懂得回歸。
(五)安心異鄉
“鄉愁”乃一生魂魄所依,然而,只有離鄉的人才會發現故鄉愈難回,“鄉愁”便愈深,這就需要身處異鄉的領導干部推己及人,因為你的故鄉即是別人的異鄉,你的異鄉即是別人的故鄉。贈人玫瑰,手有余香,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建設異鄉就是建設故鄉,正所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古代賢人對待“鄉愁”的態度,往往包含隨遇而安、無往不快的豪氣,很值得學習。他們“以天下為己任”,身處異鄉卻能泰然處之。“此心安處是吾鄉”、“所戀在哪里,哪里就是我們的故鄉”,折射出先賢棲居異鄉、建設異鄉卻不感漂泊孤獨的淡定情懷。
(六)懂得珍惜
只有對得住過去,才能回得了過去,才能留得住“鄉愁”。“子欲養而親不待,人欲惜而愛無存”,常令人感傷“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人間的悲傷莫過如此。“逝者如斯夫”,一切終將成為過去。有些東西不懂得珍惜,只能遺憾終生,有些東西忘了,就再難記起。懂得珍惜親情,懂得珍惜光陰,懂得珍惜當下,才能使回憶充滿美好,才能使“鄉愁”不留遺憾,才能不忘父母祖輩,才能讓兒孫記得住我們,才能使中華美德“薪盡火傳,不知其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江南,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故鄉,如果我們的兒孫只能從詩詞中,從發黃的典籍中,才能知道“鄉愁”的寄意,要靠注釋才能懂得“小橋流水人家”的意境,卻不知“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真切含義,這難道不是現代人不珍惜當下的過錯么?
(七)返璞歸真
現代社會為人們提供了大量橫向發展和向上流動的機會,同時也讓人們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欲望。奔跑在成家立業路上的人們,內心很難眷顧那純真的“鄉愁”,“回家看看”成為一推再推的行程。人心不古,“鄉愁”就會無足輕重;人若簡單,“鄉愁”便能駐守于心。現代人復雜的內心如若“返璞歸真”,記得住“鄉愁”就有了精神基礎。歷史上的成功人士大都具有真性情和赤子之心,他們在尋覓地理意義上的家園的同時,也不斷尋覓心理意義上的家園,將經歷過的人生情感與景致訴諸筆下,深刻的內涵對現代人有無盡的啟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面對人生,人們需要改變對于家園的漫不經心,汲取古人對家園深厚的人文關懷以及對于生命情感誠摯的眷戀,用真情灌溉或已干涸的心田。
(八)詩意生活
“鄉愁”常出現在詩詞之中,是詩人的專用詞匯。雖然今天是一個以互聯網為標志的高科技時代,但又是一個需要詩歌的時代。“詩意地活著”不只是詩人的理想,也是民族提升境界的因素。唐宋士大夫的“鄉愁”情結是歷史上的巔峰期,“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若為化得身千億,散向峰頭望故鄉”,他們的詩詞溢滿了“鄉愁”,所展現的人文情懷“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常常引起讀者的強烈心理共鳴。唐詩宋詞中所蘊含的古老文化信息和感情因子,撞擊人們的心靈,滌蕩人的精神,像一曲清溪淺流,緊緊地伴隨著世人的漫長人生,既用似水柔情澆灌心田,又在需要時洗滌心頭的煩惱。其實,現代人生命的深處也都蟄伏著詩意,人生年華有限而詩意無窮。要重建心靈的故鄉和精神的家園,唐宋文人是很好的楷模,他們把詩詞作為生命中的必需品,在生活中尋找并且創造詩情詞意。一首好詩、好詞就是一道美麗的風景,“不有佳詠,何伸雅懷”。
三、結束語
微言難明大義,祛病需用良方。面對唐朝詩人崔顥的千古一問:“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希望筆者的愚見能夠讓領導干部有所啟發。“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大量的山水、文脈依然存在,可記可憶的“鄉愁”讓人們與歷史交接,與古今共鳴,有著深厚的現實基礎。“往日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希望領導干部能夠帶領民眾留住美好的“鄉愁”。水滴匯成溪,稻穗集成束,如果人人都有濃濃的“鄉愁”,國家就會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1]鄭偉:《公共視野中的核心價值觀建設》,《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
[2]王代莉:《近代文化觀的流變與審思》,《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
[3]王其輝:《中國共產黨執政文化發展規律探析》,《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
[4]孫瑩瑩:《兩型社會建設中領導干部心理健康狀況及應對方式研究》,《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