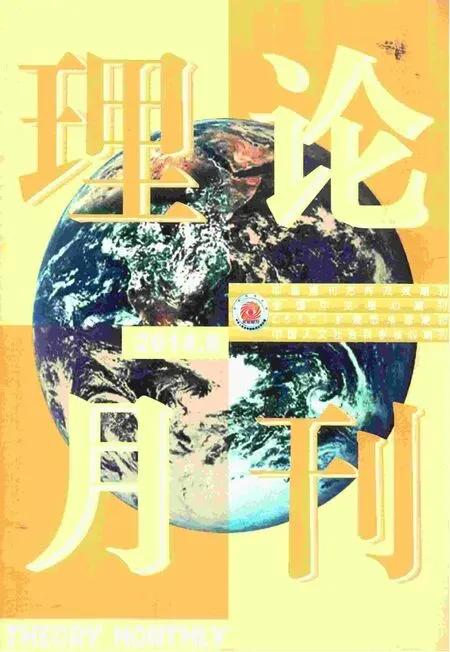中國古典戲劇神幻敘事功能及文化基因分析
齊海英
(沈陽大學 文化傳媒學院,遼寧 沈陽 110041)
中國古典戲劇敘事具有較強的寫意性,這迥異于西方戲劇寫實性風格。但中國古典戲劇的寫意并不等于脫離了現實,古典戲劇文本的題材與內容依然是源于現實生活,創作者以寫意化的藝術形式表現著對現實生活(尤其是底層平民生活)的強烈關注。只是戲曲創作者在現實性題材的敘述中時常超越生活時空而進行“想落天外”的神幻化敘事。這種實中帶虛、真中有幻的敘事筆法使中國古典戲劇形成了獨特的審美風貌。本文擬從主觀和客觀兩個視角對中國古典戲劇中神幻敘事功能作一探討與梳理,并且對此敘事策略形成的文化基因加以必要的揭示,以便于更深入了解中國古典戲劇的民族敘事特色。
一、古典戲劇神幻敘事功能分析
(一)主觀功能之一:情節“奇”“真”矛盾的化解策略
古典戲劇文本創作的最終目的是為舞臺“搬演”服務的,因而,廣大觀眾自然成為創作者創作戲劇文本的重要的制約和影響因素之一。戲劇“搬演”是一種不避俚俗,為廣大民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實踐活動,這便需要顧及到不同層次觀眾的口味與心理需求,所以,戲曲“搬演”的過程想要最大程度地吸引觀眾則必須在情節的安排與設計方面下工夫。平淡無奇的情節敘述會使觀眾興味索然,因而追求情節的曲折與離奇便成為古代戲曲創作者吸引和迎合接受者的重要手段之一。戲曲創作上的這種實踐性制約與需求反映在戲劇理論上,就形成了古典戲劇理論家所反復強調的一個理論審美范疇——“奇”。而尤其是明清時期出現的戲劇體裁——傳奇更是以“奇”作為其敘事突出特征。且看幾位古代戲劇評論者對此審美范疇的經典論述:
跬步之間,惟務搜奇索古而已。故其編撰,多使人感動詠嘆。[1]
古人呼劇本為“傳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經人見而傳之,是以得名,可見非奇不傳。[2]
傳奇者,傳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則不傳。[3]
五大南戲之一的《拜月亭》之所以被人尊崇的原因之一便是其富有巧合性的傳奇敘事:書生蔣世隆與妹妹瑞蓮,在戰亂中走散;尚書王鎮的妻子張氏和女兒王瑞蘭也在逃亡的人流中失散。因瑞蓮與瑞蘭姓名的諧音,造成瑞蘭、蔣世隆和張氏、瑞蓮的相遇,分別結為夫婦和母女。蔣世隆夫婦在酒店又巧遇王鎮,王鎮嫌棄蔣世隆是平民百姓,硬將世隆與瑞蘭二人分開。不久王鎮一家團圓,蔣瑞蓮偶然聽到王瑞蘭拜月時口念蔣世隆之名,從而知道了兩人原來是姑嫂。蔣世隆后來與結義兄弟陀滿興福相遇,一起上京趕考,分別中文武狀元。最后,世隆與瑞蘭團聚;瑞蓮由世隆作主,嫁給陀滿興福。
此劇處處充滿巧合與誤會,構成一出出令觀眾欲罷不能的戲曲“搬演”傳奇效果。
情節之“奇”往往依靠一系列的巧合、誤會等富有戲劇性效果的藝術手段營造而成。戲曲創作者既要努力追求文本敘事的接受“奇”效,同時又要保持情節發展上的自然與合理性,也就是要努力保持戲曲文本“奇”與“真”的和諧、統一敘事效果。但在具體的文本操作實踐中,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二者不能兼顧的創作困境,即創作者在追求敘事之“奇”的同時,卻難以保證情節發展處處銜接自然、合理,可能會出現一些情節鏈條斷裂、后續敘事合理性缺失等等問題。當遇到這種敘事困境時,現實性的敘事手段似乎難以突破這種困境,而只有借助于神幻化的敘事構想,即在“神助”之下使敘事獲得向前推進的依據和合理性。
南戲《殺狗記》第二十六出《土地顯化》開篇如此敘事:
【粉蝶兒】(外扮土地上)略駕祥云,霎時便臨凡世。
善哉,善哉!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小神乃孫華家中土地。近思本人棄親愛疏,不聽妻勸。楊氏今夜倩人殺狗,假扮如人,放在后門,仗此勸解。雖然如此,人和狗相不同,孫華豈不認得?今夜小神當顯神通,即與變化,令他兄弟二人看見,只道是人,不道是狗。自此稱楊氏為賢德之婦。
《殺狗記》情節發展到此際,便遇到了一個敘事推進的困境:孫華妻楊氏為使丈夫與其弟二人和好,定下殺狗扮人勸夫計,此情節構想與設計固然新奇巧妙,但存在著敘事難以為繼的漏洞:無論如何裝扮,狗與人的差別卻禁不住人眼的細致觀瞧,如此一來,后續的《見狗驚心》、《親弟移尸》等情節便失去了存在的現實依據。此時,作者便只能請“神”相助了。在上一段引文中,作者將敘事權托付與土地神,土地神成為跳躍于故事內外的全知全能,且具有神幻魔力的敘事者,使孫華兄弟只見“人”形,不見“狗”態。這樣,現實敘事困境因“神助”而獲得破解。
南戲《荊釵記》寫書生王十朋赴京趕考,其妻錢玉蓮被富家子弟孫汝權和繼母逼婚,無奈之下投江自盡,幸被新任福建安撫錢載和救起,后來才得以與夫婿再續姻緣。投江自盡,恰巧能遇到同姓錢安撫,又被收為義女,可謂奇之又奇。從現實敘事角度看,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這樣,作者又預先通過角色敘事搬請神祗:
【山歌】(丑上)做艄公,做艄公,起樁開船便拔篷。相公要往福州去,愿天起陣好順風。
(末)好好!說得利市!
(外)艄子,明早開船。
(丑)明早賽神好開船。
(外)合用物件說將來。(丑道介。外)你且聽我說,夜來寢睡之間,忽有神人囑付言語,說有節婦投江,使吾撈救。又道此婦人與吾有義女之分。汝等駕幾只小船,沿江巡哨,不拘男婦,撈救得時,重重賞你。
(眾)領鈞旨。
因有如此這般的鋪墊性的神幻敘事的嵌入,所以后文的一系列情節都獲得了存在和立足的依據。
(二)主觀功能之二:作者主觀理想愿望的超現實化呈現與張揚
戲曲作品與中國古代其他形式的藝術作品一樣,都是表達和宣泄作者思想和情感的審美載體。作者受生活現實的感召和激發,通過對生活現實的藝術化摹寫來抒發獨特的生存體驗與情思。作者對生活和生存的期待與理想往往在現實中難以達成。現實是“如此”的生活,而理想與愿望是“應該如此”的生活,所以,作者的主觀生存理想和愿望難以獲得現實化的兌現與驗證。而作者蘊積在心中的生存愿望與理想又是不吐不快的。那么,在如此情境下。作者便會以神幻敘事去沖破現實對心靈世界的束縛與阻隔,營造出一片雖幻而情真的藝術境界。
湯顯祖《牡丹亭》中的杜麗娘活著時可以為“情”而死,死后又可以為“情”而復生,這種可以跨越和往來于陰陽兩界的至幻敘事為人們所激賞的原因是因為它源于至真之情。湯顯祖本人在《牡丹亭記題詞》中對此有透徹的闡述: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4]
所謂的“至情”便是湯顯祖體驗到的人類理想化的具叛逆色彩的情感存在狀態。而《牡丹亭》中生死互轉的神幻敘事使這種理想的情感存在狀態獲得了超越現實束縛的最大程度的張揚。
南戲《白兔記》敘事也充溢著濃郁的神幻色彩:第四出《祭賽》中劉知遠偷食社祭福雞時有如此的神幻描寫:“只見滿殿紅光,神帳里現出五爪金龍,把福雞爪去了。”第六出《牧牛》中有劉知遠牧牛困睡臥龍岡時鼻息如雷、蛇穿七竅、火光透天的神幻景象。第十二出《看瓜》中有劉知遠看守瓜園刀斬瓜精,獲取頭盔衣甲、兵書寶劍及天機讖語的神幻描寫。第十八出《拷問》中借岳勛節度使之女岳小姐之口寫劉知遠巡更時“提鈴喝號”“聲音似虎嘯龍嘶”,行走之處“紅光閃爍,紫霧騰騰。”更神奇的是岳節度使令人捆吊劉知遠時無端起火,燒斷繩索。拷打之時“五爪金龍”“抓住板子,不容打下。”第三十出《訴獵》中劉知遠之子狩獵時借白兔引領巧遇生母李三娘。
中國傳統的固守田園的封建農耕社會形態決定了古代先民更多地是被動依賴天(自然)之力而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周而復始的生存實踐與體驗便造就了古代先民畏天而又敬天、親天的集體無意識化慣性心理。“舉頭三尺有神明”(俗語)“五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子語)“恪謹天命”(《尚書·盤庚》)“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書·召誥》)“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詩·大雅·板》)等等都是這種慣性心理的勸戒化表述。所以,古人無論是求福還是避禍,都希望得到上天的護佑和幫助。在這種企求和期盼中,上天在人們的心中便具有了兆示吉兇禍福的先驗功能。
《白兔記》中的男主角劉知遠歷史上確有其人,而且又是一個萬民仰望的帝王。劉知遠(公元895~948年),五代后漢開國皇帝,即帝位后改名劉暠,947年—948年在位。上述神幻敘事固然有帝王崇拜,宣示“君權神授”的倫理性功能。但在本劇中,作者截取的敘事時段是劉知遠稱帝之前,劇中的劉知遠還只是一個無意仕途,后被逼迫而走上博取武功之路的貧家子弟形象。作者重點關注的是劉知遠與李三娘之間悲歡離合的情感糾葛及倫理價值判斷。因此,上述神幻敘事除有銜接、調和故事情節的功能之外,更主要的是以引人稱奇的敘事手段表達著創作者善惡相報的理想化倫理價值觀。
在中國古典戲劇中,很多作品都有一個主人公死后遂愿的神幻化團圓結局,諸如 《竇娥冤》、《倩女離魂》、《梧桐雨》、《漢宮秋》、《長生殿》、《牡丹亭》等等都如此。 “死后遂愿是以靈魂不滅為基礎的,正是有情人不滅的靈魂最終成了‘眷屬’,而好人所積的善業,壞人所作的惡業,在來世都得到了相應的報應。”[5]這種報應是廣大民眾渴盼的道德評判結果,但在現實中難以實現,所以只能將之寄托于大快精神的神幻敘事中。
(三)客觀功能:虛實互見的意境化審美氛圍的生成
前面已經談到中國古典戲劇具有強烈的寫意色彩。而古人的理論表述中又有將戲劇視為“寓言.”的理論見解。如清人平步青曾有論述:“梨園戲劇所演之人之事,十九寓言,而實事可以演劇者,反多湮滅。”[6]今人曾有論述:“在古典劇論中,人們常常把戲劇稱為‘詩’,稱為‘曲’,或者稱為‘樂府’,其所追求的正是要強化戲劇藝術的‘詩化’特征,而古代劇論家把戲劇的故事本體逕稱為‘寓言’,同樣也是與上述追求相吻合的。誠然,‘寓言’是一種敘事藝術,但在中國古代的敘事文學中,它是一種最富于寫意性、象征性的藝術樣式,‘寓言’的精神實質乃是最大限度地摒棄敘事藝術所固有的那種客體性制約,而將敘事結構落實到創作歸旨上,從而完成寓言藝術的象征性和寓意性。而這正是中國戲劇的故事本體所刻意追求的。 ”[7]寫意、寓言、詩、曲、樂府等等都共同指向戲劇作品所具有的“詩化”審美風格,而“詩化”又恰恰是中國傳統戲劇意境化敘事特征的重要體現。意境敘述是具有民族文化底蘊和特色的一種敘事策略,它廣泛地存在于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等文學敘事實踐中(參見拙文《意境敘述的缺席與在場》,《社會科學輯刊》2006年第1期)。古典戲劇中大量存在的神幻情節是創作者為某種特定目的而進行的敘事結撰,敘事的主觀功能明顯,上文已有論述。但同時,神幻情節也是造成戲劇文本敘事意境化色彩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戲劇文本敘事中,寫實性的曲詞、賓白與神幻性的情節融和于一體,形成濃郁的意境化敘事色彩。
鄭光祖《倩女離魂》之第二折《魂送江畔》寫男主人公王文舉泊船江畔,月夜思念倩女,撫琴寄懷。此處雖未細寫王生撫琴之音聲、情態,但在讀者或觀眾的藝術化聯想中,已油然而生纏綿悲愴,超出文本之外之藝術情韻。而在此寫實描述之中又融入了神幻性敘事因素:倩女魂靈離體,聞琴聲追趕而至,其魂靈與文舉偕往京師。此神幻情節固然也有表達戲劇創作者主觀愿望的敘事功能,但同時以其超越現實的神幻傳奇性與寫實性情節融和于一體,形成了實中有虛、虛中有實,迷離惝恍如“鏡花水月”“羚羊掛角”般空靈、蘊藉的意境化藝術氛圍,給讀者或觀眾以幾多神思翩躚的審美體驗與享受。
白樸的雜劇《梧桐雨》和洪昇的傳奇《長生殿》都以唐明皇李隆基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為敘事原型,二者雖在主題指向及意蘊容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別,但都運用了神幻敘事:《梧桐雨》中唐明皇因思念情極而入夢,得見貴妃亡魂;《長生殿》中唐明皇也因情而入惡夢,因夢而得楊通幽及招魂法術,因法術而與貴妃月宮相見,永結終身。
以上作品中神幻化的“夢”“法術”等被賦予了溝通冥陽兩界的超凡敘事權利與功能,而此敘事策略得以生成和存在的依據便是作品主人公和創作主體一吐而快的真“情”摯“意”。正如明人梅孝己在《墨憨齋新定灑雪堂傳奇序》中所論:“傳奇之事,何取于真?作者之意,豈遂可沒,取而奇之,亦傳者之情耳。 ”[8]此神幻敘事為“情”與“意”的抒寫創設了廣遠深邃的藝術空間,成就了虛實互融、情意氤氳、余韻裊繞的藝術境界。
二、神幻敘事形成的文化基因
中國古典戲劇作品中的神幻敘事看似是一種敘述策略和技巧,但其實是民族文化觀念與思維的藝術化與審美化呈現。中國很早就有了魂魄鬼神等觀念。《說文》:“魂,陽氣也。”“魄,陰神也。”“鬼,人所歸為鬼。”“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魂與魄在《禮記外傳》中又被解釋為:“人之精氣曰魂,形體曰之魄。”由此形成了靈魂崇拜觀念。靈魂崇拜源于萬物有靈意識,古人不僅相信靈魂的存在,還相信靈魂不滅,認為靈魂可以離開形體而長生不死。古人認為,人的精神和肉體活動,受魂與魄的支配。并且魂與魄可以分離,人死形魄入土,靈魂則升天變成鬼魂。為使這些鬼魂有個生活的場所,人們便制造了另外一個世界——陰間,或者叫“陰曹地府”,給鬼魂居住,這是一個超現實的世界。由于有了這樣一個世界,鬼魂就具有超人的力量,人們崇拜它,祭祀它,依靠它消災祈福。
漢代佛教思想的傳入又為靈魂崇拜增添了新的內涵。佛教以緣起論解釋生命的輪回。輪回的動力來源于眾生自身的業力,這種業力量即使在行為終止之后也不會完全消失,仍然保持一種余勢,轉變成推動生命未來走向、決定其未來命運的力量。業行有善有惡,善行有善報,惡行有惡報。佛家宣揚的不同業因必然帶來不同果報的因果報應思想更加豐富和強化了靈魂崇拜的意識和觀念。
當然,作為晚近興起的戲劇文學的創作者及研究者對神幻敘事的虛幻本質應該說已有自覺而清醒的體認,如明代胡應麟在《莊岳委談》中有如此的認識:“凡傳奇以戲文為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9]由此看來,古典戲劇中具有深厚文化意味的神幻敘事是創作者明知其“幻”而有意為之,目的在于通過這種神幻敘事達成情節發展的圓滿,強化情感意旨的抒寫,同時此奇幻色彩的敘事自然而然地為中國古典戲劇營造出了詩意流蕩的藝術氛圍與境界。神幻敘事確是極具民族特色的戲劇敘事策略。
[1]鐘嗣成.錄鬼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2.
[2]李漁.閑情偶寄[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8.
[3]孔尚任撰,吳書蔭校點.桃花扇[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4.
[4]陳多,葉長海.中國歷代劇論選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56.
[5]祁志祥.佛教美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95-96.
[6]朱一玄,劉毓忱.三國演義資料匯編[C].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624.
[7][8]譚帆,陸煒.中國古典戲劇理論史[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173,151.
[9]陳多,葉長海.中國歷代劇論選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6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