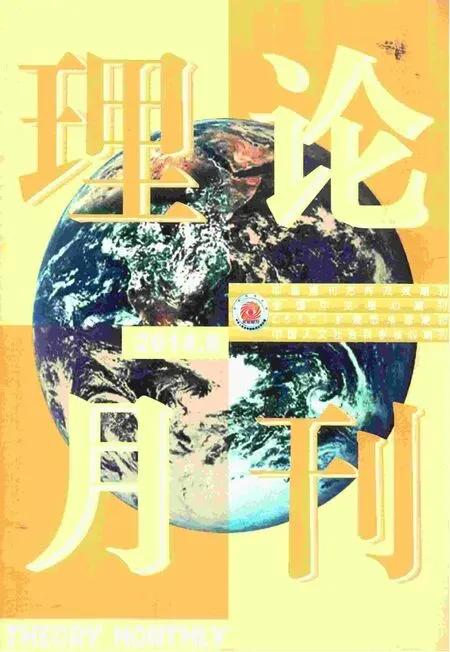《最藍的眼睛》中規(guī)訓權力的運行手段*
劉盛華 ,李 霞
(黃岡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北 黃州 438000)
法國后現代哲學家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規(guī)訓與懲罰》一書中論述了關于現代靈魂與一種新的審判權力之間相互關系的歷史,論述了現行的科學—法律綜合體的系譜。他指出,在這種綜合體中,懲罰權力獲得了自身的基礎、證明和規(guī)則,擴大了自己的效應,并用這種綜合體掩飾自己超常的獨特性。 他深入研究了現代社會的權力運行機制,并將現代社會比成一座圓形全景敞式監(jiān)獄。該概念始于 Bentham的全景敞視建筑(panopticon),其構造原理是:四周是一個環(huán)形的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戶,對著環(huán)形建筑。這樣,透過窗戶環(huán)形建筑內的囚禁者被監(jiān)視。身在其中,“人徹底被觀看,但不能觀看別人;在中心瞭望塔,人能觀看一切,但不會被觀看。 ”(福柯,2003:226)。
福柯指出,在這種建筑中,權力是可見的卻又無法確定的,即被囚禁者應不斷地目睹著窺視他的中心瞭望塔,但他在任何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窺視。中心瞭望塔象征著權力,這種權力的運行機制非常詭秘。這樣,權力在自動地發(fā)揮作用,被監(jiān)視者在監(jiān)視目光的壓制下,可以自覺實行自我監(jiān)禁。
美國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她的小說中記錄了黑人民族在有種族歧視傳統(tǒng)的社會所遭受的苦難,展示了一幅黑人種族在白人種族的強勢壓制下,在白人文化的強烈沖擊下被規(guī)訓、封閉、控制、隔離和排擠的清晰畫面。本文試圖選取莫里森的處女作《最藍的眼睛》,分析白人社會是如何對黑人種族進行成功的規(guī)訓,使之成為溫順而有用的成品。同時旨在進一步強調,黑人要沖破種族歧視的藩籬,首先必須解除自我監(jiān)禁,并進行有力的反抗,同時依靠群體、社區(qū)團結的力量,實現人與人的平等和諧以及自然完美的生存。
在《規(guī)訓與懲罰》中,福柯指出,規(guī)訓權力的成功源于簡單的手段:層級監(jiān)視,規(guī)范化裁決和檢查。本文將從這三個角度探討小說中的黑人民族是如何一步步陷入社會權力的泥沼當中的。
一、層級監(jiān)視
層級監(jiān)視是規(guī)訓權力實施的首要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對規(guī)訓的物理結構和組織結構的雙重要求。也就是說,它可以體現在規(guī)訓場所的設計上,也可以體現在監(jiān)視組織的設計上。比如軍營中的班長、排長、連長、營長和學校里的課代表、班長、老師、校長。完美的規(guī)訓機構“應能使一切都一目了然。中心點應該既是照亮一切的光源,又是一切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匯聚點,應該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又是一個所有的目光都轉向這里的中心”(福柯,2003:197)
筆者認為,在《最藍的眼睛》中,規(guī)訓社會對黑人的監(jiān)視或窺視有三個層次,即來自強勢文化主體的監(jiān)視,來自集體或社區(qū)的監(jiān)視,以及個體間的監(jiān)視。
1.來自強勢文化主體的監(jiān)視
《最藍的眼睛》中的強勢文化即白人文化,其對黑人種族的監(jiān)視和規(guī)訓始于“權力的眼睛”。在薩特看來,“人試圖以另一個人的視角來定義自己,只有當一個人通過自己的眼睛在另一個人的眼睛中看到自己,才能在他人眼睛里賦予自己身份,只有相互存在的認可才能產生健康的視覺平衡。 ”(Sartre,1966:57)
佩科拉的父親十三歲時和黑人女孩達琳第一次的性愛是在兩個白人的注視和手電筒的照射下完成的。在這里,白人的注視和手電筒的白光是白人文化的象征,是一種絕對權力的體現。在白人文化的注視和監(jiān)視下,喬利乖乖地接受指令,執(zhí)行命令,變成了馴服的肉體。由此可見,即便是明目張膽的監(jiān)視也變得合法化,且更具有制約性,從而使權力更好地得以流通。“面對他人的注視,我處于永恒的危險中。或者說,我在走向我存在的死亡。我面臨著被化為一塊頑石的死亡威脅,因此我必須反抗。這是我存在下去的唯一可能,我必須以眼還眼。”(萬俊人,1996:55)而事實是喬利沒有以眼還眼,這就決定了其主體地位的慢慢喪失。
在以白人文化為主流的社會中,黑人往往被忽視,成為白人眼中的一個盲點。當佩科拉高興地去雅克鮑斯基商店買糖果時,雅克鮑斯基 “迫使自己將目光朝她轉去……他的目光猶猶豫豫,徘徊不定,在時空的某一固定點上他感覺沒有必要浪費他的眼神。他并沒有看見她,因為對他來說,并不存在什么看得見的東西。”而當佩科拉朝他望去的時候,“看到的是一片空白……沒有一絲對人類的認同---目光呆滯,毫無察覺。 ”(莫里森,2005:39)由于雅克鮑斯基對她的忽視,她看不見自己,她相信自己的存在的信念逐漸減弱,逐漸被毀滅了。由此,她堅定了一個信念:自己很丑,因為沒有藍眼睛。
學校和媒體也成為白人強勢文化的象征。在《規(guī)訓與懲罰》中,福柯指出,學校的建筑也將成為一個監(jiān)視機構。“監(jiān)督的細節(jié)被明文規(guī)定,監(jiān)督進入教學關系中。”(福柯,2003:199)
在這種監(jiān)視下,來自莫畢鎮(zhèn)的淺棕膚色的女孩們接受的規(guī)訓是“將自然大方,以及一切人類感情都拋棄。無論這種簡樸的本色從哪里冒頭,她們都會把它掃除一清;在哪兒積累成習就在那兒把它消滅;在哪兒生根開花就在那兒發(fā)現鏟除...笑聲過于響亮,發(fā)音不夠清晰,舉止不夠文雅都需糾正。 ”(莫里森,2005:54)
學校,作為監(jiān)視機構充分發(fā)揮其作用,與強勢文化權力者的共謀關系還體現在整個教育體制中。這點我們可以從皂頭牧師切丘給上帝的信中得到證實。他寫到:“我們在殖民地生活的人把白人主子最富戲劇性、最明顯、也是最糟糕的特點學到了手……我們并非出身顯赫但卻很勢利,并非貴族但很講究成分。我們以為權威就是對下屬殘忍……把強暴誤以為是激情。”在這樣的監(jiān)視機構下,受教育者形成了有利于社會經濟統(tǒng)治階層的認知、美學和道德價值觀念。
在強勢文化的監(jiān)視下,黑人被不同程度地規(guī)訓,成為馴服的肉體。這種監(jiān)視“既增強了人體的力量(從功利的經濟角度看),又減弱了這些力量(從服從的政治角度看)”。(福柯,2003:156)使他們變得更有用。這正是黑人種族主義內在化的根本原因。
2.來自群體或社區(qū)的監(jiān)視
莫里森善于將小說人物置于某個群體或社區(qū)中。《最藍的眼睛》不僅揭露了種族主義內在化對黑人的巨大傷害,也披露了黑人內部對其中弱勢人群的毀滅性影響。作為社區(qū)的成員,布里德洛夫家時刻處于其監(jiān)視之下,從身體到精神都是馴服的。
布里德洛夫一家堅信自己是丑陋的,因為“他們四下里瞧瞧,找不到反駁此話的證據;相反,所有的廣告牌、銀幕以及眾人的目光都為此話提供了證據。”(莫里森,2005:24)于是,他們不加疑問便接受了這件丑陋的外衣。對于布里德洛夫一家的苦難,黑人社區(qū)總體上不伸出援助的手,不露出寬容的笑容。當聽說佩科拉被父親強奸并懷孕了的事實時,他們對這故事“感到厭惡、可笑、驚訝、憤恨甚至興奮。我們希望聽到人們說‘可憐的孩子’或是‘可憐的寶貝’,可是大家只是搖搖頭而已。我們希望看見人們皺起眉頭表示關懷,可看到的臉都毫無表情。”(莫里森,2005:120)在黑人社區(qū)監(jiān)視下,布里德洛夫一家沒有給他們造成威脅,沒有引起他們的妒忌,也沒有越界超過他們,這正是現代規(guī)訓社會權力機制要達到的最理想的狀態(tài)。“不需要武器,肉體暴力和身體約束的監(jiān)視系統(tǒng)。那里只有一道監(jiān)視的目光,在它的重壓之下,每個人最終都使之徹底內化到自己心中。以至于自己成了自己的監(jiān)視者,……這真是一個絕妙的方案……”(米勒,2005:303)在白人文化霸權的虛偽面具下,白人種族主義者從內部分化黑人,白人社會的種族主義動機顯而易見。
3.強勢個體對弱勢個體的監(jiān)視
“權力從未確定位置,它從不在某些人手中,從不像財產或財富那樣被據為己有。權力運轉著。”(福柯,2004:27-28)也就是說,權力是無主體性的。在權力的系網絡中,每個人都只是權力的一個點。他既是權力的實施者又是權力的實施對象。小說中有著較淺膚色的杰蘿丹接受白人的倫理教育,受到白人強勢文化的規(guī)訓,因此從不讓自己的兒子尤尼奧爾與下層黑人交往。此時,權力的客體演變成權力的主體。她時刻監(jiān)視著自己的孩子,給他解釋有色人與黑人之間的差別,不讓他和黑人孩子玩,不讓他在土堆上玩,不讓他“比試誰的折刀刀刃快。誰能把唾沫吐得又高又遠。”(莫里森,2005:24)盡管這些是他最喜歡玩的游戲。這種監(jiān)視和規(guī)訓導致的最終后果是尤尼奧爾變得心理失衡,舉止變態(tài),完全沒有男子漢氣概。最終他引誘佩科拉去他家玩,把她關在屋里,將小貓摔死,卻嫁禍于可憐的佩科拉。
《最藍的眼睛》是關于“眼睛”的故事,黑人在視與被視之間認識白人世界,認識自身,而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卻未能正確認識自己,反而在白人霸權文化的監(jiān)視下變得異常的馴服。
二、規(guī)范化裁決
規(guī)范化裁決是規(guī)訓的另一個有效手段,規(guī)范化裁決意味著規(guī)訓享有某種司法特權。“人們很容易理解規(guī)范力量如何在一種形式平等的體系中起作用的,它是在強求一律的原則下。凸現各種個體的差異。這既是實用的必然,也是度量的結果。”(福柯,2003:208)顯然,社會規(guī)范戴著平等的假面具去實施真正的不平等,從而達到對下層人的規(guī)訓和束縛。
在克勞迪婭姐妹的眼里,同班同學莫麗恩沒有她們善良,沒有她們聰明,但根據社會規(guī)范的裁決,她比她們可愛,因為她有漂亮的膚色,所以在學校里,“老師叫到她時總是滿臉微笑以示鼓勵。黑人男孩子在走廊里從不使壞將她絆倒;白人男孩子也不用石子扔她;白人女孩子被分配和她一起學習時也沒有倒抽一口氣;當她要用廁所間的水池時,黑人女孩子都會讓到一邊……”(莫里森,2005:40)可見,規(guī)訓的標準即規(guī)范包括明文規(guī)定的,也包括那些自然而然形成的經驗準則。在這種“自然的”規(guī)范下,人們自覺地遵守行為規(guī)范。對人們日常行為規(guī)范的制定和相應的獎懲制度正是規(guī)范化裁決的核心內容。通過規(guī)范化裁決,統(tǒng)治階級對社會生活中的每一個個體進行評估和分類,被統(tǒng)治者按照這種分類和區(qū)別自覺地實施自我監(jiān)視,這正是規(guī)訓權力的高明之處。
小說中還有一個典型的社會規(guī)范,那就是關于針對黑人而設置的禁區(qū)。比如“湖邊公園似乎渴望接待整潔有禮的白人孩子和家長在夏季到這來游玩……黑人是不許進公園的。”(莫里森,2005:67)就連湖邊的大白房子也不允許黑人逗留,以致當佩科拉和克勞迪婭姐妹去白人雇主家找媽媽時,“因為怕被人看見,也因為知道我們不該到此地來,我們未敢閑逛,繞過房子走到了后門。”(同上)
這些貌似平等的規(guī)范是由法律、計劃、條例所明確規(guī)定的,是一種“人為”的秩序。
“規(guī)范化裁決的標準是那些已經精心確立的各種內部要求,這些要求精密聯系,環(huán)環(huán)相扣,服務于規(guī)訓目的;凡達不到要求的必須受到懲罰。”(張海斌,2004)而這種懲罰的目的是同一化,規(guī)訓化過程,是為了對規(guī)訓對象進行更好的指導和監(jiān)督。因此,當喬利第一次認真地和達琳做愛,受到兩個白人獵人的凝視時,盡管他感到羞辱和憤怒,卻不敢去怨恨那兩個白人,而是將所有的怨恨撒向達琳,因為他清楚地明白 “這種想法會毀了他……仇恨白人會讓他自取滅亡,會將他像煤球一樣燃燒,只剩下灰燼以及團團的青煙。”(莫里森,2005:97)這正是規(guī)范化裁決在起作用,喬利擔心違反這種規(guī)范會受到懲罰,故而不敢反抗。
同時,規(guī)范化裁決采取的是二元機制,即獎和懲。在這種機制下,受訓者的行為和表現都被納入善與惡,好與壞兩個等級之間的領域。規(guī)訓懲罰的標準即規(guī)范包括明文規(guī)定的,也包括那些自然而然形成的經驗準則。規(guī)訓處罰所特有的一個懲罰理由是不規(guī)范,不符合準則。然而喬利的行為,包括酗酒,游手好閑,打老婆,燒房子,以及強奸女兒的可恥行為,在這個動輒得咎的懲罰羅網中,永遠無法符合社會規(guī)范,必將遭受來自規(guī)訓社會的嚴厲懲罰。因此他成了人們眼中的,老狗、毒蛇、耗子一般的黑鬼,他的生活也永遠是孤獨的,充滿著懲罰和排斥的。
與此相反,喬利的妻子波莉在白人家當傭人時的表現體現了規(guī)范化裁決機制中的另一面,獎。盡管波莉算不上是個好妻子,好母親,但在白人的家里她是個“出色的”幫傭。她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美好有序,她“生活的全部意義只存在于她的工作之中,她的品德無可挑剔,她積極參加教堂活動,煙酒不沾”。可見她的行為是符合社會規(guī)范的,是規(guī)訓權力所提倡的,所以她得到了回報。在白人家里,她盡情享受著人們的贊揚,享受著“權利、贊許和奢侈的生活”,享受著主人給她的愛稱。然而這種對歸順者的獎賞是為了實現對受訓者更好地訓練和矯正,“使之符合同一模式,使他們學會服從、馴服、學習與操練時專心致志,正確地履行職責和遵守各種紀律。”(莫里森,2005:206)這也正是規(guī)范化裁決的藝術所在,即在一種貌似平等的體系中起作用,目的是做到更為隱密的規(guī)訓。這是“一種謙恭而多疑的權力,是一種精心計算的、持久的運作機制。”(莫里森,2005:193)
三、檢查
福柯認為檢查(examination)將層級監(jiān)視和規(guī)范化裁決結合起來,進一步鞏固兩者的成果。“規(guī)訓權力是通過自己的不可見性來施展的。同時,他卻把一種被迫可見原則強加給它的對象。在規(guī)訓中,這些對象必須是可見的。他們的可見性確保了權力對他們的統(tǒng)治。正是被規(guī)訓的人經常被看見和能夠被隨時看見這一事實,使他們總是處于受支配的地位。”(福柯,2003:211)白人奴隸主對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不可見的權力規(guī)訓,正是用了這種策略。他們對黑人女性的規(guī)訓,不光體現在對身體的摧殘上,還體現在對思想的毒害上,讓黑人產生自我憎恨的心理,這是規(guī)訓的最高策略。在《最藍的眼睛》中,很多黑人女性都在這樣的規(guī)訓中崩潰了自己的身體陣營。
通過檢查,每個人都變成了一個“個案”,并獲得自己的身份標志。小說中的喬利便是這樣的一個“個案”,在社區(qū)人們的檢查下,他的身份被確定為“如同老狗,青蛇,耗子一般的黑鬼。”(莫里森,2005:11)此外,在杰蘿丹等人的檢查下,所有的黑人都是丑陋,骯臟的標志。因此,當她發(fā)現佩科拉出現在她家時,她的本能反應是“你這討厭的小黑丫頭,從我家里滾出去。 ”(莫里森,2005:60)
同時,檢查不僅使人置于監(jiān)視領域,也使人置于書寫的網絡中。在書寫文件相伴下的檢查,使每一個體變成了一個“個案”。成為“個案”的每一對象都會被“描述記錄,判斷評價,與他人形成對照”,同時他也會被“訓練糾正,歸類劃分、排除或是規(guī)范”等等。 (福柯,2003:215)
在小說的結尾,皂頭牧師切丘給上帝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這是對其內心世界更加真實、更加準確的再現。在這份書寫文件中,他描述記錄了自己的心聲,對自己近乎變態(tài)的行為做了判斷評價,認為撫摸小女孩的小奶頭并輕輕地咬它們時,是在表示友好,是自己的工作。他還在自白中將自己與上帝進行了對比,認為自己做了上帝“沒做,不能做,也不想做的事”,(莫里森,2005:215)認為自己比上帝更勝任他的工作。通過書寫,檢查者對他的思想了如指掌。
此外,不得不提到的一幕,是當波莉生產的時候,醫(yī)生對她的“檢查”。“一個小老頭醫(yī)生來給我檢查……他查完了之后又來了一些醫(yī)生……老一點的在教年輕的有關生孩子的事情,給他們示范。他走到我跟前時說給這些女人接生不會有麻煩,她們生起來很快,也不感到疼痛,就像下馬駒兒一樣。”(莫里森,2005:79)盡管波莉實實在在存在,卻無法被別人“看見”。醫(yī)生肆意處置她的肉體,不顧她的感受,以驗證他們對黑人的一貫想象。正如福柯所言,“檢查是這樣一種技術,權力借助于它不是發(fā)出表示自己權勢的符號,不是把自己的標志強加于對象,而是在一種使對象客體化的機制中控制他們。在這種支配空間中,規(guī)訓權力主要是通過整理編排對象來顯示自己的權勢。”(福柯,2003:211)在醫(yī)生眼里,波莉與任何一個黑人沒有什么不一樣,也只是一個抽象的存在;在對黑人的這種模式化處理中,黑人被完全客體化為一個符號,一個代表野蠻、愚蠢、低劣的符號。由此可見,懲罰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權力實踐,懲罰通過技術——符號對肉體實施直接的控制。
《最藍的眼睛》深刻揭露了白人社會對黑人民族的詭秘的規(guī)訓,使讀者清醒地識破它使黑人們成為溫順而有用的文化規(guī)訓成品的詭計。同時,對照白人強勢文化對黑人的規(guī)訓手段,我們領略了其強加于黑人的令人窒息的規(guī)訓力量,引起了我們對處于社會邊緣的人們悲慘生活的關注和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然而,“反抗與權力是共生的、同時存在的...只要存在著權力關系,就會存在反抗的可能性。”(福柯,1997:240-241) 因此,黑人民族必須解除精神包袱,進行有意識的反抗,在反抗中重塑自我,喚醒自我意識,走出權力規(guī)訓,樹立正確的自我價值觀,從而贏回失去的話語權。同時,黑人必須緊密團結起來,獲取集體的力量,才能實現真正的平等,走向真正的自由,實現真正的獨立。
[1]Sartre, Jean-Paul.Being and Nothingness [M].New York:Citadel Press,1966.
[2]董雪飛,田靜.規(guī)訓·懲罰·抵抗——論《看不見的人》中的權力關系[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
[3]黃婉嬋.權力與反抗——福柯的局部反抗理論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2007.
[4]蔣賢萍.“權力 -話語”語境下的《紅字》[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10,(8).
[5]路紅.構建黑人身體譜系圖——談托妮·莫里森小說中黑人女性身體[D].西北大學,2010.
[6]米歇爾·福柯.規(guī)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出版社,2003.
[7]米歇爾·福柯.必須保衛(wèi)社會[M].錢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8]寧東.權力視野之下的《麥克提格》[J].語文學刊,2008,(10).
[9]宋銀苗,常轉娃.《最藍的眼睛》文本中的“窺視”母題[J].咸寧學院學報,2011,(2).
[10]托妮·莫里森.最藍的眼睛[M].陳蘇東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
[11]萬俊人.于無深處——重讀薩特[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12]王泉.B先生的治家之道——《帕米拉》中的懲罰和規(guī)訓[J].山東外語教學,2004,(5).
[13]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愛欲[M].高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4]張海斌.福柯《規(guī)訓與懲罰》解讀[J].讀書與隨筆,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