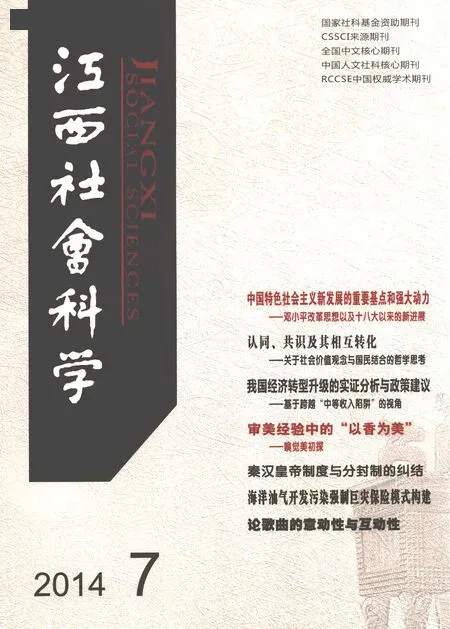論歌曲的意動性與互動性
■陸正蘭
在所有的表意文本體裁中,歌曲有著特殊的文化功能。歌曲的起源與發生,充滿了意動性。中國文化傳統的源頭經典《尚書·堯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這段名言一直被后世認為是中國詩學的綱領性開端。關于“詩言志”,整個一部中國文學史都在討論這個“志”究竟是什么,這里不用再討論了。關于“歌永言”,我本人提出過一個看法,認為它是指歌詞“延長指稱距離”[1],因為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尚書》里說的“詩”與“歌”,指的基本上是同一種文體,詩即歌即歌詞[2](P120)。本文著重討論的是最后一句“神人以和”,歷來注意它的學者很少,更沒有人指出其重要理論意義。
一、如何理解“人神以和”?
一般人認為這是指歌曲的禮儀性,或歌曲作為原始巫教的禱文源頭,“讓人神關系和諧,溝通順利”。筆者認為對它的理解應更進一步:祭神歌曲的理想效果,是讓神(意圖中的接收者)與歌者共同歌唱,呼應“以和”而成歌。后世的歌世俗化了,但歌曲這種體裁的根本品質沒有變:所有的歌曲,都希望取得接收者參與傳唱的效果,這就是本文討論的歌曲的“意動與互動”品格的由來。
文本的意動品質,是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意向性聯系。它是某些體裁特別注重的文化功能——期盼接收者在接收文本之后采取行動以“取效”。雅克布森著名的符號主導功能論指出:“當符合表意側重于接收者時,符號出現了較強的意動性,即促使接收者做出某種反應”[3](P169-184),即本文說的“意動性”。趙毅衡在其專著中指出:“意動性是許多符號過程都帶有的性質。”為此,他將符號文本“多少都有以言取效的目的”稱為“普遍意動性”,把某些意動性占主導地位的體裁稱為“意動性體裁”。[4](P120)歌曲的意動更注重“以言取效”,因此是典型的意動體裁。
“以言取效”來自于奧斯汀的言語行為說。奧斯汀在探討語句的品質時,將言語行為分為三種類型:以言言事,即說出一句有意義的話,表達一種意義;以言行事,完成交際的任務:說事、做事、起效;以言成事,通過說某事而造成或獲得某種結果。[5](P37-42)這最后一個類型,即是本文著重討論的:當一個或一種文本的意圖性指向接收者時,語句目的是成事(perlocutionary),在接收者身上產生效果。[6](P5)雅克布森認為意動性最極端的形態是祈使句。它在歌曲中體現得最為集中和頻繁。比如歌曲《大刀進行曲》中唱出的呼吁:“看準那敵人,把他消滅,把他消滅,沖啊!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殺!”這是再清晰不過的意動了。
歌曲并不是一個靜態的文字或圖像文本。相反,它具有強烈的歌唱實踐品質,只有歌眾的歌唱實踐,才讓其成為一首歌。這正是歌曲這一文化體裁的特殊性體現,正如詹姆遜所論,體裁是一種“‘機制’,作家與特定公眾之間的社會契約,其功能是具體說明一種特殊文化制品的適當運用”[7](P93)。
歌曲這種不斷反復實踐的文本特性,實際上是通過歌曲的流傳機制來實現的。筆者的觀點是“歌必然以流行為目的,任何歌曲都是意圖流傳的”。[8](P7)更明確說,幾乎每首歌創作出來,目的都是為了歌眾傳唱、意圖流傳的,歌的產生就是為了流傳。
歌曲的這種意動品格非常明顯。雖然闡釋學也論述接受者主體和發送者主體之間的“闡釋循環”,傳播學也提出受眾反饋的作用,但每種藝術文本意義的實現,即受眾對文本的闡釋性閱讀,作為意義的錨定點是有爭議的。有的闡釋學家認為作者意圖是解釋的標準,有的認為“讀者有權力使意義蔓生”[9](P321-334)。這場論辯已經延續了大半個世紀,至今結論仍不是很明確。但對歌曲這種體裁來說,闡述標準的種種討論并不適用,對歌曲文本微言大義的闡釋,是歌曲文本的文學性解釋,而歌曲不完全是文學。歌曲的特殊性,并不在于讀者對文本的闡釋性閱讀,它的主要文化功能,并不需要對歌詞的多層歷史文化含義作復雜闡釋,相反,歌曲文本的意義必須落實在歌的傳唱者身上。歌唱目的并不需要溯回意義發出者的原語境,而更注重應和在場的語境要求。歌眾的傳唱目的,在于他們進一步使用這些文本作自我表達,傳唱是歌者對文本的再創造。傳唱者可以拋開作者原意圖,在自己現有的語境中重新開辟意義之徑。
因此,歌眾傳唱讓歌曲意義具體化為在場意義,歌眾并不把作者的意圖作為意義的指歸,而讓自己成為歌曲意義的主宰者。這一點,歌曲明顯區別于其他藝術題材。
二、從意動到“無限意動”
文本的模態,就是文本的意圖性,在文本中表現在兩個地方:一是文本之內的詞語意義,一是口氣、場合、體裁等文本外語境條件。相比而言,文本內的形式品格雖然比較清楚,在主導格局上卻是次要的;文本外的語境條件,才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因為語態品格超出文本,是發出者與接收者之間的一種文化意向性契約,由于這個契約,接收者愿意回應發出者標明的某種意圖。
上述討論似乎非常抽象,其實在歌曲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這種關系極為具體。例如汪峰作詞作曲的《存在》這首歌它用一連串的悖論語句,陳述一種哲理,一種有關生存意義的觀點:我們的生存目的與我們當下的境況經常是背離的,因此人們經常是無可奈何地做與愿望相反的事。這樣一分析,《存在》的文本方式應當是“陳述式”。但實際上這只是語句的內部語義結構造成的假象。這首歌曲,不是用來討論哲學的,而是用來意動的。它希望聽到并傳唱的人拒絕茍活,而是振作起來“保持憤怒”,是在號召歌眾采取行動,勇敢地“展翅高飛”,過一種積極的人生。因此,即使再哲學,再“陳述”的歌曲,最終也不會丟掉它的意動目的。歌曲作為意動型的本文,總是在提供一種對話情境,此“對話情境”呈現出一種祈使式的呼吁。
請注意《存在》這首歌的最后一句,言說方式很特殊,不是祈使句而是疑問句,這是歌曲常用的特殊意動方式,用疑問句掩蓋要求對方采取行動的意圖,以緩和命令的嚴厲或迫切程度。
比如陳小奇作詞作曲的《濤聲依舊》。歌者以“舊船票”自況,似乎是一首情歌,要“登上你的客船”。但是意動是可以無限延伸的,就像作者本人所說,歌曲的“深層結構,表現的是這個時代人們的困惑。舊船票、客船是個象征,表現出新舊時代之間的矛盾、心態。”[10](P155)既然是一種象征,意義之門對每個歌眾來說就是開放的。因此,意動表意是可以無限延伸,可以稱之為“無限意動”。不同歌眾可以將歌曲應用于不同場合,表現完全不同的意義。
歌曲的這種“無限意動”方式,符合符號學關于意義延伸的原理,接近皮爾斯所說“無限衍義”,即:“一個符號,或稱一個表現體,對于某人來說在某個方面或某個品格上代替某事物。該符號在此人心中喚起一個等同的或更發展的符號”[11](P228)。符號的意義,就是被另一個符號替代的潛力。當“下里巴人”被一代代唱下去時,“陽春白雪”無法被傳唱,這個歌曲文本便從此消失了。因此,歌曲的意義必須用不斷傳唱來實現,理想的“歌眾”,應該作為一個新的符號文本的“再創作主體”,賦予歌曲新的含義。
三、從意動到互動
歌曲的這種意動性質,進一步造成社會交往的互相意動,互相影響,即歌曲的“互動性”。例如,某詩人喜歡模仿徐志摩的詩風,我們也可以說徐志摩會喜歡此詩人的詩風,這是對“意圖循環”和“意圖逆行”的一個很好解釋。然而,這是一個詩人對另一個詩人的態度,在詩的流傳中出現的可能是極少的,畢竟不是每個讀者都寫詩。歌曲則不同,因為每個歌眾都要唱歌,每個繼續傳唱的歌眾都“被(原作者)感興趣”,歌眾看中某位作者作的歌,也就是他們自己被某位作者看中,因為歌眾要做的不僅是接收一首歌,而且要在傳唱實踐中對這首歌進行再創造。
歌曲的這種互動品質,也暗合了現象學關于“交互主體性”的看法。胡塞爾對交互主體性概念解說如下:“我們可以利用那些在本己意識中被認識到的東西來解釋陌生意識,利用那些在陌生意識中借助交往而被認識到的東西來為我們自己解釋本己意識……我們可以研究意識用什么方式借助交往關系而對他人意識發揮‘影響’,精神是以什么方式進行純粹意識的相互‘作用’”。[12](P858-859)他已經意識到所有的“交往”是一種發揮意動性(“對他人發揮影響”)的方式。
因此,真正的意動取決于互動。文本背后的主體關注,是一種“主體間”關聯方式。音樂社會學家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指出:“歌曲的本質是對話。”[13](P23)不同于一般日常會話,這種會話更注重理解、認同與協商。歌曲的意動要落實到各種傳唱,因此歌眾的傳唱,對歌曲的發出者有一種回饋性的意動,實際上演唱是一種交換意動的過程。歌曲的意義在傳達中重新編碼,從而在歌者代表的創作主體與歌眾主體之間,制造一種動力性交流。
在歌曲流傳的五個基本環節(詞、曲作者、歌者、制作傳播機構、歌眾)中,我們可把前四者看成是一個共同的精英制作集團,最后一環是歌眾及其傳唱。在其傳播過程中,歌眾會比一般符號受眾表現出更明顯的能動性。他們對歌曲的接受,不可能遵循制作精英理想的模式,而是就自己的客觀條件和主觀需要,予以利用和改造。推動歌曲文本流行的動力正在于歌眾不斷創造新符號的能動性,正如符號學家達內西所說:“每個人內心都有一股尋找意義和制造意義的沖動,這種尋找導致了符號的產生”[14](P186)。比如20世紀90年代流行的一首耳熟能詳的校園歌曲《同桌的你》(高曉松作詞作曲):“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誰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誰看了你的日記/誰把你的長發盤起/誰給你做的嫁衣。”它被更年輕的一代,改編成更具當代感的《同班的你》:“你總是唱著不想長大/擦肩就是二十好幾/誰擁抱活潑開朗的你/誰陪著犯二的你/誰聽了我給你的微信/誰把它徹底清零。”
歌眾的這種能動性甚至超過了霍爾的“對抗式解碼”、費斯克的“生產者式的解碼”,獲得了更自由的“創作式解碼”。這就是我們在歌唱活動中看到的自由的“翻唱”和“改編”現象。歌眾對歌曲文本的傳唱實踐,實際上是一場情感狂歡。每個歌眾都在“演唱中”進行一種個性操演。任何一個歌唱的符號運用者都無法完全控制其符號意義,意義通過在場與缺場的相互作用,形成一個不斷增值的新的符號。
四、歌曲是共同主體性的實踐典型
盡管在上文中,我們說到了歌眾是一種強力的能動受眾,發揮著特殊文化功能,但歌曲作為一種特殊的意動體裁,在其生產和流傳過程中,它的影響力也受制于歌曲創作——流傳的每一環之間的深層互動。
我們看到在歌曲生產流傳的全程中,每一個環節的創作意圖性并不完整,前面的總被后面的不斷修正,沒有一個環節能享受意圖的充分自由。換句話說,個體的選擇都會受“歌眾社群”影響,他們雖有在場的主體獨立性,但不可能充分,只有融于一個社群,才可能實現主體完整性。對一首歌來說,流傳不僅是每個環節主體之間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體現,更要演化成有效的“共同主體性”(com-subjectivity)。共同的主體性,就是激發歌眾傳唱,在意動中完成意義。
歌曲生產和傳播流程中的所有主體,是依靠生活世界的情感經驗相互關聯,并據此建立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每個人貌似獨自欣賞,實際上是在通過主體間性與社群相通。他們哪怕相隔萬里,從未相逢,卻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完成一個意義,形成一種社會群體,即哈貝馬斯所說的“交往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通過這種內部活動,所有參與者都可以相互決定他們個人的行動計劃。因此可以無保留地追求他們非語言活動目的”[15](P52)。歌者與歌眾的互動,甚至能互相轉化,即歌眾與歌者互換位置。歌唱行為完美地體現哈貝馬斯提出的共同主體論,能使自我與他者緊密地交融,它也是符號的社會性功能的最佳范例。
在歌詞中,在演唱活動中,“我”與“你”的語境不斷變化,歌詞當中的“你”是飄移的,有時候這一句話落在一個人身上,下一句話就變成“我”就是那個“你”,再下一句話就感覺這是一個社會了,再下一句話又可能變成了一個旁聽者,這個“你”是浮動的。
一部歌曲史就是一部歌眾傳唱的文化實踐史,歌曲的文本存在品格,充分體現在歌眾的傳唱實踐中。意動性與互動性,并不一定是非常具體的祈使,有時候歌曲請求對方實施的行動,可以很不可解,甚至荒謬。例如這首《祈禱》:“讓地球忘記了轉動呀/四季少了夏秋冬/讓宇宙關不了天窗/叫太陽不西沖”。
這樣祈使的目的,似乎離意動很遠,只是一個象征姿態,一個促使歌者從凡庸的日常事務探出身來,企及表面上的“不可能”的某種超越,這時候的意動與互動,是一種想象的應和,也正是意動性才有可能做到這種超越。這就讓我們回到了本文開頭的“人神以和”命題上。歌者(歌曲的創作集團)與歌眾(實現歌曲意義的傳唱者集團),最終應和而形成的,是歌的“意義場”。歌曲作為一種文化體裁的最終問題,是如何保證一首歌的流傳實踐不停止,也就是落在歌曲的無限衍生意動性上,這就是歌曲的“人神以和”目的論:讓神和人一道唱歌,讓聽者變成歌眾,變成傳唱者,成為歌曲藝術的神。
[1]陸正蘭.論體裁的指稱距離[J].文學評論,2012,(3).
[2]王小盾.詩六義原始[A].王小盾.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1輯)[C].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3](俄)羅曼·雅克布森.語言學與詩學[A].趙毅衡.符號學文學論文集[C].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4]趙毅衡.廣義敘述學[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3.
[5]邱惠麗.奧斯汀言語行為論的當代哲學意義[J].自然辯證法研究,2006,(7).
[6]John R Searle.A Classification of Illocutionary Acts.Suzame Romaine.Language in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7](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作為社會象征行為的敘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8]陸正蘭.歌詞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9]W.J.T.Michell(ed).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10]陳小奇,陳志紅.中國流行音樂與公民文化:草堂對話[M].廣州:新世紀出版社,2008.
[11]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vol 2).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 -1958.
[12]倪梁康.胡塞爾文集[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
[13]Simon,Frith.Popular Music:Music and Society.London:Routledge,2004.
[14](美)馬塞爾·達內西.香煙、高跟鞋及其他有趣的東西:符號學導論[A].肖惠榮,譯.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
[15]Juergen Habermas.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Cambridge:MIT Press,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