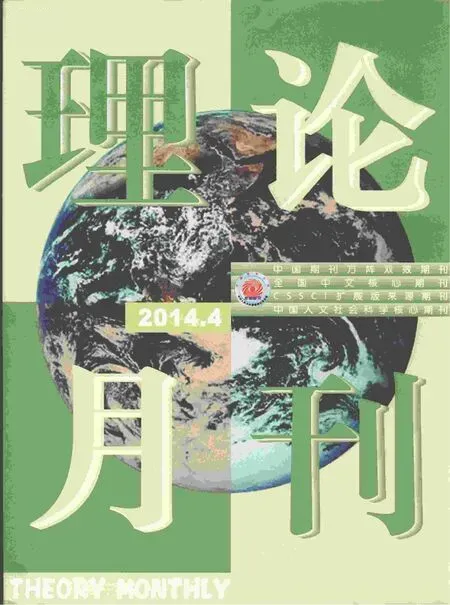朱熹理學思想述論
柏家文
(安徽大學 歷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2)
南宋朱熹繼承北宋五子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和邵雍的儒學思想,尤其是二程理氣學說思想,將儒學發展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使儒學亦成為極具思辨性的學說思想體系,回答了宇宙、自然、人及社會等一系列思想命題。
一、理的宇宙本體論
理本體論是朱熹理學思想體系的基礎,對于宇宙本體,朱熹提出太極即理、陰陽是氣、理氣動靜、理一分殊等范疇。朱熹認為理乃是宇宙萬物的本體。他說,“太極只是一個‘理’字。 ”[1]“理者,天之體。 ”[2]“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3]宇宙間天地萬物莫不是由理而形成的,萬物也莫不從宇宙太極中稟受了這個“理”,不論是有生命的生物,或是無生命的舟車,皆有“理”寓于其中。“理是人物同得于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 ’”[4]
朱熹認為沒有“理”,便沒有天地,沒有人物,沒有一切。從邏輯上說,有了“理”便有了陰陽“氣”的流動,遂化育為萬物。他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 ”[5]“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6]“理”是促使事物生成的法則,“氣”是構成萬物的質料。萬物皆由“氣”依“理”而生。“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后有性;必稟此氣然后有形。 ”[7]
朱熹認為理氣的運行并沒有時間上的先后,“有是理后生是氣”,是自“一陰一陽之謂道”的邏輯推來的。[8]因而他認為理氣只是有邏輯上的先后,“理與氣本無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時,卻如理在先,氣在后相似。”[9]太極之理是形而上者,無形無跡,陰陽之氣是形而下者,有形有跡。有跡之氣是無形之理的載體,無形之理是有跡之氣運行的法則。兩者相伴而生,相伴而行,合為一體,非為二物。“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10]“是先有理,后有氣邪;后有理,先有氣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 ”[11]“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12]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陽交感,理與氣合,萬物生化。朱熹認為作為本然的太極是不動的,動靜的是陰陽之氣,太極只是乘陰陽二氣的動靜之機而動,“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 ”[13]太極之理作為本體存在于陰陽二氣的動靜之中,不是動的主體,氣才是動靜的主體,動則為陽,靜則為陰,而作為這動靜根據的“理”亦在“氣”中,“理”隨“氣”動。 “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無形,而氣卻有跡。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靜!”[14]朱熹以人騎馬作比,動的是馬,而人隨馬動。“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后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 ”[15]
太極陰陽的動靜也是沒有先后的,朱子并以人的呼吸作比。他說,“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后。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后?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16]動靜前后相繼,無始無終。朱熹引述程子的話說,“‘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 ”[17]“‘繼是動靜之間否? ’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 ’”[18]
朱熹認為太極之理是宇宙萬物的普遍法則,理與氣合,化育萬物,萬物皆稟受此理,而萬物又各具有為此物而不為彼物的特定之理。他引述程子的話說,“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個理。”[19]“理固是一貫。謂之一理,則又不必疑其多。自一理散為萬事,則燦然有條而不可亂,逐事自有一理,逐物自有一名,各有攸當。”[20]他以草木桃李人物之不同為例說,“如草木,只是一個道理,有桃,有李。如這眾人,只是一個道理,有張三,有李四;李四不可為張三,張三不可為李四。如陰陽,西銘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21]萬物稟受太極之理,而物各有不同,朱熹認為這是因氣有精粗偏正的結果。二氣五行,絪缊交感,千變萬化。他還進一步說,“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22]
二、性即理的心性論
心性論是朱熹理學思想的核心內容,是關于人及人類社會的思想理論。朱熹提出“性即理”的心性論命題,將人性論與理氣的宇宙本體論很好地貫通起來。認為“心”統“性”與“情”,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心”有“道心”與“人心”之分,“性”有“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別。
理本體論告訴我們,宇宙間萬物皆由“理”而形成,“理”附著于“氣”而萬物化育。朱熹認為“天命之謂性”,“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23]所有人之“心”即由“性”這個太極天命之“理”與“陰陽二氣”交缊而成,“性”附于了“心”上。“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 ”[24]
人自其誕生,心的作用是從不停息的,但其作用過程可以分為思慮未萌的“未發”狀態和思慮已萌的“已發”狀態。思慮未發為“性”,已發為“情”。朱熹說,“性是未發”。[25]“性情一物也,其所以分,只為未發已發之不同耳。若不以未發已發分之,則何者為性,何者為情耶? ”[26]“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 ”[27]也就是說,“情”還沒有發出來時,此時的“心”表現為渾然狀態,就是“中”,就是“性”,但各種“情”也還是附于“心”的,只是沒表現出來而已,一旦發出就表現為“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只是渾然,所謂氣質之性亦皆在其中。至于喜怒哀樂,卻只是情。 ”[28]
朱熹認為“性”與“情”是一體的,都附著于可見可把握的物“心”,“心”就是“性”“情”物化的主體。 他說,“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29]“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合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30]他還舉邵雍的話說,“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此說甚好。蓋道無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個心,卻將性在甚處!須是有個心,便收拾得這性,發用出來。”[31]朱熹并高度評價張載“心統性情”說,他說“后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個‘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32]
“心”是“性”“情”的物化載體,兩者統一于“心”,“性”是形而上之理,通過“情”來表現出來,因而已發之“性”已不是“性”之本體,而是“性”之用。所以說“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亦即心有體用,思慮未萌未發是性是體,一旦萌發之際即變為情,變為心之用。“心有體用,未發之前是心之體,已發之際乃心之用。 ”[33]“性以理言,情乃發用處,心即管攝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34]他舉孟子的話說,“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35]
朱熹認為“性”是“心”的未發狀態,是太極之“理”,天命之“性”,沒有不善的;“情”是已發,受精粗偏正“氣”的影響,有善與不善。“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才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36]“性未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稟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 ”[37]
朱熹認為人之“心”有“道心”“人心”兩種,他說,“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命之性為根于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38]朱熹認為人的知覺活動出于“理”的便是“道心”,出于“欲”的便是“人心”。 “此心之靈,其覺于理者,道心也;其覺于欲者,人心也。 ”[39]“只是這一個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40]這就是說,道心是出于天理的道德意識,人心是出于個體情欲的感性欲念。朱熹認為造成道心人心之別的原因在于人是“理氣”合一,稟“理”成性,稟“氣”成形,性則一,氣則有所不同。“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41]
宇宙萬物皆稟“理”成性,稟“氣”成形。 “心”是“氣”的物化,在物化過程中,稟受了天地之理的“本性”,這就是來自太極純然的“天命之性”。然而“氣”有精粗偏正,萬物也就有了“氣質之性”。因此,朱熹認為人之“性”有“天命之性”“氣質之性”之分,發展了程顥程頤關于人性論的思想。“天命之性”萬物皆同得于天,而之所以有人與物,善與惡,賢與愚之別,皆由于所稟“氣質之性”的不同。“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42]“有氣質之性,無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無氣質之性,亦做人不得。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卻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然此理卻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卻是氣也。”[43]“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后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缊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后有以為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后有以為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于《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 ”[44]
三、窮理致知的認識論
理本體論認為,萬物皆由“理”與“氣”合而成,“理”在物中,太極有太極之“理”,萬物又各有其“理”。太極之“理”是宇宙的普遍原則,物物之“理”是其各自為物的法則。人類認識的活動就在于窮索宇宙萬物之“理”。朱熹認為其手段就是格物窮理格物致知,窮理致知的主體條件就是體認者要主敬涵養。
“格物致知”語出《禮記·大學》篇,朱熹解釋說,“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45]“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到也。”[46]就是說在認識的實踐活動中,要努力窮索事物之理,在通曉事物之理后,才能使我們的知識完備,達到“致知”。
那怎樣才能“致知”呢?朱熹主張“格物窮理”,他在《補大學格物傳》中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47]
窮理又是怎樣的功夫呢?朱熹說,“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于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于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腳進得一步,右腳又進一步;右腳進得一步,左腳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48]心有知,物有理;理有未窮,所以知有未盡。以現有的知不斷窮索未知之理,一物一物地格,持之以恒,自然就貫通了。這是一個量的積累的過程,當積累達到一定程度,人的認識就會有豁然貫通達到理的質的飛躍。
在窮理過程中,亦并非須格盡天下所有之物,他說“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49]這是由特殊到普遍,由個別到一般的認識過程。
朱熹認為要達到窮理致知須用主敬涵養的態度,何為主敬呢?他說,“敬不是萬事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 ”[50]還說,“敬只是惺惺法,所謂靜中有個覺處。”[51]這是窮理致知的主體條件,沒有主敬,則心思散亂而不清明,是不可能體認事物之理的。“身心散慢,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先且習為端莊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理明耳。”[52]“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53]
四、知而行理的實踐論
知行即致知力行,致知屬于認識論范疇,力行屬于實踐論。朱熹認為只有求得反映“理”即事物規律或道德準則的“知”,才能作出合乎“理”的“行”。 “知”和“行”都是十分重要的,不可偏廢。他說,“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廢。……但只要分先后輕重,論先后當以致知為先,論輕重當以力行為重。 ”[54]認識了宇宙萬物之“理”,即事物的普遍法則和規律,具備了處事所需的豐富完備的知識,就要用這些知識來指導我們人類現實的社會和生活實踐。在人性論上說只有認知了道德,確立起完善的道德意識,才能達到主體的道德自覺,才能在社會活動中踐行道德。朱熹理學思想所體認的“知”即太極之“理”,人性論上也就是人所稟受的先天固有的“天命之性”仁義禮智,因而人類所有的“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必須以“仁義禮智”為道德標準,至于“中”“和”,方能成就或“圣”或“賢”。
如上文所說人類在稟受了天理“仁義禮智”之“性”的同時,是由精粗偏正之“氣”成形的。體現“仁義禮智”的先天之“性”都是善的,而這氣則有致賢愚、善與不善。朱子理學告訴人們,可以通過為學的途徑和克治之功來變化“粗偏”之氣稟。“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稟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稟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卻是要變化氣稟。……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于中乃可。 ”[55]
朱熹認為,用功克治首要的要在“心”上下功夫。“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樂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節則謂之和’,心是做工夫處。”[56]心是統一性情的,心有道心人心之分,性有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別。道心是符合天理的道德意識,人心則是個人的感性欲念。符合天理的道德意識是天命之性的反映,個人欲念則是氣質之性的體現。符合天理的道德意識即仁義禮智,出于“理”,皆善;個人欲念出于“氣”,有善與不善,若不加以“省察克治”,則會流于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后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為圣;稟其清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57]所以要時刻省察克治,以致存“仁義禮智”之“天理”,滅“惡和不善”之“人欲”。
主敬涵養是在“心”上做功夫的重要方法,它不僅是窮理致知認識論的方法,也是躬行實踐的方法。他說,“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58]也就是說在生活實踐中要收斂身心,使內心常處于一種敬畏、警省狀態,專一而不放縱散逸,做到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同為學窮理一樣,不用主敬的功夫和態度,是不可能踐行真正意義上的“理”的,“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 ”[59]
踐行道德,朱熹認為還要努力為學,變化氣稟。他引述《大學》中的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認識論,“親民”“止于至善”是實踐論,為學致知是為了更好地指導實踐。也就是說為學之目的,在于明白上天賦予我們的“理”、“性”,即先天的道德法則“仁義禮智”。在修身治國齊家平天下的各項實踐中,要貫徹“仁義禮智”,親而愛人,摒卻由于“氣”之不同所致的惡和不善的私欲雜念,喚回“道心”,向純凈的天命之性“理”仁義禮智邁進,最終達到善之極,是為圣賢。
在實踐中,要踐行“仁義禮智”重要的是要做到“信”,“信”是成就并體現“仁義禮智”的。“‘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60]“誠是個自然之實,信是個人所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61]
[1][3][5][6][8][9][10][11][16][17][18][19]〔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1[M].
[2][14][23][24][25][29][30][32][33][34][35][36][56]〔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5[M].
[4][12][22][28][31][37][38][42][43][44][55][57]〔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4[M].
[7]答黃道夫[A].朱文公文集:卷 58[C].
[13]太極圖說解[M].
[15]朱子語類:卷 94[M].
[20][21][60][61]〔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6[M].
[26]答何叔京十八[A].朱文公文集:卷 40[C].
[27]太極說[A].朱文公文集:卷 67[C].
[39]答鄭子上八[A].朱文公文集:卷 56[C].
[40](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78[M].
[41]中庸章句序[A].四書章句集注[C].第14頁.
[45]大學章句·經一[M].
[46]大學章句·公圣一[M].
[47]大學章句[M].
[48]〔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17[M].
[49]〔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18[M].
[50][58]〔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12[M].
[51]〔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63[M].
[52]朱文公文集:別集三[M].
[53][59]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南宋建炎至德佑·勉齊集:卷 36[M].
[54]〔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 9[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