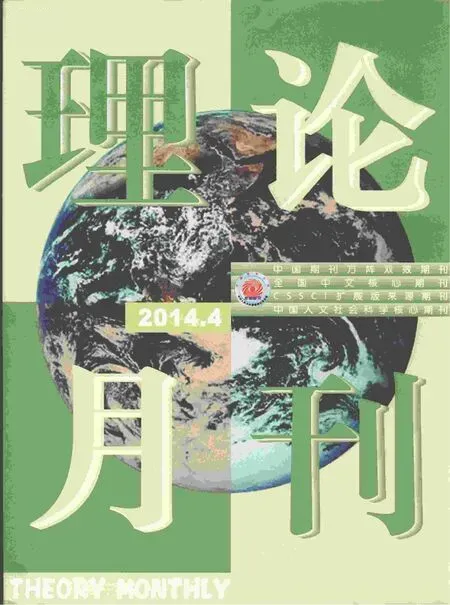論梅光迪《近世歐美文學趨勢》的研究特色與史料價值*
楊克敏
(華東師范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上海 200241)
一
民國時期以梅光迪 為代表的“學衡派”知識分子群體,往往因為他們的“文化保守主義”主張而被斥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逆流”,受到學界的冷落。近年來,隨著一些重要史料的相繼發現,人們對“學衡派”的固有觀念開始發生轉變,對其研究也逐漸升溫。與“學衡派”同人相比,梅光迪身前留下的著作并不多,正如吳宓所言:“梅好為高論,而完全缺乏實行工作之能力與習慣,其一生之著作極少,殊可惜”,《近世歐美文學趨勢》正是這極少的論著之一。
陶行知在《辦理暑期學校及國語講習科報告》指出,民國九年(1920)夏,南京高師校長郭秉文、副校長劉伯明、教務長兼教育科主任陶行知等倡導舉辦暑期學校。教員除了本校老師外,還聘請北京大學教員胡適之、陳衡哲;南開大學教員凌冰、梅光迪等。所開課程:“共十九種,為小學組織法、天演學說、中國古代哲學史、文學概論、歐美文學趨勢……多者每周五時,少者二時。”[1]其中天演學說、文學概論、歐美文學趨勢便是梅光迪講授的。《近世歐美文學趨勢》就是梅光迪為“歐美文學趨勢”這門課所撰寫的講義。當時,講義印發有兩種方式:“講義用油印,間有用石印、鉛印者。逐日出版,每月多逾二萬頁,少亦一萬六七千頁。教員不備講義者,由校派速記員臨時記下,付印分給。”[2]講義屬于后者,由學生馮策、華宏謨同記,吳履貞補記整理。據筆者查證,這本講義最初是以教學大綱的形式出現《師范教育》上。1922年,在該刊第2期的專欄“選課課程綱要”上,刊載了這本講義的大綱《近世歐美文學綱要》,并規定:“本科目每星期一小時,半學年十八小時畢事。”而其詳細內容則是在90余年后才被收錄在《梅光迪文存》里,于2011年4月由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為講義,梅光迪在編寫體例上采用的是典型的教科書寫法。在講述之前,作者開辟了一個“導言”,對這門課程的講授范圍、研究宗旨以及研究方法作了比較詳細的介紹。該講義以講述歐美從文藝復興至浪漫主義近兩三百年間的文學為主要內容,梅光迪認為:“西洋文藝發源希臘,世之公論,而希臘文學思想當以亞里士多德氏為其首領,亦公言也。故本科研究方法,縱浚河導源,提綱挈領,首論文藝復興,以上溯希臘以亞氏為主。十七、十八世紀模仿時代,乃及本科范圍自浪漫主義之興以迄今日,凡一百二三十年,其間文學之派別趨勢,皆能略考其優劣,辨其是非”。[3](P93)從這段引文我們可以看出,梅光迪在勾勒歐美文學發展的脈絡時,將文藝復興作為講義的開端,可以說是眼光獨具、點中要害。因為文藝復興上承古希臘文化、下啟歐洲近代文化,它使在中世紀被視為異端的古希臘、羅馬文化得以重見天日,并且使歐洲文學因脫離宗教而獲得獨立。梅光迪以某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點為中心,散射出與之相關的知識鏈條,這樣既重點突出,又使整體結構緊湊、集中,對于文學史的編寫具有借鑒意義。在研究方法上,梅光迪強調文學與文化的密切關系以及比較方法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民國時期的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在方法論實踐上日趨成熟,具有了現代學科建設的自覺意識。
除導言外,講義共十三章,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為第一部分,主要講述文化復興時代、亞里士多德的《詩說》以及古學派文學(文藝復興后到十八世紀末);第四章到第十章為第二部分,分別涉及浪漫派文學的總體概要、浪漫派與自然主義、浪漫派與自然界、浪漫派與近世民族主義、浪漫派與近世大同主義、浪漫派與超人文主義以及對浪漫派與寫實派的比較分析等專題,正如梅光迪所言:“今茲所述,蓋以最近百二三十年間之文學為主,溯流窮源,對于前二期及古代之文學亦略及焉”。[3](P92)所以,浪漫派是梅光迪重點講述的內容,它在講義中占了相當的篇幅;第十一至十三章為第三部分,依次以葛德、卡萊爾、安諾爾德(Arnold)為代表性的個案,回應第一部分,使其的理論闡述具體化。這樣的編排體例使講義達到了清晰、有序、全面且有所側重的要求。該講義近12萬言,在要言不煩的論述中閃爍著思想的火花與文字的光彩。
二
綜觀講義的內容設置、結構安排、行文表達、理論思辨,梅光迪以鮮明的新人文主義理論色彩、強烈的文化批判意識以及對文學流派的辯證分析、對國別文學的局限性認識等,顯示了梅光迪深厚的學術功底和開闊的學術視野。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民國時期“精神獨立,學術自由”的氛圍。
(一)鮮明的新人文主義理論色彩
從所受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經歷來看,梅光迪于1911年考取第三屆庚子賠款留美生考試,1915年夏師從哈佛大學新人文主義學者白璧德教授,專攻西洋文學并獲文學博士學位。新人文主義主張恢復古典文化的精神和秩序,強調個人道德完善,以匡救現代文明的弊端的思想對梅光迪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本講義以新人文主義為主導思想,理論色彩濃厚,在字里行間充分顯示了梅光迪作為新人文主義學者所接受的學術訓練及所具有的學術痕跡。
梅光迪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逐次講述了文藝復興、亞里士多德的《詩說》與古學派文學之后,又在講義的最后三章以古典文學與文化的集大成者歌德與卡萊爾、安諾爾德為分析個案。梅光迪認為希臘的自由精神與希伯來的宗教精神是近世西洋文化的兩大源頭。中世紀盛行后者,文藝復興后者復活。希臘重知、希伯來重行,兩者共同促成近世西洋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在這里,梅光迪以“兩希文化”作為研究西方文學的背景,更多的顯示了他對外國文學本體所蘊含的深層意蘊的整體關照。在梅光迪看來,卡萊爾與安諾爾德是“兩希文化”的化身,“卡氏代表希伯來之精神者也,故其為人能苦能行。其代表希臘精神者,厥為安諾爾德”。[3](P115)安諾爾德是比白璧德更早的西方人文主義學者,針對當時英國人重實行而不用腦、重道德而蔑知識、重習慣而輕理論以及重科學而輕文學的弊端,安諾爾德認為以道德、知識、美術、社會生活四要素為基礎的完全人格是“文化救時”的關鍵所在,也是新人文主義崇尚人的道德、強調文化的人文關懷、反對功利主義的審美觀的體現。從第四章到十章,梅光迪針對浪漫主義思潮大潑筆墨,在行文中對浪漫派的否定批判則是言辭激烈、鋒芒畢露 。如在第十章“近世西洋之小說”中梅光迪分別從起源、宗旨、方法等方面對寫實派與浪漫派進行比較分析,指出,“浪漫派之流弊:(一)專事傳奇,不重真理,讀之無益。 (二)假造過多,而無人生實際。 ”[3](P113)
這樣首尾呼應古典文化與文學,中間夾擊浪漫派的結構框架與整體分布比例,是梅光迪提倡中庸、節制、理性的古典主義,反對偏執、激進、逾越常規的浪漫主義的新人文主義主張的寫照,從中顯示了梅光迪鮮明的學術觀點、縝密的邏輯思維。梅光迪在《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4]中說:“彼等言政治經濟,則獨取俄國與馬克思,言哲學則獨取實驗主義,言西洋文學,則獨取最晚近之短篇小說獨幕劇及墮落派之著作。[5]而于各派思想藝術發達變遷之歷史,與其比較之得失,則茫然無知”。從這段引文我們可以看出,在略帶火藥味的語氣中,梅光迪對于“新青年派”破舊立新的激進、功利意識所流露的不滿與不屑。與“新青年派”對于西洋文學與文化的“就近性”認識不同,梅光迪則強調古典文學與文化在外國文學教學與研究中的重要意義與價值,正是他的這種歷史思考與判斷建構了這本講義的主要落腳點與支撐點。
(二)強烈的文化批判意識
在導言中,梅光迪指出文學與文化的密切關系,對于研究歐美文學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在講義的第四章到第十章中,梅光迪對與浪漫派相關的社會思潮條分縷析地闡釋中,以極強的理論思辨色彩,顯示出強烈的文化批判意識。
在新文化運動中,進化論成為以陳獨秀為首的激進派與以胡適為首的自由派提出 “打倒孔家店”、“破舊立新”等口號的理論依據。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與《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中強調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文學發展有賴于前后的繼承與革新,強調在時間的動態延展中,文學發展越往后越高級。用進化證明新比舊好、新必勝古。由此,進化論的文學史觀也在文壇上蔓延。在周作人 《近世歐洲文學史》的緒論中出現了“變更”、“歷級而進”、“向上”等詞語;茅盾則認為文學呈單線發展并按一定的程式演變,而且越發展越好。“翻開西洋的文學史,見他由古典——浪漫——寫實——新浪漫……這樣一連串的變遷,每進一步,便把文學的定義修改了一下,便把文學和人生的關系束緊了一些。”[6]他們明顯受到了文學隨時間流轉而呈向上發展趨勢的進化論文學史觀的影響。
針對把生物進化論所包含的“新陳代謝”的一般規律,移植到解釋文學史前后更替的歷史過程中的傾向,梅光迪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學進化之說,全無根據。蓋事物之進化,有其規律和方法言之耳。故機械科學有進化之象征。文學美術則規律以外,尚有賴乎天才。”[3]98當時的中國,科學就是一切,梅光迪強烈反對培根的科學主義。梅光迪認為科學是客觀的,有一定的規律。規律是從自然科學中轉引過來的理論范疇,規律的形成需要具備可重復性與可檢驗性。而文學雖然也有修辭學、文法學等種種的體例,但它更講求個體的主觀能動,它是不能父子相承、代代相傳的。如希臘的文學、意大利的繪畫、英國的詩人、法國的戲曲家、太史公的散文以及李、杜的詩歌等都是后代所不能與之抗衡的。在文學上有所建樹并成一家之言者,必然有其不同于常人的創造力,它不為規律所束縛、也不是規律所能束縛的。茅盾認為新文學就是進化的文學,而進化論的文學有三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質;二是有表現人生、指導人生的能力;三是為平民的非為一般特殊階級的人的。”[7]這種把進化論用于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做法,已經超出其適用于科學與社會實用知識的范圍。其實,進化論很難適用于文學研究的需求,這樣的生搬硬套往往把復雜的文學現象簡單化。
所以,梅光迪反對文學進化之說,“文學進化,至難言者,西國各家,(如英國十九世紀散文家即文學批評家韓士立Hazlitt)多斥文學進化論為流俗之錯誤,而吾國人乃迷信之。且謂西洋近世文學,由古典派而變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變為寫實派,今則又由寫實派而變為印象、未來、新浪漫諸派,一若后派必優于前派,后派興而前派即絕跡者。然稍讀西洋文學史,稍聞西洋名家緒論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國人童呆無知,顛倒是非如是乎。 ”[3](P133)梅光迪認為文學經典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他說:“我們必須理解和擁有通過時間考驗的一切真善美的東西”,才能有標準,“判斷真偽與辨別基本的與暫時性的東西”。[8]梅光迪注重共時的文學品性而非歷時的時間范疇,而古典文學是過去一切經驗、生活、智慧堆積而成的蓄水池,歷經千年而不朽,且無古今中外之分。精神文化與完美的人性,只有發揚而無所謂進步,所以進化的觀念不能應用到文學研究中。由此,梅光迪認為“文學進化之學者,不知文學之歷史者也。 ”[3](P98)
梅光迪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反對進化論文學史觀,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胡適的又一次的反擊,由此引發人們對文壇上流行的進化論文學史觀的再思考,具有警醒和糾偏的歷史作用,至今也有可資借鑒的價值。
(三)對文學流派的辯證分析
梅光迪認為“凡一主義之創行,其末流無不有弊。”[3](P103)對于講義的主體部分古學派與浪漫派,梅光迪并不是一味的褒揚、也不是一味的貶抑。認為古學派占據西洋文學史上最重要人物的大多數。“十八世紀之后,歷十九世紀以迄于今,古學派文學猶盛。其中最大人物,詩人則有德之葛德(Goethe),可為近兩百年來第一詩人。”[3](P98)梅光迪還專門解釋了classical的含義,認為把它翻譯成“古典主義“、“擬古主義”等是極大的錯誤。“蓋此派文學極優,非可以“古典”、“擬古”等狹隘名詞加之也。 ”[3](P98)另一方面認為古學派的弊端是忽視現代人的人生觀,“古學派至十八世紀末,流弊甚大。極易模仿古代文字,而不直接模擬人生,致成為機械的模仿。 ”[3](P103)此外,還認為古學派重視理性、棄絕情感是“桎梏天性,莫此為甚。”
由于新文化者所提倡的浪漫派與梅光迪的新人文主義所講求的中庸、節制、理性的古典主義精神相背離。在梅光迪看來,在西洋文學史上古學派占據西洋文學史上最重要人物的大多數。古學派的重要詩人但丁、戲劇家莎士比亞、拉興、穆利爾等都是浪漫派的主要人物不能與之比肩。對于浪漫派文學梅光迪這樣描述:“其所著述皆托意寓言,荒誕不經。良以無知之徒胸無成竹,妄言妄聽,故多無稽之談。 浪漫文學即投世之所好而起者。 ”[3](P103)與古學派文學家重思想、理論、實效的特征相比,梅光迪浪漫派文學是奇怪、情感、自然三者的結晶體,“其論述則大言無當,成為虛誕的文學,而皆少文學的真價值者也。 ”[5](P100)梅光迪從新人文主義的批評標準出發,視浪漫的情感是不健康的、畸形的,從而認為“托爾斯泰之博愛主義,妻子不能信,村農議其非,終皆發狂以死。始雖樂觀,終必悲觀,趨于兩極,此一定之理也”。[3](P101)而托爾斯泰的博愛被周作人標舉為“現代文學的特色”——人道主義思想的代表之一,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學”。[9]在談到盧梭的作品時,梅光迪認為“盧騷之感情小說出,最歡迎之者,為貴族婦女。故浪漫派之文學,可謂之婦女文學。蓋婦女者,最富于感情者也”。[3](P105)言語中暗含了梅光迪對浪漫派文學放縱情欲的嘲諷與輕視。
但在第六章“浪漫派與自然界”中認為,梅光迪認為與古學派文學偏重宮廷和城市而厭棄自然不同,浪漫主義文學傾向于自然界的描繪,密切了自然界與人生的關系。認為浪漫派描寫人物從環境入手,并且刻畫精微入微、惟妙惟肖是浪漫派特長之所在,也是它對文學界的貢獻之所在。這顯示了梅光迪在否定浪漫派文化前提下的一種內在矛盾性。
(四)對國別文學認識的局限性
講義的名稱是《近世歐美文學趨勢》,其實重點在歐洲文學。而對美國文學,梅光迪只是輕描淡寫地一句話,“美洲文學不過歐洲文學之副產、英國文學之支流,約言之可也”。[5](P91)且再也沒有下文,所以這本講義的名稱應更名為《近世歐洲文學趨勢》似乎更為恰當。這種對美國文學的否定性認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人們對于美國文學的總體印象。如1929年曾虛白在《美國文學ABC》中曾這樣寫道:“在翻開美國文學史以前,我們應該先要明白了解‘美國文學’這個名詞,在真正世界文學史上是沒有獨立的資格的。它只是英國文學的一個支派”。[10]而在1932年,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志則認為:創造性和自由性是美國文學的重要特征,并將第一個外國文學研究專號鎖定為專美國文學。之后,《文學月報》在1941年6月刊出“美國文學特輯”、《時與潮文藝》也在同年11月 “美國當代小說專號”等才使美國文學真正進入了人們的學術視野。
講義中對歐洲以外國別文學的否定性認識,同樣也出現在對俄國文學與日本文學上的論述中,這與對寫實主義弊端的批判相關。梅光迪以《詩說》中亞里士多德對照相和圖畫的區別為例,指出近世寫實主義的弊端在于描寫人生而無選擇,并認為“專寫不良事實,不造理想人格,反日以囚盜淫惡之事為其材料,是率人而禽獸也。 ”[5](P96)而時人所稱頌的托爾斯泰、孟伯騷等的寫實主義,究其實質不過是歐美文學的一部分,“淺者不察竟視為不遷之宗,代表一切,不其謬乎。此無他故,乃不知歐美文學之奧蘊,日從日本故紙堆中討生活也。 ”[3](P92-93)梅光迪認為俄國文學自彼得一世以后,“一切全襲法國,即論小說家如托爾斯泰者,亦不過抄襲法國寫實派之方法,而吾國少年近方步武日本之西洋文學派,亦醉心于俄國文學,愚亦甚矣。 ”[3](P96)與此相關,吳宓 1921年10月22日在《中華新報》上也發表《寫實主義之流弊》一文,1921年11月1日茅盾在《時事新報》附刊《文學旬刊》第54期發表《“寫實主義之流弊”?——請教吳宓君,黑幕派與禮拜六派是什么東西!》一文予以回應。茅盾認為“以不健全之人生觀示人也”是加給俄國寫實派的罪名。俄國寫實派大家果戈理、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作品都含有廣大的愛,高潔的自我犧牲精神。并以克魯泡特金在《俄國文學的理想與實質》中反對左拉等人的“丑惡描寫”為例,說明自果戈理以來的寫實主義是“新”寫實主義,與法國不同。
在這里,梅光迪對歐美文學給予極高的評價:“蓋近世歐美文學,實為近世歐美文化之代表。近世歐美文學之內容,實包近世歐美盛行之思想學術一大部分。故欲研究近世歐美文化,以為創造吾國新文化之借鑒者,當自研究近世歐美始矣。 ”[3](P93)由于語言障礙(不懂俄語)以及新人文主義視角等原因,這種揚歐抑美、俄、日的厚此而薄彼傾向,使梅光迪在對待國別文學上存在一定局限性和狹隘性,從而給自己的研究設置了障礙。
三
我們通過對梅光迪這本講義的分析,不僅僅是對外國文學研究可能性的思考,也包含了外國文學學科史的回顧。拂去歷史的塵埃,從回到歷史現場、喚起歷史現場的想象和體驗這一角度看,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大學講授《歐洲文學史》與梅光迪1920年在南京高師第一屆暑期班講授《近世歐美文學趨勢》,兩者的時間差只有3年。前者于1918年出版了同名專著,已是眾所周知。而后者在當時沒有公開發表,但是它生動反映了民國時期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學的“期待視野”。與周作人《歐洲文學史》、《近世歐洲文學史》注重對不同時期大量作家作品的講解不同,這本講義在內容上雖略顯簡略,但它比其更具系統性。在整個編寫上,《近世歐美文學趨勢》以新人文主義的視角出發,更傾向于從思想、理論的角度對歐美文學的發展總體趨勢進行的宏觀概括與精細體悟,由此我們可以觸摸不同的學術經歷與背景民國學人的研究路徑,以及他們對于世界文學資源的不同感知與想象。在今天同樣也具有著鮮活的生命力與啟示性。時隔90余年始被發現的《近世歐美文學趨勢》是除周作人的《歐洲文學史》外,又一論述西方文學發展的力作,其在外國文學學科發展史研究、外國文學學術史梳理方面的史料價值不容小覷。
[1][2]方明主編.陶行知全集:第1卷[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341,342.
[3][8]梅鐵山主編.梅光迪文存[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93,1.
[4]梅光迪.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J].學衡,1922,(2).
[5]胡適.論短篇小說[J].新青年,1918,(5).
[6]沈雁冰.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J].小說月報,1921,(2).
[7]茅盾.新舊文學平議之評議[J].小說月報,1920,(1).
[9]周作人.空大鼓[M].上海:開明書店,1930.8.
[10]曾虛白.美國文學 ABC[M].上海:世界書局,19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