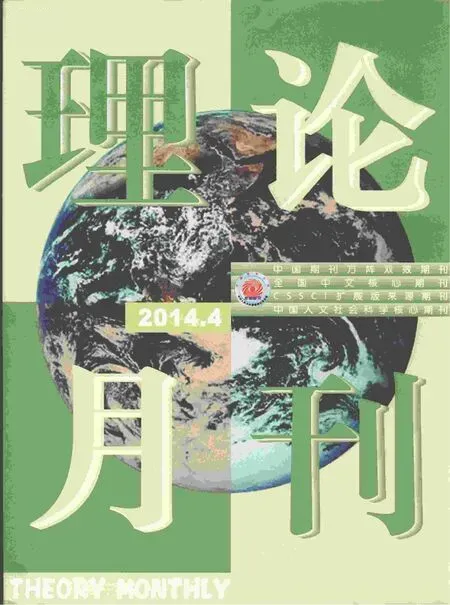論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中的公共治理變革
彭宗峰
(南京大學(xué) 政府管理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23)
自20世紀(jì)70、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性的市場化轉(zhuǎn)向以及全球性的資本擴(kuò)張,“經(jīng)濟(jì)——技術(shù)”系統(tǒng)再次被賦予“自由”去重構(gòu)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基本制度安排。“經(jīng)濟(jì)——技術(shù)”系統(tǒng)以其工具理性改造著福利國家改革所釋放的制度空間,為塑造一種新型社會(huì)形態(tài)提供了重要的動(dòng)力。然而,“經(jīng)濟(jì)——技術(shù)”系統(tǒng)也是形成現(xiàn)代社會(huì)分化性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的核心機(jī)制。尤其是在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過程中,由“經(jīng)濟(jì)——技術(shù)”系統(tǒng)所引致的社會(huì)分化和社會(huì)差異既不能在原有的社會(huì)整合機(jī)制中獲得秩序,也尚未找到一個(gè)相對合理的新型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機(jī)制達(dá)致秩序。在這種轉(zhuǎn)型社會(huì)形態(tài)中,必然存在著諸多失序和風(fēng)險(xiǎn),而風(fēng)險(xiǎn)如果不能及時(shí)合理地加以治理,就會(huì)引發(fā)危機(jī)。歷史經(jīng)驗(yàn)表明,自全球性的市場轉(zhuǎn)向以來,生態(tài)危機(jī)、科技危機(jī)、制度危機(jī)的事件不斷增長,全球陷入了一種風(fēng)險(xiǎn)恐懼之中。對這種社會(huì)形態(tài)的理論思考,則表現(xiàn)為一種關(guān)于“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知識(shí)范型。這一知識(shí)范型為揭示當(dāng)前社會(huì)的特征與發(fā)展趨勢提供了一個(gè)重要的視角,并為構(gòu)建新型社會(huì)及其治理結(jié)構(gòu)提供了一個(gè)可能的向度。
一、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及其二重性
“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知識(shí)范型是由烏爾里希·貝克首倡并加以系統(tǒng)闡述的。自貝克之后,“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成為了觀察當(dāng)前轉(zhuǎn)型社會(huì)的一種重要視角。貝克從一種生態(tài)主義的視角探討了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特征,認(rèn)為人類社會(huì)已經(jīng)從一種“財(cái)富分配”的社會(huì)轉(zhuǎn)向一種“風(fēng)險(xiǎn)分配”的社會(huì)。在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中,人們具有一種平等的地位,誰都不可能脫離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而自存。然而,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并不是簡單的風(fēng)險(xiǎn)再生產(chǎn)的社會(huì),其在歷史維度上具有解構(gòu)和建構(gòu)的雙重意義。貝克把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與“自反性現(xiàn)代化”聯(lián)系在一起,自反性現(xiàn)代化是指“創(chuàng)造性地(自我)毀滅整整一個(gè)時(shí)代——工業(yè)社會(huì)時(shí)代——的可能性。在這里毀滅的對象是西方現(xiàn)代化的勝利成果”。[1]這也就意味著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是對工業(yè)社會(huì)的一種批判和重建,工業(yè)社會(huì)的歷史遺產(chǎn)要在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中被審查、批判和再造。這樣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就具有了與工業(yè)社會(huì)不同的含義。在貝克看來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至少有以下含義:(1)既不是毀滅也不是信任/安全,而是“真實(shí)的虛擬”;(2)是有威脅的未來,(始終)與事實(shí)相反,成為影響當(dāng)前行為的一個(gè)參數(shù);(3)既是對事實(shí)也是對評價(jià)的陳述,它在“數(shù)字化的道德”中結(jié)合了起來;(4)控制或缺乏控制,就像在“人為的不穩(wěn)定”中表現(xiàn)出的那樣;(5)認(rèn)識(shí)(再認(rèn)識(shí))沖突中表現(xiàn)出來的知識(shí)或不知;(6)由于風(fēng)險(xiǎn)的“全球性”而使全球和本土同時(shí)重組;(7)知識(shí)、潛在沖突和癥候之間的差別;(8)一個(gè)人為的混合世界,失去了自然與文化之間的二元性。[2]其實(shí),這就意味著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具有一種啟蒙的意義,其本質(zhì)向度在于尋求一種替代工業(yè)現(xiàn)代性的可能性空間。
其實(shí),貝克的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理論是對20世紀(jì)中后期高度發(fā)達(dá)的工業(yè)社會(huì)以及福利國家改革所釋放的制度空間所做的思考。工業(yè)社會(huì)發(fā)展到福利國家階段時(shí)已經(jīng)達(dá)到頂峰,在一個(gè)高度組織化的社會(huì)中,“國家機(jī)器把其防務(wù)和擴(kuò)張的經(jīng)濟(jì)、政治需要強(qiáng)加在勞動(dòng)時(shí)間和自由時(shí)間上,強(qiáng)加在物質(zhì)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勢必成為極權(quán)主義。”[3]這樣的一個(gè)龐大而復(fù)雜的機(jī)器的運(yùn)轉(zhuǎn)必然要以削弱民主和自由為代價(jià),而經(jīng)濟(jì)生活也在國家共同體的干預(yù)下獲得再生產(chǎn)。然而,福利國家在20世紀(jì)中后期就不再具有優(yōu)勢,嚴(yán)重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以及政府債務(wù)負(fù)擔(dān)已然引起了社會(huì)的信任危機(jī)和治理危機(jī)。隨著新公共管理運(yùn)動(dòng)的興起,全球范圍內(nèi)的國家都開始消解福利國家的意識(shí)形態(tài)和制度設(shè)置,轉(zhuǎn)而尋求市場化和社會(huì)化的理念和機(jī)制。這樣就在福利國家改革所釋放的制度空間中,“經(jīng)濟(jì)——技術(shù)”系統(tǒng)再次獲得重塑社會(huì)生活的“自由”權(quán)利。然而“經(jīng)濟(jì)——技術(shù)”系統(tǒng)是現(xiàn)代社會(huì)重要的分化機(jī)制,容易引發(fā)社會(huì)失序和信任危機(jī)。其實(shí),福利國家的改革效應(yīng),引發(fā)了兩種危機(jī)的交疊。其一是國家危機(jī),也就是國家治理神話的“祛魅”,其二是市場危機(jī),也就是市場神話的“祛魅”。在這兩種危機(jī)的交疊中,人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建立于工業(yè)社會(huì)意識(shí)形態(tài)基礎(chǔ)上的“市場——國家”范型的失效。
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具有一種解構(gòu)工業(yè)社會(huì)的向度。首先,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消解了建立在工業(yè)化基礎(chǔ)之上的組織化,釋放了一種新的個(gè)體化能量。工業(yè)社會(huì)中的身份認(rèn)同機(jī)制在新的個(gè)體化過程中不再有效,一種工業(yè)集體主義的理念不再能包容新型的社會(huì)公眾。隨著工作場所和工作機(jī)制的靈活化,個(gè)體開始成為自身工作的組織者。這樣個(gè)體化也就更深入的削弱了福利國家的基礎(chǔ),而貝克認(rèn)為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整體趨勢是生存的個(gè)體化形式和狀況的出現(xiàn),它迫使人們?yōu)榱俗陨砦镔|(zhì)生存的目的而將自己作為生活規(guī)劃和指導(dǎo)的核心。”[4]其次,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消解了國家治理的有效性。福利國家的改革本身就是對國家治理有效性的質(zhì)疑,在市場化轉(zhuǎn)型之后,其實(shí)社會(huì)治理的結(jié)構(gòu)就不能再被設(shè)想為一個(gè)單向度、單層級(jí)的結(jié)構(gòu),而是需要一個(gè)多維立體的視角。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在拓展治理結(jié)構(gòu)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且表現(xiàn)為從民族國家向上拓展為國際和全球,向下拓展為地方。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拓展機(jī)制表達(dá)了對一種新型社會(huì)治理結(jié)構(gòu)的需求。其三,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消解了工業(yè)現(xiàn)代性的一些基本的價(jià)值和意識(shí)形態(tài),比如基礎(chǔ)主義、理性主義、普遍主義、主客二分等。基于理性主義的思考在工業(yè)現(xiàn)代性中表現(xiàn)為工具理性和形式主義,致使社會(huì)在技術(shù)統(tǒng)治的意識(shí)形態(tài)下不斷制造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和危機(jī)。
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解構(gòu)向度其實(shí)是一種冒險(xiǎn),在消解了工業(yè)現(xiàn)代性所建構(gòu)的秩序中,新型的社會(huì)秩序并不能立刻呈現(xiàn)而只能以風(fēng)險(xiǎn)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因?yàn)樯形葱纬梢环N新的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機(jī)制,所以風(fēng)險(xiǎn)總是具有一種不確定性和無法預(yù)測性。福利國家改革后,國家認(rèn)同相應(yīng)的減弱,在市場性的個(gè)體化和全球化的推動(dòng)下,新的社會(huì)個(gè)體和群體開始生成。在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松散網(wǎng)絡(luò)中不同的個(gè)體和群體依據(jù)自身的價(jià)值和利益行動(dòng),必然會(huì)有沖突。從全球范圍看,資本的全球流動(dòng)生成了其全球性的人格代表,形成了一個(gè)資本流動(dòng)的不均衡的結(jié)構(gòu)。從社會(huì)認(rèn)同的角度看,原先對于民族國家的認(rèn)同現(xiàn)在開始分散化,一方面“社會(huì)凝聚力不能在民族(或國家)層面運(yùn)作的國家來保證,但可以通過能生產(chǎn)忠誠感、社區(qū)認(rèn)同與歸屬感的地方政府來維持”;[5]另一方面“公民在這種全球背景中行動(dòng)起來,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施加他們的影響”。[6]在這樣的分化網(wǎng)絡(luò)中由于認(rèn)同基礎(chǔ)和原則的差異必然存在相應(yīng)的沖突風(fēng)險(xiǎn)。當(dāng)然,風(fēng)險(xiǎn)并不必然引發(fā)危機(jī),而且可能是一種機(jī)遇。這也就是說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中存在著重構(gòu)社會(huì)秩序的因素。其一,雖然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帶來個(gè)體化,但“個(gè)體化預(yù)設(shè)了前提條件,也就是社會(huì)規(guī)范、法律和準(zhǔn)則的內(nèi)化”。[7]比如新型個(gè)體在新型網(wǎng)絡(luò)媒體的基礎(chǔ)上開始表達(dá)自身的意愿,通過相互的溝通交流,一種新型的公共輿論生成機(jī)制開始浮現(xiàn),一種積極主動(dòng)的公共領(lǐng)域建構(gòu)進(jìn)程開始啟動(dòng)。其二,一種新型的社會(huì)文化開始形成。尤其是在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hù)方面,“超越現(xiàn)存人類的包容”、“對責(zé)任的強(qiáng)調(diào)”以及“邁向全球公民身份”等理念開始生成。在環(huán)境保護(hù)運(yùn)動(dòng)的推動(dòng)下,諸多新型的社會(huì)機(jī)制逐步建立并不斷完善。一種全球生態(tài)公民身份的理念逐步被人們所接受并加以積極建構(gòu)。
總的說來,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解構(gòu)了工業(yè)現(xiàn)代性的基本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和秩序,并引發(fā)了諸多社會(huì)危機(jī);另一方面在社會(huì)危機(jī)的深層理念中蘊(yùn)涵著對于一種新型社會(huì)形態(tài)的訴求,其以諸種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并引發(fā)社會(huì)治理結(jié)構(gòu)的變革。
二、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中的公共治理嬗變
有什么性質(zhì)的社會(huì)就需要什么性質(zhì)的治理。工業(yè)社會(huì)的治理結(jié)構(gòu)其實(shí)是在“經(jīng)濟(jì)市場——民族國家”的二元論視角上建構(gòu)起來的。歷史經(jīng)驗(yàn)表明工業(yè)社會(huì)的治理結(jié)構(gòu)經(jīng)歷了兩個(gè)階段,即“市場自由——國家保護(hù)”階段以及“壟市場斷——國家干預(yù)”階段。雖然新公共管理運(yùn)動(dòng)釋放的是“自由市場”的信號(hào),但“國家保護(hù)”并不能被再次拾起。因?yàn)楣I(yè)社會(huì)發(fā)展到福利國家已經(jīng)把它自身的潛能發(fā)揮到了極致。在工業(yè)社會(huì)向后工業(yè)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過程中,一種新型的社會(huì)形態(tài)開始以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而工業(yè)社會(huì)的“經(jīng)濟(jì)市場——民族國家”的治理體系不能再解決這些風(fēng)險(xiǎn)。
首先,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拓展了“經(jīng)濟(jì)性個(gè)體化——政治性民主化”的關(guān)系。隨著資本的全球化擴(kuò)張,經(jīng)濟(jì)性個(gè)體開始在全球范圍內(nèi)流動(dòng)。這包括一些全球性商人以及國際流動(dòng)的勞動(dòng)力。這些個(gè)體及其可能的群體其實(shí)已經(jīng)形成了不自覺的全球性經(jīng)濟(jì)公民的角色,他們在全球范圍內(nèi)流動(dòng),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在最基礎(chǔ)的公共治理層面上,他們被各國承認(rèn)擁有相應(yīng)的經(jīng)濟(jì)權(quán)利和人身自由,也就是一種全球性的經(jīng)濟(jì)公民身份。但是在政治和文化權(quán)利方面,這些個(gè)體仍然要受到民主國家的限制,他們在積極公民參與上并未形成一種全球特征。譬如歐盟,“一方面是在超民族層面上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和管理的系統(tǒng)性整合;另一方面則僅僅在民族國家層面上才有效進(jìn)行的政治整合”。[8]
其次,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拓展了“社會(huì)性個(gè)體化——政治性民主化”的關(guān)系。社會(huì)性的個(gè)體化其實(shí)是在一種文化意義上來說的,也就是一種社會(huì)認(rèn)同。福利國家消解后,個(gè)體對共同體的認(rèn)同也從民族共同體轉(zhuǎn)向地方共同體以及全球共同體。在新公共管理運(yùn)動(dòng)中,授權(quán)社區(qū)成為一種改革的向度,而在新公共服務(wù)理念中,社會(huì)的自組織也成為一種價(jià)值偏好。因?yàn)樵诘胤叫缘男∪后w內(nèi),人們能夠相對經(jīng)常的接觸和交流,再加上社會(huì)中存在的互助和志愿機(jī)制,一種小范圍內(nèi)的公共領(lǐng)域就被激活了。這種地方性的認(rèn)同顯然對國家認(rèn)同形成了一定的排斥,那么國家層面的公共治理怎樣協(xié)調(diào)地方層面的公共治理就需要在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中重新表述和建構(gòu)。與社會(huì)性個(gè)體化的地方轉(zhuǎn)向相反的全球化轉(zhuǎn)向也挑戰(zhàn)了國家層面的公共治理。在現(xiàn)代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交往結(jié)構(gòu)中,一些志愿組織開始走出國家的范圍,在全球范圍內(nèi)發(fā)揮其治理功能。在一定意義上,一種全球公民社會(huì)正在形成。全球性的社會(huì)認(rèn)同的形成也必然拓展民族認(rèn)同的結(jié)構(gòu),為形成新的社會(huì)認(rèn)同做準(zhǔn)備。
再次,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拓展了“虛擬性個(gè)體化——政治性民主化”的關(guān)系。隨著網(wǎng)絡(luò)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虛擬性的個(gè)體開始在一個(gè)符號(hào)化的世界里生成他們的文化以及公共領(lǐng)域。隨著政府電子化和信息化的發(fā)展,電子民主和網(wǎng)絡(luò)民主也初現(xiàn)端倪。圍繞著公共輿論的生產(chǎn)、傳播和治理,網(wǎng)絡(luò)公民與電子政府的關(guān)系也發(fā)生了相應(yīng)的轉(zhuǎn)變。尤其是在即時(shí)互動(dòng)技術(shù)出現(xiàn)之后,網(wǎng)絡(luò)民主的發(fā)展更是深刻的改變著公共治理的空間和結(jié)構(gòu)。
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拓展了公共治理的空間,同時(shí)也拓展了公共治理的方式。從一個(gè)“公共領(lǐng)域——私人領(lǐng)域”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二維構(gòu)造的分析框架中,我們可以看到,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對于公共治理方式的改造。在福利國家的官僚體制中,國家壟斷了治理的權(quán)力,為了整合所有的社會(huì)階層,官僚體制以民族主義和技術(shù)主義的意識(shí)形態(tài)實(shí)行全面的管理。也就是說,在福利國家的官僚體制中,私人領(lǐng)域更多的被公共領(lǐng)域侵占,社會(huì)自下而上的治理過程幾乎不能發(fā)揮作用,尤其是在選舉政治中,人們普遍表現(xiàn)出一種政治冷漠。正如馬爾庫塞所描繪的單向度的社會(huì)一樣。“技術(shù)的進(jìn)步擴(kuò)展到整個(gè)統(tǒng)治和協(xié)調(diào)制度,創(chuàng)造出種種生活(和權(quán)力)形式,這些生活形式似乎調(diào)和著反對這一制度的各種勢力,并擊敗和拒斥以擺脫勞逸和統(tǒng)治、獲得自由的歷史前景的名義而被提出的所有抗議。”“大多數(shù)人對民族目標(biāo)和由兩黨支持的政策的接受,多元主義的衰落,企業(yè)和勞工組織的溝通,都證明了對立面的一體化”。[9]而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則在國家改革釋放的制度空間內(nèi),基于市場性自由改造了公共治理的方式。此起彼伏的新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新的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的生成都在國家政治結(jié)構(gòu)之外形成一種公民政治的結(jié)構(gòu),其自下而上的表達(dá)一種新型的公民身份,拓展了公共領(lǐng)域的范圍。比如生態(tài)主義的興起,使人們重新定位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從一種技術(shù)統(tǒng)治中超脫出來,走向一種和諧文化。與生態(tài)文化相伴隨的就是一種生態(tài)公民身份和生態(tài)政治。這些生態(tài)公民身份的表達(dá)和生態(tài)政治運(yùn)動(dòng)的興起,自下而上的改變了公共治理的方式和公共治理的內(nèi)涵與外延。而且,自下而上的公共治理向度,對于消解國家治理的管理主義,構(gòu)建一種合作治理結(jié)構(gòu)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重塑公共治理結(jié)構(gòu)
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二重性及其對公共治理結(jié)構(gòu)的擴(kuò)展必然引發(fā)公共治理結(jié)構(gòu)的變革。公共治理結(jié)構(gòu)的重建需要以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提供的社會(huì)條件為前提,但新型的公共治理結(jié)構(gòu)是對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這一過渡性社會(huì)階段的超越,它需要以一種合作社會(huì)為價(jià)值導(dǎo)向。在當(dāng)前的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中,公共權(quán)力的治理結(jié)構(gòu)仍然以國家管理主義為主導(dǎo),這種公共權(quán)力的治理結(jié)構(gòu)是與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相沖突的,而合作性社會(huì)更不可能以國家管理主義的公共權(quán)力治理結(jié)構(gòu)為秩序框架。因而伴隨著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轉(zhuǎn)向合作社會(huì),國家管理主義的治理結(jié)構(gòu)也應(yīng)相應(yīng)的轉(zhuǎn)向良善的公共權(quán)力治理結(jié)構(gòu)。
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向合作社會(huì)的轉(zhuǎn)型,要以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所提供的條件為前提。首先,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使得人們對社會(huì)的構(gòu)成有了新的理解。在新公共管理運(yùn)動(dòng)的市場化轉(zhuǎn)型中,人們同樣也關(guān)注了家庭、鄰里和社區(qū)等社會(huì)機(jī)制。“家庭、家族、鄰里、工作群體、友誼圈、志愿性協(xié)會(huì)都是個(gè)體確定歸屬感與對他人表達(dá)承諾的方式。”[10]這些機(jī)制運(yùn)行的原則與企業(yè)和市場運(yùn)行的原則不同,它們更多的是一種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的機(jī)制,在市場化大力推進(jìn)社會(huì)分化的過程中,這些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機(jī)制起了重要的穩(wěn)定作用。這些地方性的社會(huì)整合機(jī)制借助于一種人道主義和類意識(shí)并通過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的中介就有可能形成一種全球性的社會(huì)認(rèn)同和信任機(jī)制。其次,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使得人們對社會(huì)外延的認(rèn)知不再局限在民族國家的范圍內(nèi)。工業(yè)社會(huì)主要是在民主國家的范圍內(nèi)來治理社會(huì),但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打破了這一思維定式,使得人們對社會(huì)的深度和廣度都有了新的認(rèn)知。就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啟蒙功能而言,“全球風(fēng)險(xiǎn)的一個(gè)主要效應(yīng)就是它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 ‘共同世界’(common world),一個(gè)我們無論如何都只能共同分享的世界,一個(gè)沒有‘外部’、沒有‘出口’、沒有‘他者’的世界。 ”[11]再次,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提供了一個(gè)不均衡的社會(huì)總體圖景,一方面隨著資本的全球化,一種全球性市民社會(huì)已然形成,但是公共權(quán)力的治理機(jī)制和文化認(rèn)同機(jī)制并未形成一種全球性的特征。這固然是一種矛盾并可能引致風(fēng)險(xiǎn),但這也為防止全球同質(zhì)化提供了空間。因而合作性社會(huì)的建構(gòu)并不能以同質(zhì)化為原則,而應(yīng)尋求在多個(gè)層次和多種領(lǐng)域的合作。
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向合作社會(huì)的轉(zhuǎn)型,需要一種文化整合機(jī)制。當(dāng)然這種文化整合機(jī)制既不是對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的認(rèn)同,也不是一種文化同質(zhì)化的文化霸權(quán)主義。它需要一種尊重和包容的機(jī)制。合作社會(huì)的文化整合機(jī)制應(yīng)該是一種文化民主化機(jī)制。文化民主化的一種可能的向度是一種新型的共和主義理念。赫曼·范·岡斯特仁的建構(gòu)具有一定的啟發(fā)意義:“公民是自主的、忠誠的、能夠明確判斷和履行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的雙重角色”、“多元主義的組織”、“政府必須承擔(dān)領(lǐng)導(dǎo)責(zé)任”、“一種平等的政治地位”、“一種責(zé)任”“所有的領(lǐng)域”。[12]這就意味著文化整合機(jī)制需要在所有的領(lǐng)域中以積極的公民身份和負(fù)責(zé)任的政府來塑造。
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向合作社會(huì)的轉(zhuǎn)型,需要對公民政治領(lǐng)域加以建構(gòu)。公民政治領(lǐng)域其實(shí)不同于官僚政治,也不同于傳統(tǒng)的選舉政治,它是在共同體的成員資格的道德理念引領(lǐng)下形成的一個(gè)特殊的政治領(lǐng)域。它是從市民社會(huì)出發(fā)來建構(gòu)的一種公民社會(huì),其在與公共權(quán)力政治相接觸時(shí),以一種公共輿論和政治行動(dòng)表現(xiàn)其功能。在網(wǎng)絡(luò)社會(huì)的背景中,隨著輿論生產(chǎn)、傳播與治理機(jī)制的轉(zhuǎn)型,一種新型的網(wǎng)絡(luò)公民政治領(lǐng)域也開始發(fā)揮其特定的公共輿論批判功能。
這樣由市民社會(huì)、政治社會(huì)等領(lǐng)域以及文化及其民主化為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原則的諸多機(jī)制就推動(dòng)著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向合作社會(huì)的轉(zhuǎn)型。然而這些機(jī)制并不能單獨(dú)發(fā)揮作用,它們還需要在公共權(quán)力治理結(jié)構(gòu)中表達(dá)自身。這就需要公共權(quán)力治理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型。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要突破的公共權(quán)力治理結(jié)構(gòu)就是在民族國家基礎(chǔ)上建立起來的國家管理主義。國家管理主義的公共權(quán)力治理結(jié)構(gòu)以國家壟斷社會(huì)治理權(quán)力為特征。隨著國家改革與市場化轉(zhuǎn)型,國家管理主義的基礎(chǔ)逐漸轉(zhuǎn)變。公共治理也開始利用市民社會(huì)和公民社會(huì)來發(fā)揮治理功能。這就為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改造公共治理結(jié)構(gòu)提供了制度性空間。從價(jià)值取向上看,公共治理結(jié)構(gòu)的應(yīng)該從壟斷的管理轉(zhuǎn)向良善的治理。
公共權(quán)力治理結(jié)構(gòu)從壟斷管理向良善治理的轉(zhuǎn)型,首先需要對市民社會(huì)和公民社會(huì)授權(quán)并予以信任。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使得市民社會(huì)和公民社會(huì)在治理上的功能呈現(xiàn)出不同于國家的管理功能,它們在培育社會(huì)信任和防范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方面比國家更靈活、更接近問題的解決情境。在國家分權(quán)的過程中,公共領(lǐng)域的范圍也不斷擴(kuò)展,市民社會(huì)和公民社會(huì)本身內(nèi)在的公共性也會(huì)被激活。公共領(lǐng)域從國家向社會(huì)和個(gè)人的擴(kuò)展,其實(shí)表達(dá)了一種相對完整的公共性結(jié)構(gòu)。公共性結(jié)構(gòu)內(nèi)含著三種不同的公共領(lǐng)域:一種是政治權(quán)力性公共領(lǐng)域;一種是公共輿論性公共領(lǐng)域;還有一種是生活世界的公共交往。在一定程度上,生活世界的公共交往為生成公共輿論提供了前提條件,而公共輿論為改造公共權(quán)力提供了重要的批評機(jī)制,而公共權(quán)力領(lǐng)域的改造又反過來促進(jìn)生活世界的公共交往與公共輿論的再生產(chǎn)。公共性在市民社會(huì)和公民社會(huì)的運(yùn)行則為改造國家壟斷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其次,公共權(quán)力治理結(jié)構(gòu)從壟斷管理向良善治理的轉(zhuǎn)變,需要對公共權(quán)力的不同層級(jí)體系加以合理建構(gòu)。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使得公共危機(jī)的治理不再局限于國家的層面,全球性的公共治理以及地方性的公共治理都在不同程度上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協(xié)調(diào)地方、國家與全球的公共治理,擴(kuò)展公共性的縱向結(jié)構(gòu)也是改變公共權(quán)力壟斷治理的一個(gè)重要方面。公共權(quán)力的分層體系不能依據(jù)官僚制形式加以建構(gòu),應(yīng)當(dāng)賦予公共權(quán)力治理分層體系以靈活性,網(wǎng)絡(luò)式和協(xié)商式是一種可能的模式。
再次,公共權(quán)力治理結(jié)構(gòu)從壟斷管理向良善治理的轉(zhuǎn)變,需要建構(gòu)一種新型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公共權(quán)力運(yùn)行的價(jià)值導(dǎo)向,直接關(guān)系到公民與共同體的公共利益。傳統(tǒng)的政治文化以民族國家為范圍在個(gè)體與共同體之間進(jìn)行建構(gòu)。至少來說有三種政治文化:一種是自由個(gè)體主義的政治文化;一種是共同體主義的政治文化;一種是共和主義的政治文化。當(dāng)然它們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因而不能以一種單獨(dú)的政治文化為主導(dǎo)來建構(gòu)新的政治文化,但要在個(gè)體與共同體之間保持平衡。這樣新型的政治文化就需要一種反思的能力,不斷地調(diào)整各種要素之間的關(guān)系。政治文化的建構(gòu)也不能僅僅停留在國家的層次上,要向下擴(kuò)展以獲得一種豐富的政治認(rèn)同,同時(shí)也要向上擴(kuò)展以獲得一種基本的共識(shí)。同時(shí)這種政治文化也應(yīng)該建立在民主化和協(xié)商的基礎(chǔ)之上。
總的看來,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生成與發(fā)展消解了工業(yè)社會(huì)及其治理結(jié)構(gòu),同時(shí)也為構(gòu)建新型社會(huì)及其公共治理結(jié)構(gòu)擴(kuò)展了制度性空間。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作為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特殊階段,其發(fā)展的目標(biāo)模式是一種合作性社會(huì),順應(yīng)合作性社會(huì)的生成趨勢,公共權(quán)力治理結(jié)構(gòu)也需要在突破傳統(tǒng)模式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有效轉(zhuǎn)型。當(dāng)然,一種合作社會(huì)與良善公共權(quán)力治理結(jié)構(gòu)生成與發(fā)展的可能性,需要建立在對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及其二重性的深刻認(rèn)知與積極應(yīng)對的基礎(chǔ)上。
[1]烏爾里希·貝克等.自反性現(xiàn)代化[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4.5.
[2]烏爾里希·貝克.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再思考[J].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shí),2002,(4):49.
[3]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4.
[4]烏爾里希·貝克.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106-107.
[5]彼得·桑德斯.自由社會(huì)的公民身份[A].布賴恩·特納編.公民身份與社會(huì)理論[C].長春:吉林出版集團(t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2007.92.
[6]里查德·福爾克.全球公民身份的建構(gòu)[A].巴特·范·斯廷博根編.公民身份的條件 [C].長春:吉林出版集團(t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2007.149.
[7]安東尼·艾略特.公民身份的再造[A].尼克·史蒂文森編.文化與公民身份[C].長春:吉林出版集團(t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2007.74.
[8]尤根·哈貝馬斯.公民身份與民族認(rèn)同[A].巴特·范·斯廷博根.公民身份的條件[C].長春:吉林出版集團(t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2007.37.
[9]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3-4.
[10]彼得·桑德斯.自由社會(huì)的公民身份[A].布賴恩·特納編.公民身份與社會(huì)理論[C].長春:吉林出版集團(t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2007.95.
[11]貝克,鄧正來,沈國麟.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與中國——與德國社會(huì)學(xué)家烏爾里希·貝克的對話[J].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10,(5):209-210.
[12]赫曼·范·岡斯特仁.公民身份的四種概念[A].巴特·范·斯廷博根編.公民身份的條件[C].長春:吉林出版集團(t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2007.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