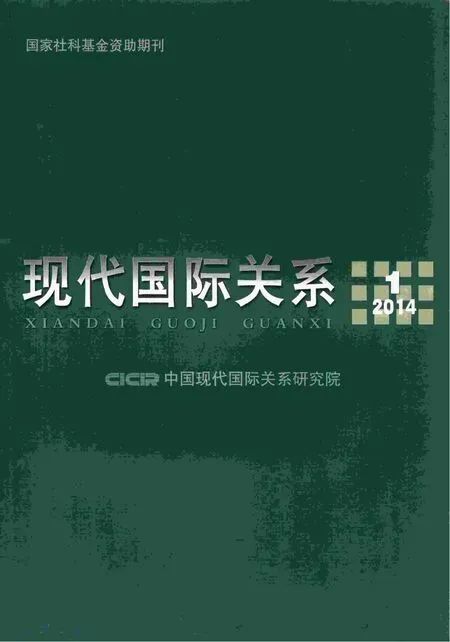保持中美日動態平衡仍是美戰略首選
袁 鵬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當前中日之間的戰略博弈同美國的亞太戰略有著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歷史地看,今日日本國內政治的變動可從1945-1951年麥克阿瑟接管日本時期進行的改革找到淵源,而釣魚島問題的存留更與1951年美國拋開中國大陸和臺灣單方面對日媾和直接相關。現實地看,本輪中日關系變局固然與中日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日本國內右傾化趨勢加大等結構性因素有關,但另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外因則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深度推進。因此,要實現中日關系轉圜,既需要從中日兩國自身查找原因、尋求對策,也需要準確把握并善加利用美國因素。其中,把握美國亞太戰略的本質尤為重要。
國內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本質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和資源,牽制或遏制中國的迅速崛起,確保美國在亞太的主導地位不動搖。因此,“以日制華”正取代“日中平衡”,成為美國東亞政策的主軸或不可逆轉的戰略方向。筆者認為,這一判斷有一定道理,但認定美亞太戰略的未來趨勢就是“以日制華”,則未免失之簡單,流于表面。至少從現在看,美國在日中之間搞動態平衡或巧妙制衡的基本戰略選擇還難說已經發生不可逆轉的根本性變化。
從本質上說,中國是美國的主要挑戰,日本是美國的核心盟友,這一點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發生根本變化。但挑戰不等于威脅,盟友還算不上朋友。以現實主義戰略觀為主流的美國,對外戰略很少受條條框框限制,戰略利益永遠都是最高準繩。這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中美日關系的變動中一再得到驗證。
冷戰時期,美國一度將朝鮮戰爭中的對手中國列為主要威脅,但在中國、蘇聯之間兩相權衡后,最終確立聯中抗蘇路線,美中成為“準同盟”關系。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和1972年尼克松訪華,被日本人稱之為“尼克松沖擊”,引發日朝野對美、對華戰略大辯論,直接加速中日恢復邦交的進程;冷戰后,克林頓政府一開始擺出咄咄逼人的姿態對付中國,1997年簽署美日防務新指針,美日關系實現了面向新時期的戰略轉向。但翌年克林頓總統對華展開長達12天的歷史性訪問,并同中方達成致力于構建“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的重要共識,令日本戰略界瞠目,媒體更將克林頓的“越頂外交”與當年的“尼克松沖擊”相提并論。小布什上臺之初,稱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擺出一副聯手日、臺遏制中國大陸的高壓態勢,但“9·11事件”的突發迫使小布什政府改變對華政策,中美關系由此保持了長達七八年的和平穩定期,日本則“借船出海”,謀求“脫美入亞”,美國在中日之間維持了總體戰略平衡。奧巴馬上臺之初,美中關系勢頭積極,包括布熱津斯基在內的戰略界人士甚至提出“中美共治”、“兩國集團”這樣的倡議,而美日關系則因普天間機場搬遷、印度洋斷油、核密約曝光、鳩山倡導“東亞共同體”等事件陷入低谷。這一狀態直到鳩山下臺、野田執政之后才得以逆轉,隨后發生的中日撞船事件、日本“購島事件”等則使得美日關系加速靠近、美中博弈越來越深。
問題在于,從此以后,美國是否已然確立“以日制華”的亞太戰略主軸,抑或還是會像過去一樣,不時在中日之間冷一方熱一方保持“動態平衡”式的戰略選擇?美國國內對此也在爭論,政府似乎沒有得出最終的結論。從最近對兩件事情的反應看,美國也很“糾結”。一是應對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美國一方面從言詞和行動上給予強烈反制,與日形成制華統一戰線,但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同日本保持距離(如同意民用飛機向中國申報),不隨日本的節拍起舞(如拜登訪日期間未同意與日簽署譴責中國的聯合聲明),也未因此而干擾美中關系的其他重要議程,令日本深感失望。二是應對安倍參拜靖國神社。事實上,美國一直擔心安倍會走這步棋而干擾其亞太戰略大局,因此2013年國務卿克里和國防部長哈格爾在訪日期間特意安排參訪日本千鳥淵戰歿者公墓,以傳遞美國不希望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的信號。孰料安倍對美國發出的信號置若罔聞,出于國內政治需要,小局不服從大局,最終進行了參拜。美國駐日使館和美國國務院事后均對此公開表示“失望”。其背后折射出三個信息:其一,安倍執意參拜,失道寡助,即使在美國國內也遭到猛烈批判,基于國際道義,美國不得不表態;其二,安倍一意孤行,顯示美國無法全面掌控日本的戰略方向,也難以讓日本全面服從美國的整體戰略布局;其三,安倍此舉不僅授中國以柄,也傷害日韓關系,令美國的東北亞同盟體系難以形成合力。
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對美國在東亞的“第一島鏈”形成壓力,對其亞太戰略利益構成沖擊。進一步說,中國海空力量的崛起及綜合實力的上揚,對美國亞太主導地位形成結構性挑戰。對這一基本態勢,美國戰略界似有共識。但在以什么樣的戰略應對中國的崛起及戰略擴展方面,美國迄今并未完全形成一致。“以日制華”是一種選項,但過去幾年的事實使美國意識到,日本既不是省油的燈,也不是好打的牌,玩不好反而會被日本利用,使美國成為日本實現其自身戰略抱負的工具。而從更長的時段看,日本在追求自身所謂“正常大國”地位過程中,既挑戰中國,更挑戰美國。因為日本的憲法是美國一手打造的,至今美國仍在日本保留大量駐軍。可以預料,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過程,必然是一個擺脫美國控制的過程。一旦走到那一步,讓美國離開亞洲的,恐怕是日本而不是中國。因此,美國的亞太戰略始終存在另一種聲音,那就是中美共治。事實上,“以日制華”也好,“中美共治”也好,在現實政策中都難以簡單實施,而最佳策略仍然是維持在中日之間“巧妙的制衡”。當前,美國一方面強化美日之間的軍事關系并深化政治關系,另一方面也積極呼應中方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正是這種“巧妙制衡”策略的現實運用。對中國而言,如何把握美國戰略的這種微妙之處,加強中美在反制日本右傾化以及其挑戰戰后國際秩序方面的合作,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