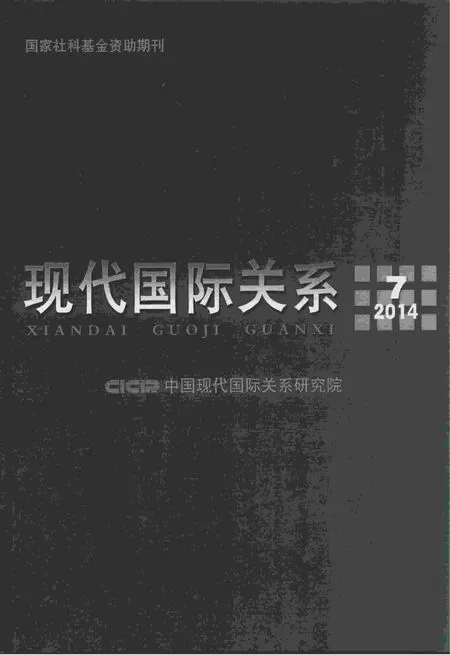我們為什么探討國際秩序變遷?
袁 鵬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國際關系則有自己的準則,國際社會也有自己的秩序。近一個時期,有關國際秩序的探討重新熱絡起來。對中國而言,面對日本安倍政權參拜靖國神社、挑戰歷史認識、解禁集體自衛權、大力推動修憲等一系列動作,捍衛戰后國際秩序已成當務之急。中俄兩國元首一致同意明年共同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70周年,意在彰顯捍衛戰后國際秩序的決心和意志;而對美日而言,似乎是中國(而非日本)正在破壞現存國際秩序,中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在南海的系列維權行動,被美日媒體甚至官方視為“挑戰現存秩序”,美國并一再敦促中國與東盟國家簽署《南海各方行為準則》,試圖給中國設規矩,防止中國進一步破壞現存“秩序”;對謀求“入常”的德國、日本、印度、巴西等國而言,現有國際秩序未能反映新的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和國際現實,它們因此呼吁改革安理會、改革聯合國;圍繞烏克蘭危機的博弈,美歐與俄羅斯也各有各的國際秩序觀,彼此唇槍舌戰,互不相讓。
于是乎,舉凡世界大國,幾乎都在談論國際秩序,幾乎都認定是別國在挑戰現有秩序,而自己是國際秩序的捍衛者。究竟誰是誰非,誰對誰錯?這就涉及到一個根本性問題,我們探討的究竟是什么秩序。如果此秩序非彼秩序,談的不是一回事兒,則彼此沒有交集,胡亂攻擊一氣,反而使秩序更加無序。
所謂國際秩序,是國際社會通過主要國家的斗爭與協調而形成的規范重大國際行為的原則、機制的總和。參與國越多,代表性越廣,所形成的秩序就越具權威性,尤其是經過世界大戰、用鮮血凝聚而成的國際秩序,就更需時刻遵循、堅定捍衛;而參與國以意識形態或特殊陣營劃線,不具廣泛代表性,所形成的秩序則只能是對小圈子的規范,因而無法用以約束整個國際社會。
今天中國所強調、所捍衛的國際秩序,正是前一種秩序,即“戰后國際秩序”這一“大秩序”。它是基于二戰后世界新的力量對比、以主要戰勝國為首、得到所有戰勝國一致認可、充分體現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充分反映國際公理與正義、集體建立起來的當代國際關系理念、規則、組織和機制的總稱,包括:以《聯合國憲章》為核心,反映世界和平、民主、進步潮流的一系列國際關系理念與價值觀;以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為中心,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的集體安全機制①其中最重要的是賦予安理會“五常”以否決權。由于“五常”對戰勝法西斯付出了最大的犧牲、做出了最大貢獻,因而享有有別于一般成員國的、對于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特殊權力與特殊責任。與此同時,“五常”均擁有“否決權”也體現了主要戰勝國應協調一致與“大國共治”的戰后世界秩序“頂層設計”。;通過兩場歷史性審判,以及戰勝國條約、戰敗國改造等一系列方式,形成的懲罰戰敗國侵略罪行、剝奪其戰爭潛力和權力、從法律上制度上限制其政治與軍事野心的一整套戰后制度設計;以及通過《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文件,對戰后領土歸屬問題作出的公正安排。
上述內涵是得到包括美、蘇、中、英、法等主要戰勝國一致認可,得到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集體認同的。因此,以此為核心的戰后國際秩序理應為各國共同遵奉、集體捍衛。問題是,隨著時間推移,尤其是二戰結束近70年間,國際社會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長達10余年的反恐戰爭及戰后最大規模的金融與債務危機,國際格局、力量對比、大國關系和國際機制均發生了重大變化,凡此使得“戰后國際秩序”的內涵及外延相應生變,各國對此的理解也漸行漸遠,實有必要正本清源,對究竟何謂“戰后國際秩序”來一番徹底檢討。其中問題之一,是一些國家偷換概念、夾帶“私貨”,將出于集團目的、未得到廣泛承認的相關安排也視做“戰后國際秩序”的一部分,進而魚龍混雜,混淆是非。比如,在涉及包括釣魚島在內的中日領土糾紛問題上,美國往往將1951年《舊金山和約》作為重要基礎,而眾所周知,《舊金山和約》是在因朝鮮戰爭美中敵對、因冷戰美蘇對立的背景下,美國撇開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包括中國大陸和臺灣)和蘇聯、單獨與日本媾和的產物,自一開始就不被中國政府所接受。因此,以《舊金山和約》作為戰后國際秩序規范的一部分顯然站不住腳。再比如,美國、日本及歐洲一些國家將北約和美日同盟看成戰后國際秩序的一部分。但實際上歐洲的北約是在二戰結束后4年即1949年正式成立,是徹頭徹尾的冷戰產物,并在其后不斷擴容,直至冷戰結束后還不斷增加新成員、擴展新使命,是一種典型的“冷戰秩序”而非“戰后秩序”;亞太地區的美國同盟體系也是在上世紀50年代后逐步搭建的,基本是美國主導下的反蘇反共聯盟。這種帶有明顯陣營性的同盟體系安排,顯然不應視作戰后國際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對北約及美國亞太同盟體系,我們可以表示理解甚至尊重其現實存在,但不可能作為戰后國際秩序的一部分加以接受。
更為嚴重的是,個別國家明目張膽地對戰后國際秩序進行挑戰而未受到應有的制約。日本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實質性解禁集體自衛權,企圖修改和平憲法,有條不紊地朝“擺脫戰后體制”步步推進,尤其是安倍政府輕易地越過歷代內閣不敢逾越的界限、公然堅持解禁集體自衛權,無疑使日本《和平憲法》中所規定的保證永久放棄宣戰權以及不以武力解決國際紛爭、不保持軍隊、不承認交戰權等核心條款面臨沖擊,可以說是戰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大轉折,等于沖破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聯合國憲章》確立的戰后國際秩序。令人憂心的是,一手打造日本《和平憲法》的美國,此一時彼一時,對日本安倍政權的所作所為不僅不加管束,反而為其背書,大有放日“出籠”牽制中國的意味,這種極其短視的政策選擇不僅給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傳遞危險的信號,殃及中美關系,而且遲早會讓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顛覆戰后國際秩序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想關上就難。對此,中國如不站出來大聲反對,則日本破壞戰后秩序的行為就會更加肆無忌憚,戰后秩序就將難以為繼。
因此,國際社會的當務之急,是重新找回“戰后國際秩序”的內核,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賦予新的時代精神。因為這是世界主要國家處理國際事務的最大公約數,是各國必須首先遵奉的“大秩序”。在此“大秩序”下,任何小圈子或小集團內部的體系或規矩都是“小秩序”。“小秩序”必須服從“大秩序”,而不是沖擊或綁架“大秩序”。在罔顧“大秩序”的情況下動輒拿“小秩序”說事兒打人,于情于理都不通。2015年將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也是戰后國際秩序確立70周年。70年來,雖然各種局部戰爭或地區沖突不斷,但世界大戰終究得以避免,這不能不說是戰后國際秩序最重要的價值所在。因此,2015年不應僅僅是中俄聯合紀念這70周年,而是所有參與締造戰后國際秩序的國家都應該來一起紀念,在歷史的長河中審視現在、展望未來,從而共享國際權力、共擔國際責任、共護國際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