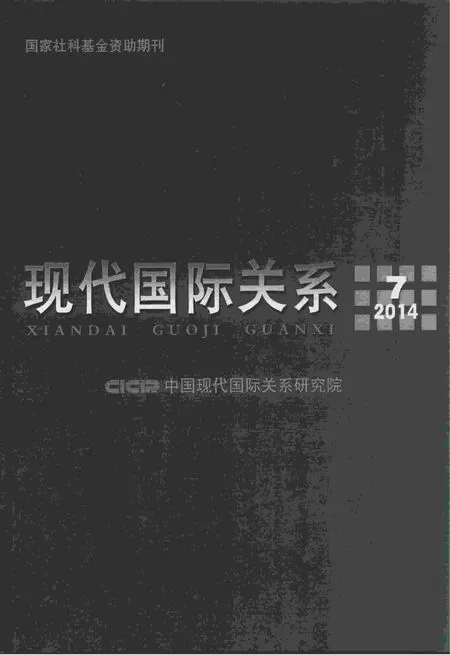對當前國際秩序轉型的幾點看法
胡仕勝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南亞東南亞與大洋洲所所長、研究員)
當前國際秩序尤其是地區秩序正處于一種將變未變的混沌狀態,存在著四大明顯特點。首先,中美博弈是催生現有秩序轉型的最大推力。中美都是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大國:一個是最大的守成國,一個是最大的新興國;一個是現有制度與秩序最關鍵的主動設計方,一個是現有制度與秩序最重要的被動獲益方;一個是最發達的西方民主體,一個是發展最快的東方威權體;一個希望繼續維持其在所有區域的主導地位,一個希望能在盡可能多的領域獲取重要話語權甚至主導權。而且,兩國都在推動當今秩序轉型。美國重在變革那些不能繼續服務于其主導性甚至壟斷性利益與地位的規則與秩序;中國重在變革那些不能代表其日益崛起之地位與日益拓展之利益的規則與秩序。重要的是,相比其他國家,中美兩國更具有帶動現有秩序變化的戰略需求與資源支撐。兩國的博弈也因此具有牽動國際秩序尤其是周邊秩序變動的巨大能量。可以說,中美博弈實際上是新舊秩序“破與立”的大博弈。
對美國而言,推動現有國際秩序轉型或變化的途徑主要有三。一是變革不再能幫助其維持霸主地位的規制,例如對日本擺脫二戰后體系的支持與慫恿,以及放棄打破WTO多哈回合談判僵局的努力等。二是創立利于其鞏固壟斷性地位的新規制、新高地,最明顯者當屬其近年大力推進的、旨在超越甚至最終可能取代WTO的TPP和TTIP談判進程。若其成功,將大大便利美牢固占據未來發展新高地,繼續在全球范圍內攫取壟斷性利潤,從而極大地強化其維持全球霸主地位的物質支撐。三是削弱甚至破壞那些挑戰美國主導性地位的新規制、新秩序的建立。近年通過利用西太地區國家對中國海上維權拓權行動的恐慌心理,美國不斷激化地區矛盾,竭力遏阻意在擴大中國地區主導權的新規制、新秩序的建立。例如,美國自身不承認甚至鼓動他人也不承認中國新設立的“防空識別區”;利用南海爭端,不斷慫恿越、菲干擾中國的南海維權行動;利用亞太國家對經濟上過度倚華的疑慮,積極拉攏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加入由其主導的TPP談判進程。此外,通過慫恿日本激化與中國的島嶼爭端、刺激朝鮮南北緊張局勢等,美近年大大抑制了幾年前呼之欲出的中日韓高水平次區域經貿合作安排,尤其是中斷了有可能最終挑戰美元霸主地位的中日韓貨幣安排及自貿安排的相關談判進程。
對于中國而言,它尋求變革現有秩序的主要途徑就是利用其地緣優勢、經貿優勢和資本優勢,推進與周邊地區的一體化進程,如去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兩走廊”戰略構想即旨在提高中國在周邊秩序塑造中的主體作用;推動現有國際經貿體制朝著反映中國實力變化的方向發展;推動建立有可能取代現有體制的新機制、新框架。這方面最為明顯的努力就是中國不斷推動金磚合作機制日益實體化。
其次,大國對周邊秩序的競爭遠比國際秩序競爭更加激烈。對于守成或新興大國而言,建立一種支撐其主導地位的周邊秩序是維系或提升其全球性大國地位的根本所在。任何大國的崛起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要在其緊鄰地區獲得秩序主導權;而對于任何守成大國而言,其牽制乃至壓制新興力量崛起的最有效手段也在于維系其在新興力量毗鄰地區的秩序主導權,或動用一切資源干擾新興大國在其周邊構筑新秩序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大國對周邊的秩序競爭帶有明顯的零和性質,一方的破局必然以另一方的失勢為代價。也唯其如此,這種秩序之爭蘊含相當程度的沖突性。一般而言,大國對周邊秩序的競爭不僅易引發大國之間的直接沖突,更易在夾于大國之間的第三國或地區引爆沖突,即代理人戰爭。烏克蘭之于美俄和歐俄、日本之于美中、巴基斯坦之于印中、阿富汗之于印巴、中亞之于俄中等,均易成為大國秩序競爭的主戰場。同樣,印度對于中國在南亞及印度洋地區日益擴大的存在也保持著高度戒備,并盡可能干擾中國在其周邊投棋布子。一旦中國這種日益顯性的存在最終是以取代印度主導性地位為目的,印中之間在南亞及環印度洋區域的戰略沖突也就在所難免。同理,中美在西太的博弈也日益呈現出對抗性特征。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即在于最大限度地遏制或盡可能拖延中國在西太地區確立主導地位的步伐。
然而,相比大國周邊秩序而言,在全球秩序層面,大國之間,包括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秩序競爭并不如此激烈,甚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協調、彼此磋商地共建新秩序、改革舊秩序。例如,在海上通道安全、全球反恐、北冰洋開發、外太空開發、網絡治理、氣候變化談判、貿易自由化機制改革、聯合國改革等領域,大國之間,包括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合作遠多于對抗。
第三,現有國際秩序的轉型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國際秩序的建立與轉型不是一蹴而就的。秩序主要由規則與權力構成。規則主要指秩序的運行框架,權力指維護規則運行框架的主要力量。秩序是在權力互動中通過不斷解構與建構規則及其運行框架而逐漸轉型或確立的。如果只是權力結構發生變化,而秩序得以運行的規則與框架沒有根本性改變,這種秩序就仍未完成轉型。只有當運行規則與權力格局都發生根本性變化,一種新秩序才會應運而生。鑒于此,當前的秩序可以說遠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權力格局、力量對比本身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維持當今秩序運行的最主要力量仍是美國及其同盟體系;二是支撐這個秩序運行的主要規則與運行框架未有根本性變化,如二戰結束后建立的聯合國機制未有巨變、主權國家為最主要行為體的現狀與法律地位未有巨變、維護自由貿易的國際體系尤其是市場經濟體系未有巨變。也就是說,當今秩序之爭及其核心部件的規則之爭尚未引發現有秩序的根本性轉型,以美國為首的守成力量以及以中國為主的新興力量之間的秩序之爭仍會持續相當長階段。
此外,作為當今秩序變動的最大推力—中美博弈勢將持續相當長階段。中美博弈不僅是綜合實力的博弈,更是兩種發展模式、兩種價值取向的博弈。美國等西方國家尤其懼怕這種秩序的變動或轉型導致其價值體系的崩盤。屆時,美與西方失去的將不僅僅是其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導地位,更是其數個世紀以來賴以生存的制度根基與價值體系。鑒此,美國等西方國家掌控秩序轉型主導權的政治意愿異常堅定,這也意味著這種圍繞新舊秩序立與破的競爭既相當激烈,更要持續相當長時段。這是因為,一方面,中國全方位超越美國絕非易事,甚至本世紀內尚無力完成;另一方面,即便中美綜合實力相互換位,新老大與新老二的競爭還會持續下去。歷史上,東亞朝貢體系被不平等條約體系取代經歷了數個世紀的拉鋸戰。同樣可以想見,維系美國霸主地位的同盟體系被中國主張的新型安全合作體系所取代可能也需要數個世紀的拉鋸戰。
而且,在當今世界,圍繞秩序轉型主導權的拉鋸戰正使得秩序呈現混沌特性。一方面,舊有秩序仍處在將改未改之際,易反復,甚至易倒退。無論是從G8回到G7,還是從奧巴馬政府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表示“理解”(賴斯語)到如今美方認為這種“理解”其實是種“失言”,都表明新舊秩序的解構與建構難免出現反復與曲折。此外,從IMF和WB份額與投票權的改革計劃至今未獲美國國會批準到聯合國“五常”對新興國家“入常”不情不愿,也表明現有既得利益者對舊有制度、秩序有著明顯的眷戀與堅守。再如,為維護海洋霸權與現有秩序,美至今都不愿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第四,中國在推進國際秩序轉型過程中面臨三重困擾。鑒于力量格局的變化最終必牽動規則變化以及基于其上的秩序變化,中國與現有地區及國際秩序互動關系的變化尤其具有指向性意義。然而,在推進有利于中國持續崛起的地區與國際秩序轉型的過程中,中國深受三大困擾之苦。一種困擾是,中國對現有秩序是以堅守為主還是以變革為主?是以繼承為主還是以創新為主?是以拿來主義為主還是以改良主義為主?這種困擾的產生源自這樣的事實:即中國的迅猛發展與崛起主要得益于對現有體制及現有秩序的服從與認同。正是由于這種成長經歷,中國如今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現有體制與秩序的最主要維護者,而主導制訂這套體制的美方反而成為企圖否定現有體制的最大推手。另一種困擾是,中國如何平衡對周邊秩序轉型與全球秩序轉型的追求。基于相關度的差異性,兩種追求不僅在用力方向和用力手段上不能一樣,而且最終目標似乎也應有所不同。對地區秩序轉型的追求應是中國“治國理政”的一部分,因為周邊地帶應是大國發展與崛起的戰略依托與必然延伸;對全球秩序轉型的追求才是中國未來“平天下”的一部分,可以“兼愛非攻”。這就使得相比追求地區秩序轉型,中國在追求全球秩序轉型時更易尋求與其他各方的協調與合作甚至妥協。再一種困擾是,中國究竟是參與還是阻擾美力主推進的新規制、新標準的確立?也就是說,未來中國是著眼于眼前利益的“止損”而對美力主的秩序轉型努力加以干擾,還是著眼于長遠的“坐享其成”而對美力主的秩序轉型努力予以適當支持、甚至參與,以及樂見其成?這種困擾主要緣自中國的身份困惑。中國當前仍是發展中國家,卻是發展最為迅速、利益廣布全球且日益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國,是未來絕對的全球性強國。既然美國現今推動制訂的新規制、新標準是服務于其全球性強國利益的,那么這種新規則、新標準及其所催生的新秩序不也將服務于中國這個新興全球強國的利益訴求與秩序訴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