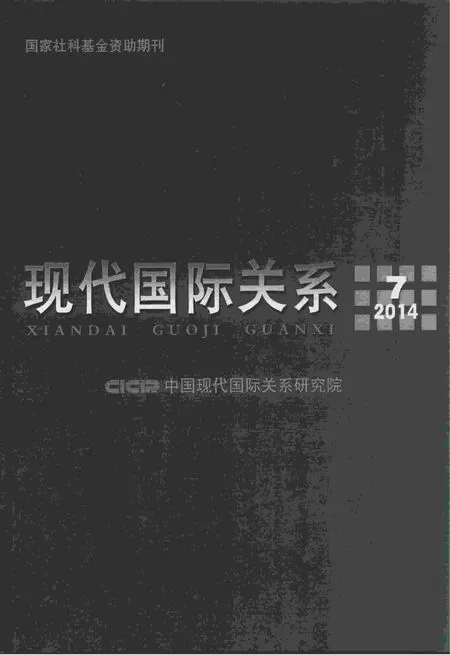關于國際格局變遷與中國和平崛起的兩點看法
王逸舟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從上世紀中葉到現在,近代形成的國際體系發生了深刻變化。二戰剛剛結束之時,全球僅有50余個主權獨立國家,它們大多歸于西方范疇,屬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支配殖民地的宗主國、主導體系的力量。那時,世界多半民族、人口和國家,真正是受奴役的、沒有發言權的“沉默多數”。如今,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之際,非西方世界國家數量占到全球國家總數(200個左右)的3/4以上,無論在聯合國還是二十國集團中都有更多的聲音與代表權,不管在國際貿易還是投資領域都受到更多重視,其中一批富有進取性的國家(以“金磚國家”為代表),更是在競爭中快速崛起,它們在器物層面(如制造業、基礎設施建設和國際經貿領域)占有越來越顯著的權重,在制度層面(如國際規則的制訂)正從單純的接受者朝著引導性角色轉變,在觀念層面變得更有自信、更自覺地探索符合本國需求的發展道路。中國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上世紀前葉它被認為是東亞病夫,受到西方列強的肆意宰割與奴役壓榨,如今則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積極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和為地區乃至全球事務做出貢獻。對照一個世紀前兩次世界大戰前后的國際格局,21世紀的當下,代表人類多數的國家制度和國際社會正在由舊式的自然狀態(霍布斯所說的“叢林政治”)朝著新的自為形態(有意識、有努力的平等、正義、理性安排)過渡。國際格局這種變化的積極歷史意義,無論怎么評估都不為過。
然而,我們此際特別有必要保持憂患意識與謙虛精神,充分估計自身存在的問題與矛盾。拿上面提到的三個層面來講:多數發展中國家至今仍然缺乏“高邊疆”優勢,在諸如海洋、極地、外空、金融安全和電信安全等領域的先手棋依然很少,技術創新和知識產權的份額很低。相形之下,歐美日發達國家則具有強大優勢;非西方的各個希望之星盡管表面風頭強勁,但在關鍵性的規則制定權和國際話語權方面仍缺乏操作經驗和實際文本能力,很多時候只能被動跟進甚至實際棄權;整體來看,包括崛起國家在內的發展中世界內部,廣泛存在脆弱的、麻煩的政治體制障礙與社會不滿,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遠沒有達到理想狀態。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從問題解決能手和國際體系的指導者變成了麻煩制造者和問題的一部分,但總體上還具有相對先進的技術體系、相對熟練的政治手段、相對完備的規制能力、相對穩定的社會構造。尤其應當看到,現有體系的主導國家(主要是西方大國)不愿意看到新興國家帶來的沖擊和根本改變,因而在國際間制造出各種顯性和隱性重大障礙。假使新興國家思想準備不足,有可能栽跟頭乃至沖頂失敗。
從正反兩方面講,中國既是當代國際格局變革的最大動能之一,也是未來國際關系出現戰略不確定性的最大變量之一。中國取得巨大歷史進步的基本原因,在于執政黨采取了與時俱進的改革開放方針。中國假使出現重大挫敗與麻煩,其根本原因也不在外部,而在自身。往未來一段時期觀察,我們國內的改革發展與轉型升級道路依然漫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爭奪戰和“高邊疆”攻堅戰中依然任務繁重。中國既要改造當代國際體系中不合理、不公正方面,也須改造自身存在的與時代要求不合之處。在取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軍費開支國的風光下,在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昂、外部各種壓力與挑釁頻繁的復雜局面中,要努力避免自滿、虛驕、戰略冒進。我以為,大國較量勝負的關鍵,不在誰敢于先出手,或誰能祭出什么殺手锏,而在于決策者善于審時度勢,始終不犯戰略性、結構性錯誤。過于畏縮和謹小慎微,抓不住重大時機,是一種戰略性錯誤;“綏靖主義”是另一類戰略錯誤;情緒急燥、戰略冒進則屬于第三種結構性錯誤。從中國目前條件和各方面因素考慮,防止戰略冒進是更迫切的事情。譬如說,它要求避免當下與美國在某些重大戰略問題上攤牌,或同時與多個鄰國緊張對峙甚至對抗沖突;它也需要在迅速擴展我海外利益、爭取更多戰略支點的時候,同時向外部提供各方需要的援助與公共產品。總之,中國應力爭實現“取”與“舍”之間的平衡。
古人講“成于憂慮、死于安樂”;又講打鐵先須自身硬。能否認知自身存在的短板是中國能否改變世界、影響外部的基本前提。從外交角度講,盡管中國國內進步早已今非昔比,中國公眾的開放意識和進步需求在不斷提升,但為何外界總是把中國與某些封閉、落后、一成不變的一黨執政國家相提并論?為何一些國家不斷把我們的國際戰略與“資源掠奪型”的西方列強對照?為何國際社會有相當多的朋友總覺得中國與那些麻煩國家、失敗政權或不討民眾喜歡的獨裁者走得太近?為何一些國際組織和機構老是批評中國在提供發展援助和安全援助方面“小氣”、與國力不符?在亞太,為何近期出現復雜棘手的事態,尤其一些中小鄰國對中國的防范、敵對加劇?在海洋和主權問題上,為何社會上尤其是網絡間一片喊打之聲,對于外交和決策部門對外采用強硬方針的壓力日益增大?為何各種法律的、外交的解決手段不太受到好評,大多數專家對于國際上各種解決方案很少有耐心細致的比較?對此,我們需要認真想一想,仔細梳理歸納一番,看看這里面有多少是由于一些敵對勢力刻意捏造和歪曲造成?有多少是因為官方外宣蒼白乏力所致?有多少是實際政策和決策思路的不當引發?有多少是緣于國人國際意識薄弱?哪些屬于毫無道理的指責?哪些算是誤解與偏見?又有哪些值得反思和改進?這些錯綜復雜、充滿變數的事情(及問題),都不是情緒化的反應、簡單化的方式所能解決的。今天的中國人,既不可陶醉于新近萌生的“盛世情結”和沙文主義夢囈,也不應囿于舊時狹隘的“弱國悲情”和“受害者心態”禁錮,而應仔細審視和定位新階段戰略取向,朝著新興大國、進取大國、風范大國、責任大國方向邁進。現存國際秩序中仍存在諸多結構性缺陷,少數國家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仍對中國崛起構成一定威脅,我們的海上通道安全、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和主權安全等領域仍存在這樣那樣的風險。對此,中國不能不有所防范、有所準備。中國既要發展軍事和國防方面的硬力量,也要建立建設性斡旋、創造性介入國際熱點和利害沖突的安排(與機制)。另一方面,若要改造世界,先要改造自身。適應時代要求和進步標準的國內轉型改制,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前提。須牢記:當我們反復強調“發展中國家”屬性時,并非對外宣傳上的托辭,或是為推卸國際責任尋找借口,而是坦承中國目前發展所處的較低水平,包括器物層面的相對粗放、體制層面的相對落后和觀念層面的相對自閉,是為著防止虛驕之氣阻礙高水平的內部革新和外交審慎;不管外界怎么解讀“發展中”的宣示,中國媒體和公眾要有清醒、準確的自我估計。繼續保持憂患意識、謙虛態度和奮發精神,再堅持幾代人的艱苦跋涉,中華民族重回世界偉大民族之林、為人類進步做出重大貢獻的圖景才可清晰展示。這應當不僅是外交博弈和軍事斗爭意義上的宏偉戰略,更應成為寬視角和長時段意義上謀劃中國發展的大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