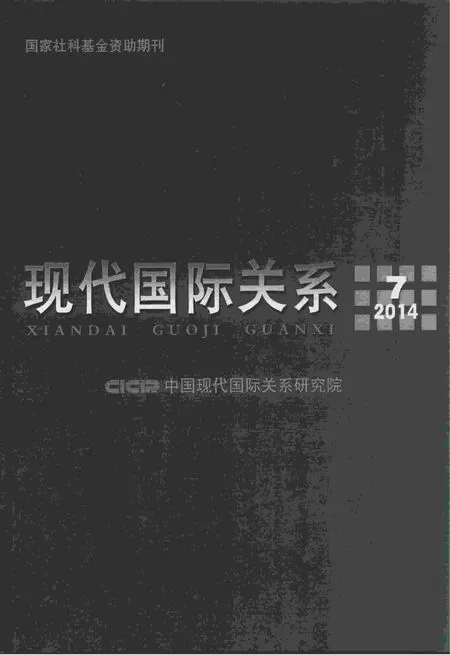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
時殷弘 (國務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世界秩序主要包含三項基本要素,即世界性的國際權勢分布、國際規范體系和跨國價值觀念體系,中國崛起與未來世界秩序的關系主要就是與這三項基本要素的關系。
關于權勢轉移趨向中的中美關系。當前國際權勢分布方面最重大的現實是人們談論得那么多的中美實力對比和權勢對比變化。在一個并非必將經久確定無疑的根本前提——巨型中國的和平騰升在未來仍將長久持續——之下,美國將認真地考慮中國不但在經濟甚而金融世界、也在外交甚而戰略世界的一流地位,并且很可能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段內最終采取一種和平的“最終解決”。這不僅意味著美國接受中國未來可能在國內生產總值、對外貿易總量和在亞洲的外交/經濟影響這幾大方面的領先地位,還接受中美之間互相的戰略威懾——既在核威懾也在常規威懾方面,連同作為相鄰兩強的和平并存,它們由某些軍備控制和地緣戰略利益互認互尊協議得到正式規制。這將包括中國在本國近岸海區擁有對美軍事邊際優勢(以臺灣東部海岸外鄰近海域為大致的戰略“分界線”),并且意味著臺海兩岸和平的或基本和平的重新統一;這也將包括中國在西太平洋一個非同小可的洋域“戰略空間”,并且相應地規制美國在東北亞的同盟體系,使之不那么軍事化、不那么以中國為鉗制和對抗目標。
與此同時,美國在中國的接受下,將保持它在世界總的軍事優勢、(特別地說)在沖繩和關島以東的西太平洋東部及中太平洋的軍事優勢。美國還將確信,中國將堅持排除用戰爭作為工具去解決與鄰國的重大爭端,如果鄰國也這么做,從而保證美國的兩項緊要利益——亞太基本和平和美國亞太盟國的安全。與此同時,美國在中國的接受下,還將擁有在某些地理區域相對于中國的外交優勢,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在世界金融和安全的體制性安排中,中美兩大國的正式影響或權勢分配將大致符合這兩大國各自擁有的相關實力和各自做出的相關貢獻。這還意味著中國的貢獻必須相應于中國增長了的實力而增進,美國的權勢則必須隨著中國的實力和貢獻的增進而相對地有所縮減。總而言之,這一切將要求:第一,美國接受一個和平和建設性的中國為世界強國;第二,中國尊重美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或許仍是頭號世界強國)的緊要利益和正當國際關切。
與此同時,必須指出中美大國關系的另一種可能前景——不祥的或甚為危險的前景。中美之間的大國“結構性對立”正在變得更為廣泛、深刻和顯著。特別是,中國經久持續的急速軍力建設正在愈益成為美國戰略精英甚而頗大部分美國公眾的顯要憂懼。另一方面,美國的地緣戰略“再平衡”,加上因為減抑人員傷亡、減少軍事開支和應對更大“威脅”的強制性必需而力度加劇的“軍事革命”(諸如“海空一體戰”之類),再加上美國經非常積極和靈巧的努力在中國周邊的外交競爭得益和地緣政治添亂,已經使中國更不滿美國及其戰略伙伴,更加決心加速推進自身軍力建設和軍事反制努力,并且新近以來考慮在東亞對美國的某些戰略盟友或伙伴作武裝較量。自多年前的里根政府以來,美國一直決心維持無可置疑的軍事優勢,將之視作美國作為超級強國的最重要戰略資產,同時反復證明在它認為必要和可行時不惜發動武力干涉甚而戰爭的決心。反之,中國近20年來為了自身國家安全、民族自尊、發展權利和呼應國內要求,始終決心軍事現當代化和擁有戰勝能力。中美之間這一最根本矛盾當然并非沒有可能破壞未來的中美關系。出于能夠進行“底線思維”的要求,中國要有應對這可能性不幸轉變為現實的心理準備甚或戰略準備。
關于中國崛起的價值要求和當今已見的價值效應。重大的歷史性創新關系到跨國價值觀念層次對世界史的貢獻以及對世界的吸引力和對本國人民的鼓舞力。現代世界史上,無論是荷蘭人、英國人還是美國人,在其崛起為頭等強國的過程中都在這方面創新良多,貢獻良多。中國自改革開放到現在為止,為世界作了什么跨國價值觀念上的基本貢獻?應當說,這方面的基本貢獻即使有,但與中國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量的飛躍相比差距太大。
另一方面,至今中國已開始顯現的、很可能具有世界史意義的一個價值創新趨向是“和平發展”觀念體系,即使這個觀念體系隨中國實力的強勁增長和中國對外態勢的某些新變化,似乎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激進的”中國人質疑,而中國能否堅持和平發展當前更是尚需有說服力地向外部世界輿論廣泛證明。在中國和平發展的觀念體系和實踐表現中,有一個非常重大的成分已經首先得到了相當充分的證實,或者說得到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最大民族成就的證實,那就是國際政治理論家理查德·羅茲克蘭斯在1985年著書強調的“貿易國的興起”,加上它反映的世界政治頗大部分機理的轉變傾向。
不僅如此,歷史由來更深刻更長久的是,中國通過在毛澤東領導下成功的革命,通過在鄧小平與其后繼幾代領導主持下的改革和發展,向全世界有力地昭示西式現代化決非現代化的唯一形態,各國人民的未來主要取決于各國人民根據本國具體情勢的自主實踐,誰也不能代替或主導各國人民自己確定本國的主要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道路,誰也不能聲稱對自己好的就必定對別國人民和全世界一樣好。這是中國樹立的在世界現代史上先前簡直沒有過的巨型范例,肯定具有世界歷史意義。
世界秩序的方向很大程度上由什么樣的“國際政治文化”及“戰略文化”最有影響來決定,而什么樣的國際政治文化及戰略文化最有影響,則由哪個國家載體——國際政治文化及戰略文化的國家載體——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成功來決定。假如美國自冷戰結束前后基于普遍主義“華盛頓共識”的“世界新秩序”論取得巨大成功,或者假如美國政府尤其自“9·11”往后的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際政治戰略取得巨大成功,那么世界秩序方向本會是美國式的,不管是美國式的“自由國際主義”還是美國式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然而,冷戰結束后至今,真正成功的巨型國家不是美國,而是中國:堅持自身特色和信仰本國實踐的中國作為“貿易國興起”的成功,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哲理和根本戰略的成功,中國和平發展的成功。這將在很大程度上規定國際政治文化及對外戰略文化的方向,由此大大影響世界秩序方向,只要中國自己能夠長久堅持某些中國人已經質疑的和平發展。
關于中國崛起與未來世界秩序。在“中國崛起與世界秩序”的討論框架內,特別要突出兩對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即:國際體系界限——特別是文化或狹義“文明”的界限——的擴展與國際規范的演變之間的關系;國際權勢分布的變遷與國際規范演變之間的關系,或曰權勢的能動性與國際規范的能動性之間的關系。
16世紀以來,這兩對關系的歷史表明,國際體系界限的擴展與國際權勢分布的變遷都導致了國際規范的重大演變。特別是,在現當代文明的歷史進程中,歐洲國際體系在19世紀的急劇擴展和真正全球性國際體系的出現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與之伴隨的不僅有國際體系傳統中心的衰落和側翼大國的興盛、非歐強國的大增生與其作用的大增進、非西方世界現代民族主義的偉大興起及其對西方的成功造反,還有在所有這些新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國際規范的深刻和廣泛的變更。
就其根本維度而言,當今的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大概可以簡約地概括為兩大方面。第一,中國這個富有文化特征的巨型國家在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交往和人口流動等各個領域,以迅速增進的廣度和深度介入和“纏入”外部世界,由此可以說已經并正在繼續導致全球性國際體系的重大擴展——在其內涵豐富性意義上的擴展,包括在其界限意義上的擴展;第二,“中國崛起”已經并正在繼續導致國際權勢結構的變化,它的長遠效應越來越有可能是變更性的。按照常理和現當代世界基本經驗,國際體系的廣義界限如此重大的擴展,連同國際權勢格局如此能動的變遷,勢將引發國際規范演變。在其中,首先是當代中國的根本行為模式(巨型“貿易國的興起”),然后連同中國的文明、文化、價值取向、國際政治觀和國際規范意向,加上它們與中國以外這些因素的交流、融合、激蕩、牴牾和協調,將決定未來國際規范的頗大一部分演變。這可能開拓國際規范史一個新的基本階段。
中國與基本的跨國價值體系及其創新——最不確定的未來:現代跨國價值觀念的根本范疇在“自由”、“社會正義”和“生態保護”之外,還有“經濟成長”。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主要的民族成就是在“經濟成長”范疇,但這個跨國價值遠非出自中國的創造,而且現在從政府到輿論,中國人越來越感到這一成就在多年里、在過大程度上以減損“社會正義”和犧牲“生態保護”為代價。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實現了中國社會的經濟“自由”——13億人口有了經濟“自由”當然是世界史上“自由”的巨大擴展。但經濟“自由”本身同樣不是中國的價值創新,何況中國在其他一些基本“自由”或自由權的充分實現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前所述,中國的“和平發展”觀念體系已開始顯現一種可能具有世界史意義的價值創新趨向,中國的“特殊主義”觀念體系即各國人民的未來主要取決于各國人民根據本國具體情勢的自主實踐,則理當更加如此。
綜觀中國的發展和這發展對世界的影響,可以說中國目前在力量或權勢增進方面表現得越來越有信心,在和平和正當地改變世界力量對比或權勢格局方面的信心也在顯著增長。而且,還可以預料,伴隨中國的和平崛起,國際規范體系勢將發生重大的進步性演變。但是,現在還無法較為全面和深刻地預言當代中國將對世界基本的跨國價值體系有什么世界歷史意義的大貢獻。在這方面,中國面對的歷史性挑戰在于:中國能否真正造就出一套具有較大的國際和跨國適切性和創新性的發展模式?中國能否成為世界強國、特別是能否經久保持為世界強國,將主要由中國能否成功地對付這一挑戰來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