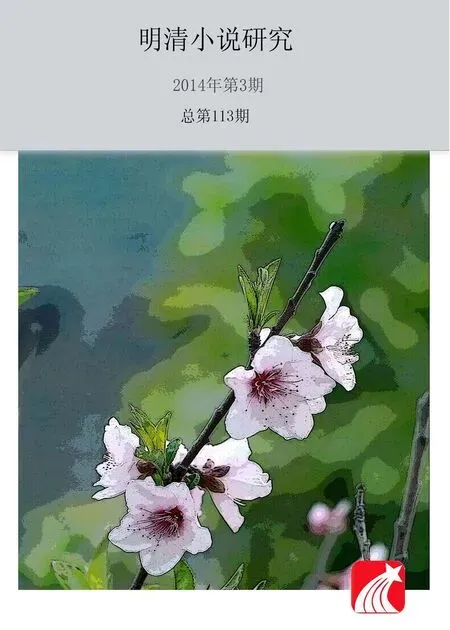俠義公案小說的界定與源流
· ·
俠義公案小說的界定與源流
·羅立群劉華·
俠義公案小說作為一種類型小說,學界至今沒有一個界定標準,導致概念模糊,外延失于寬泛。從小說類型學的角度來看,俠義公案小說的界定不應只注重題材內容,而應關注形式與內涵兩個方面,并結合時間段與典范作品綜合考量。俠義公案小說形成于清中葉,繁盛于晚清,民間說唱藝術是其產生的重要來源。
俠義公案小說 界定標準 鼓詞
俠義公案小說(又稱公案俠義小說、武俠公案小說)是清代中葉至末期頗有影響的一種文學類型,通常被認為是俠義題材與公案題材“合二為一”形成的小說流派。作為一種特殊的小說類型,“俠義公案小說”在文學史、小說史研究專著中屢被提及,研究論文也不少,這些研究雖然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在許多方面仍缺乏深入、細致的探討,比如對俠義公案小說的概念、篇目,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以及具體明確的界定,對其文化內涵和敘事模式的研究也十分欠缺。鑒于此,本文試圖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運用文學類型的理論,對俠義公案小說進行認真、全面的梳理和研究。
一、俠義公案小說的界定
最早將俠義公案小說作為小說類型加以研究并產生重大影響的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在書中設專章論述,第二十七篇名目即為“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雖然魯迅沒有明確提出“俠義公案小說”的概念,但其研究思路所形成的一種研究范式,引起學術界的普遍關注。較早將“俠義小說”與“公案小說”合并在一起,提出“俠義公案小說”概念的是吳小如、傅璇琮兩位先生。吳小如在1957年第4期《文藝學習》上發表的《讀〈三俠五義〉札記》一文,提出“俠義公案小說”的概念,傅璇琮在1957年第4期《讀書月報》上刊載《〈施公案〉是怎樣一部小說》的文章中則采用了“公案俠義小說”的提法。此后,“俠義公案小說”(或公案俠義小說)遂作為一種小說類型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俠義公案小說的界定,是俠義題材與公案題材的合流。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認為:“俠義小說與公案小說的合流,是這一時期(指近代)小說中的突出現象。”①作者在注釋中寫道:“俠義、公案小說原為兩種類型……近代前期,二者合流,出現了大量的俠義公案小說。”②李劍國、陳洪主編《中國小說通史》指出:“俠義公案小說是清代后期最有影響的小說類型。一些作家有意識地將‘武俠’和‘公案’兩類題材因素合為一體,出以白話長篇,從而形成所謂‘俠義公案’小說。”③張俊《清代小說史》也認為:“清代中葉,俠義及公案小說漸趨合流,成為一種新的藝術嘗試和創作傾向,其代表作是《施公案》、《忠烈俠義傳》、《彭公案》等。這類小說……將斷案與鋤奸合為一體,形成獨具特色的清人俠義公案小說。”④曹亦冰《俠義公案小說史》也是按照俠義小說、公案小說兩種小說類型的發展與相互合并的線索展開闡述,詳細敘述了俠義、公案題材進入小說創作領域的順序及其在整個古代小說創作中的影響⑤。這種劃分標準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僅依據題材來劃分類型,而忽略作品的其他因素,也會帶來許多問題,比如對這一類型的作品界定不夠嚴謹,范圍過寬,甚至有些模糊不清;對某些作品的歸屬或自相矛盾,或各行其是;對這一小說類型的文體特征與敘事特征難于準確概括、展開論述等。
美國學者韋勒克·沃倫在其學術專著《文學理論》中這樣論述“文學的類型”:“我們認為文學類型應視為一種對文學作品的分類編組,在理論上,這種編組是建立在兩個根據之上的:一個是外在形式(如特殊的格律或結構等),一個是內在形式(如態度、情調、目的等以及較為粗糙的題材和讀者觀眾范圍等)。”⑥很顯然,韋勒克、沃倫對文學類型的劃分,既看外在形式,也看內在形式,是一種綜合考察,而非僅僅關注題材。國內也有學者提出“小說類型學”的理論。他們認為,小說類型是一組時間上具有一定歷史延續、數量上已形成一定規模、呈現出獨特審美風貌并能在讀者中產生相對穩定閱讀期待和審美反應的小說集合體。因此,那些具備相當的歷史時段、具有穩定的形式和內涵樣貌、具有一系列典范性作品的小說樣式就被稱作“類型小說”。⑦可以看出,“小說類型學”確立的劃分標準,也不是僅依據題材,同樣關注形式與內涵兩方面,而且提出了時間段、典范作品等因素。
依據上述理論,我們認為“俠義公案小說”是一種小說類型,其類型劃分標準不應只注意題材,而應參照其他因素綜合考量。我們不妨結合有代表性的文學史、小說史列舉的俠義公案小說書目進行論述。
表格列出的作品,可以算是俠義公案小說的典范之作,從時間段來看,都產生于清代中葉至晚期,說明“俠義公案小說”是這一歷史時段創作的作品。這一歷史時段之所以會產生大量的俠義公案小說,魯迅認為一是由于社會思潮所致,“時去明亡已久遠,說書之地又為北京,其先又屢平內亂,游民則以從軍得功名,歸耀其鄉里,亦甚動野人歆羨,故凡俠義小說中之英雄,在民間每極粗豪,大有綠林結習,而終必為一大僚隸卒,供使令奔走以為寵榮,此蓋非心悅誠服,樂為臣仆之時不辦也”,“而其時歐人之力又侵入中國”,時勢變更,內憂外患,人們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和俠客身上⑧。一則緣于人們審美情趣的轉變。明代以來,四大奇書盛行,清乾隆年間又流行《紅樓夢》,但“時勢屢更,人情日異于昔,久亦稍厭,漸生別流”,俠義公案小說應運而生⑨。此外,還有文學傳承與傳播媒介發達等因素。曹亦冰《俠義公案小說史》雖然描述了俠義小說、公案小說的發展軌跡,但只是從題材著眼,沒有將“俠義公案小說”作為特定時段的小說類型加以研究,故而得出俠義公案小說形成于唐五代,成熟于宋元時期,發展于明代,繁榮于清代的結論。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七篇名為“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還沒有提出“俠義公案小說”的概念,也沒有視作獨特的小說類型,因此將《七劍十三俠》、《兒女英雄傳》以及《劉公案》、《李公案》一并列出。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已標明“俠義公案小說”,并作為特定時期的小說現象來闡述,而列出的書目卻又承襲魯迅著作,則明顯疏于考察,失于寬泛。李劍國、陳洪主編《中國小說通史》明確提出:“俠義公案小說是清代后期最有影響的小說類型。”列舉小說書目中有《七劍十三俠》,卻又指出俠義公案小說中的“俠義與公案又逐漸分化,出現了武俠小說和公案小說兩種類型,武俠如《七劍十三俠》、《仙俠五花劍》,新型公案如《九命奇冤》等”⑩。如此說來,《七劍十三俠》究竟劃歸俠義公案小說,還是分化后的武俠小說?張俊《清代小說史》有“《施公案》和俠義公案小說的產生”、“《三俠五義》和俠義公案小說的高峰”兩個章節,可見作者也是將“俠義公案小說”作為類型小說進行論述的。但在敘述俠義公案小說時,又分為俠義小說、公案小說、俠義公案小說三類,分類邏輯未免混亂。作者沒有將《七劍十三俠》歸入俠義公案小說類是對的,但將《武則天四大奇案》劃入俠義公案小說類型則不妥。這部小說以勘查案件為主要內容,沒有多少江湖豪杰的描述,理應劃歸公案小說。
總體說來,上述各家列舉的書目,基本上標示出俠義公案小說最典范的作品,卻又有所不同,均不夠精確,且有相互矛盾之處。《七劍十三俠》、《仙俠五花劍》這類小說,雖有江湖俠義與公案情節,但宗教描寫、魔幻內容較多,侈談“劍術”,奇幻飄逸,與《三俠五義》、《施公案》等作品的創作風格明顯不同,不應歸屬俠義公案小說,應歸入另一種小說類型——劍俠小說。《兒女英雄傳》、《綠牡丹》這類小說,“兒女真情”與“英雄至性”是小說著力描述的兩個方面,兒女真情的描寫突出患難相交、克己守禮,最后達到婚姻圓滿;英雄至性的描寫則強調權奸迫害、結交豪杰,通過忠奸斗爭,終至功成名就。此類小說雖也涉及俠義與公案題材,但與《三俠五義》等俠義公案小說的敘述重心偏離較大,在風格上也存在較大區別,不應劃歸同一小說類型,而應歸入英雄兒女小說。至于《劉公案》、《李公案》、《警富新書》、《清風閘》、《武則天四大奇案》等,主要情節是各類案件的勘查,相對缺少江湖俠義的內容,應屬于較純正的公案小說。表格中的《萬花樓》、《金臺全傳》、《蕩寇志》等,雖也有俠義與公案描寫,卻沒有清官與俠客聯手斷案的情節,小說有較多的朝廷內部忠奸斗爭的描述,充滿著英雄意識和傳奇色彩,其敘述風格與《三俠五義》等作品有著較大差異,列入俠義公案小說類型不大合適,似應屬于英雄傳奇小說。
上述各家列舉的書目之所以會有出入,主要是因為對俠義公案小說沒有一個準確的界定標準,過于模糊,失于寬泛。究竟如何界定俠義公案小說呢?我們認為,應該把這類作品視作特定時期的類型小說。它們是清代中葉至末期的作品,在題材內容上融匯了俠義與公案,其文體形式為章回小說,保留了相當多的北方俚語方言和濃郁的說書情調,不過多涉及兒女情事、奇幻劍術等內容,以江湖俠客和理想清官(或為皇帝)為主要描寫對象。主要作品有《施公案》及其續集、《三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彭公案》及其續集、《永慶升平前傳》、《永慶升平后傳》、《圣朝鼎盛萬年青》、《英雄大八義》、《英雄小八義》等。
二、俠義公案小說的源流
中國古代白話小說起源于民間的說唱藝術。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汴京瓦肆中的“說話”科目有講史、小說、說諢話、說三分、五代史等,俠義與公案題材應包含在“小說”科目中。至南宋,根據《都城紀勝》和《夢粱錄》兩書的記載,“說話”分四家:小說、說鐵騎兒、講史、說經。“說公案”是其中一家“小說”的子目,沒有俠義科目。雖然沒有標明俠義科目,“說話”中并非沒有俠義題材,《都城紀勝》云:“說公案皆是搏刀桿棒及發跡變泰之事。”《醉翁談錄》是一本記載宋代“說話”伎藝和“說話”資料的圖書,書中列公案名目十六種,樸刀(也作搏刀)名目十一種,桿棒名目十一種,其中公案名目下的《石頭孫立》、《戴嗣宗》,樸刀名目下的《十條龍》、《青面獸》,桿棒名目下的《花和尚》、《武行者》、《攔路虎》等,都是講說俠義故事的。雖然《醉翁談錄》將公案、樸刀、桿棒分列,但從《都城紀勝》的記載來看,樸刀、桿棒應包含在公案類中。
這樣看來,在宋代“說話”藝術中,俠義題材是有的,只是沒有單獨列出名目,它包含在公案名目中。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六明清小說部乙,按照小說題材列“說公案第三”,分子目二:一為俠義,一為精察。他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前的“分類說明”中寫道:“考宋人說話,小說有‘靈怪’,實即‘神魔’;有‘煙粉’,實即人情及狹邪小說;有‘公案’,實即‘俠義’……曰公案,注云‘皆是樸刀桿棒發跡變泰之事’,則是江湖亡命游俠招安受職之事,即俠義武勇之屬矣。”孫楷第在“分類說明”中,認為公案等于俠義,而在具體分類中,公案名目下除了“俠義”,還有“精察”,則“公案”明顯大于“俠義”。陳汝衡在《說書史話》一書中對“公案”作了較為詳細的闡釋:
公案、鐵騎兒被列在武的故事固然不錯,但這里的“武”,卻并不一定專指戰爭。所謂“樸刀桿棒”,是泛指江湖亡命,殺人報仇,造成血案,以至驚動官府一類的故事。再如強梁惡霸,犯案累累,貪官污吏,橫行不法,當有俠盜人物,路見不平,用暴力方式,替人民痛痛快快地伸冤雪恨,也是公案故事。總之,公案項下的題材,絕不可以把它限在戰爭范圍以內。凡有“武”的行為,足以成為統治階級官府勘察審問對象的,都可以說是公案故事。
陳汝衡的觀點也說明,在宋代的“說話”伎藝里,公案類的題材是較為廣泛的,俠義故事也歸屬其中。
雖然宋代的“說話”分類中,公案名目涵蓋了俠義題材,但俠義公案小說的形成與發展卻是在清代中葉至清末,促成其產生的重要因緣,正是民間的說唱藝術。明清之際,民間說唱十分流行,當時在中國北方盛行一種民間說唱形式叫“鼓詞”。鼓詞又叫說唱大鼓,是以有說有唱的表演形式敘述長篇故事,俠義故事與公案故事是其中重要的演唱題材,很受觀眾歡迎。清道光年間金梯云《子弟書》抄本,記載有《嘆石玉昆》一目,描述了嘉慶、道光年間說書藝人石玉昆說唱《三俠五義》的盛況,其詞贊道:
高抬聲價本超群,壓倒江湖無業民;
驚動公卿夸絕調,流傳市井效眉顰;
編來宋代包公案,成就當時石玉昆;
是誰拜贈先生號?直比談經絳帳人。
《三俠五義》雖然首次刊印于光緒五年,但它與道光年間的石玉昆唱本是一脈相承的。“從北京首都圖書館所藏車王府唱本《包公案》和《三俠五義》的抄本對照來看,除刪去唱詞,文字上有些加工潤色之外,情節上也只有兩處變動。因此可以說,今本《三俠五義》基本上保持了石玉昆唱本的原來面貌。”
小說《施公案》的最早刊印時間大約在清嘉慶年間,現今留存最早的一篇清無名氏《施公案序》就寫于嘉慶戊午年(1798)孟冬月。這部小說在成書前也是早就以說唱的形式在民間流傳。鼓詞曲本《劉公案》第二十三部第三回道:“三檔就是《施公案》,這人在京都大有名;他本姓黃叫黃老,‘輔臣’二字是眾人稱;說的是,施公私訪桃花寺,西山廟內拿惡僧。”黃輔臣是乾隆嘉慶年間的說書藝人,可見,在小說《施公案》刊刻前,施公斷案的故事早就在民間廣為流傳。陳康祺在其專記清代史實軼聞的筆記《郎潛紀聞》中有所記錄:“少時即聞鄉里父老言施世綸為清官。入都后則聞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強御二語。蓋二百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施世綸在康熙朝做官,作者陳康祺生于道光二十年,主要活動于咸豐、同治、光緒年間,施世綸的故事在民間傳唱了兩百多年,由說唱形式而刻成小說問世,以至于“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
小說《彭公案》出版于光緒年間,但演述彭公故事的說唱本早有流傳。清抄本《車王府曲本》中所錄鼓詞《彭公案》開篇云:“江山一統萬年青,君正臣良永太平。文官舉筆安天下,武將提刀定安寧。四句詩詞道罷,聽我在下閑演一部彭公案。這部書說的是當今萬歲康熙佛爺駕登九五,真乃是風調雨順。”從鼓詞的內容、語氣來判斷,這個鼓詞曲本應產生于清康熙年間,比小說文本問世早了兩百多年。
《永慶升平前傳》刊刻于清光緒辛卯年(1891),該書作者郭廣瑞在書前“自序”中言道:“余少游四海,在都嘗聽評詞演《永慶升平》一書,乃我國大清褒忠貶佞、剿滅亂賊邪教之實事……國初以來,有此實事流傳。咸豐年間,有姜振名先生,乃評談今古之人,嘗演說此書,未能有人刊刻流傳于世。余長聽哈輔源先生演說,熟記在心,閑暇之時錄成四卷,以為遣悶。茲余友寶文堂主人,見此書文理直爽,立志刊刻傳世,非圖漁利,實為同好之人遣悶。余亦樂從,遂增刪補改,錄實事百數回。”由此看來,《永慶升平》小說文本出版前,其故事早已在民間廣為流傳。
上述例證可以看出,俠義公案小說的產生,有一個從民間說唱到小說文本的演變過程。其間,雖有文人的加工整理,但小說文本仍在相當程度上保留了民間的生活氣息與審美趣味,正如魯迅所說:“是俠義小說之在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固平民文學之歷七百余年而再興者也。”
俠義公案小說一經問世,立刻產生強烈的社會反響,下層民眾尤其喜聞樂道。光緒年間,俠義公案小說形成了出版狂潮,《施公案》、《彭公案》、《三俠五義》等書一續再續,多達十數集,甚至二十多集。出現這種情形,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會、政治的影響,也是文化思潮、審美情趣的變化所致,更有印刷技術提高、出版業繁榮以及小說文體演變等多種因素。但隨著局勢的動蕩,清王朝日益衰落,面臨滅頂之災,加之西方文化思想的傳入,人們的思想、文化心理、審美趣味都在發生轉變,宣揚皇權思想,鼓吹“忠義”主題的俠義公案小說開始受到人們的質疑,這一小說類型也開始分化。其中公案故事融入偵探推理元素,向新型公案小說演變,出現了《九命奇冤》、《活地獄》等小說;俠義故事則逐步擯棄清官情結,著力描繪江湖奇事與武林門派紛爭,向現代武俠小說演進。清末至民初,俠義公案小說困境日顯,最終退出歷史文化舞臺。
注:
①②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385、395頁。
③⑩ 李劍國、陳洪主編《中國小說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4、1492頁。
④ 張俊《清代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頁。
⑤ 參見曹亦冰《俠義公案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⑥ 韋勒克·沃倫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63頁。
⑦ 參閱葛紅兵、肖青峰《小說類型理論與批評實踐——小說類型學研究論綱》,《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責任編輯:魏文哲
羅立群,暨南大學人文學院;劉華,暨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