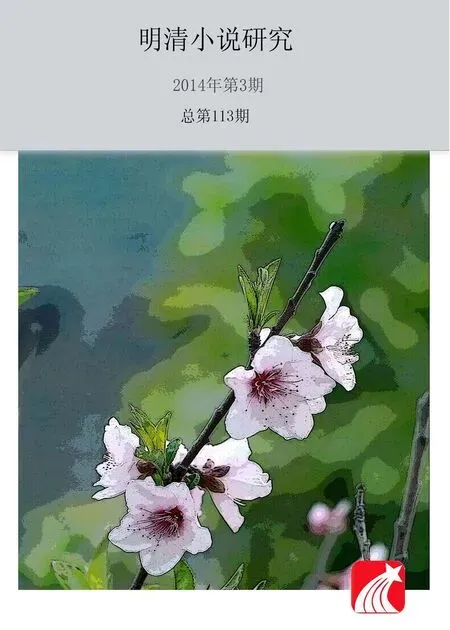明清文言小說的文體焦慮與尊體實(shí)驗(yàn)——以《剪燈馀話》《閱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為例
· ·
明清文言小說的文體焦慮與尊體實(shí)驗(yàn)——以《剪燈馀話》《閱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為例
·陳赟·
在小說體卑的普遍觀念下,明清文人寫作小說時(shí)常常伴隨著一種“文體焦慮”。他們一般只是在較雅的文言小說里才肯以真名示人,并試圖在寫作中對(duì)小說文體進(jìn)行“雅化”改造,以便提高小說文體的地位。本文以《剪燈馀話》、《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志異》三部文言小說為例,探討小說體卑觀念下文人們不同的小說寫作心態(tài),及他們?yōu)閿[脫文體焦慮而進(jìn)行的“小說詩(shī)文化”、“小說學(xué)術(shù)化”和“小說的情感敘事追求”三種尊體的努力,考察文體變革與文化土壤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
文言小說 文體焦慮 尊體實(shí)驗(yàn)
明清時(shí)期是中國(guó)小說創(chuàng)作的鼎盛期,白話小說成績(jī)尤為突出,充分展現(xiàn)了小說文體的巨大潛力。與此同時(shí),發(fā)達(dá)的文章辨體意識(shí)與理學(xué)正統(tǒng)思想的合流,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小說體卑觀念。小說實(shí)踐與理論之間出現(xiàn)巨大的地位落差,使得士大夫文人對(duì)小說既傾心向往,又心存顧忌,小說創(chuàng)作的文體焦慮因此而生。于是,小說中身份較高、形式較雅的文言小說,成了文人們公開介入小說寫作的主要選擇。文言小說體制雜亂的歷史,也為文人們推尊小說的努力留下了操作空間。本文以《剪燈馀話》《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志異》三部文言小說為案例,考察在小說體卑觀念下文人們的不同小說寫作心態(tài),及其為擺脫文體焦慮而做出的幾種文體處理方式。
一、《剪燈馀話》:體卑焦慮下的“詩(shī)文小說”實(shí)驗(yàn)
“詩(shī)文小說”的創(chuàng)作是明代文人在小說體卑壓力下進(jìn)行的一種小說雅化嘗試。“詩(shī)文小說”的說法最早由孫楷第提出,用以概括明代由瞿佑、李昌祺開創(chuàng)的“多羼入詩(shī)詞”的文言小說①。從語(yǔ)言形式上看,唐傳奇中《游仙窟》等“辭賦派”小說已開“詩(shī)文小說”之先例②,但唐辭賦派小說羼入詩(shī)文的程度較輕,總體上不影響小說敘事,“用意固仍以故事為主”,而且唐代辭賦派小說的出現(xiàn)原因與“詩(shī)文小說”有顯著區(qū)別。據(jù)今人研究,唐代辭賦派小說的出現(xiàn)一方面是文體內(nèi)部自然演變的結(jié)果,是“從秦漢以來的敘事辭賦演化而來的”③,另一方面可能與唐代舉人的“溫卷”行為有關(guān),因?yàn)檗o賦派小說“文備眾體,可以見史才、詩(shī)筆、議論”(《云麓漫鈔》卷八),可以為作者帶來名聲和機(jī)遇。而“詩(shī)文小說”盛行于小說體卑觀念深入人心的明代,創(chuàng)作小說并無(wú)直接的功利目的,往往是出于對(duì)小說本能的喜愛,含有推尊小說的意圖。王恒展認(rèn)為“明代是中國(guó)小說的雅化時(shí)期”,其基本思路是把源于“街談巷議”的小說,改造為“以儒家文化為主流,以詩(shī)書禮樂為內(nèi)核,以標(biāo)準(zhǔn)的書面語(yǔ)言即文言為外殼,以傳統(tǒng)詩(shī)文為主要形式”的“典型士大夫文化”④。顯然,這樣的“雅化”改革源于小說體卑觀念,目的是提升小說在儒家社會(huì)中的地位。
明代“詩(shī)文小說”,以瞿佑《剪燈新話》名氣最大,但從小說文體的詩(shī)文化改造程度來說,李昌祺《剪燈馀話》(以下簡(jiǎn)稱《馀話》)最為典型,更適合作為研究的范例。李昌祺(1376~1452),永樂二年進(jìn)士,官至廣西布政使。《馀話》的“自序”里⑤,李昌祺稱他十分喜歡《剪燈新話》,“銳欲效顰”,于是“捃摭文”,編為《馀話》。然而,身居從二品高官的李昌祺,不能無(wú)視小說體卑的現(xiàn)實(shí),擔(dān)心《馀話》“取譏大雅”,于是在序文中不惜筆墨對(duì)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進(jìn)行辯解。他首先承認(rèn)《馀話》“成于羈旅,出于記憶,無(wú)書籍質(zhì)證”,一度“不敢示人”,乃至想“亟欲焚去以絕跡”,但考慮到這些小說可以“豁懷抱,渲郁悶”,“較諸飽食、博弈,或者其庶乎”,于是“遂不復(fù)焚”。
需要注意的是,李昌祺在肯定此書價(jià)值的時(shí)候,引用了孔子“飽食終日,無(wú)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論語(yǔ)·陽(yáng)貨》)這句話為依據(jù)。表面上看,這是承認(rèn)自己小說價(jià)值不高的低調(diào)姿態(tài),但這段話的用典指向更可能是漢宣帝論辭賦一事。其本事見《漢書·王褒傳》: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并待詔,數(shù)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shī)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wèi),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fēng)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于倡優(yōu)博弈遠(yuǎn)矣。”
可見,西漢辭賦文體面臨“淫靡不急”的價(jià)值危機(jī),與李昌祺時(shí)小說文體遭受的境遇相似。漢宣帝在維護(hù)漢賦時(shí)雖引用孔子關(guān)于博弈的言論,但其意卻是高度贊揚(yáng)辭賦文體,認(rèn)為辭賦不僅有“綺縠”之美,而且還有“仁義風(fēng)諭”之善和“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超出博弈這種小道“遠(yuǎn)矣”!李昌祺此處把自己的小說與辭賦比,明貶暗褒,故序言中才會(huì)提及《高唐》《洛神》兩篇辭賦,稱贊二賦的“修辭縟麗,千載之下,膾炙人口”,委婉地肯定了《馀話》的“濃麗豐蔚,文采爛然”。
顯而易見,《馀話》在創(chuàng)作上是有意識(shí)地把辭賦文體作為效法的榜樣,要求語(yǔ)言具有“虞說耳目”之美,兼及“仁義風(fēng)諭”,以提高小說文體品味,減輕小說體卑帶來的創(chuàng)作焦慮。在此種小說觀念下,李昌祺讀《剪燈新話》后“惜其詞美而風(fēng)教少關(guān)”⑥就不奇怪了。在《馀話》的創(chuàng)作中,李昌祺繼承了瞿佑的“詞美”的風(fēng)格,加強(qiáng)了小說“風(fēng)教”內(nèi)容,試圖從詩(shī)文之美與倫理之善兩方面改變小說體卑的現(xiàn)狀。小說中展開倫理訓(xùn)誡,是明清小說十分流行的做法,不算什么特色,而且小說文體“涉于語(yǔ)怪,近于誨淫”(瞿佑《剪燈新話序》)的內(nèi)容傾向,大大減弱了“風(fēng)教”的效果。因此,《馀話》在小說文體上的特點(diǎn),或者說李昌祺企圖在小說中實(shí)現(xiàn)的小說尊體的努力,主要體現(xiàn)在為“詩(shī)文小說”的寫作實(shí)驗(yàn),“對(duì)瞿佑、李昌祺來說,除了顯露詩(shī)才的動(dòng)機(jī)之外,同時(shí)也含有當(dāng)社會(huì)輿論鄙薄小說之時(shí),借助正統(tǒng)文學(xué)之力,以較溫和合法的形式提高小說地位的意味”⑦。
李昌祺對(duì)小說的詩(shī)文化改造首先表現(xiàn)為敘述語(yǔ)言的雅化。《馀話》無(wú)視小說的敘事本位,把語(yǔ)言之美當(dāng)成小說的主要目的,于是在敘述語(yǔ)言中大量使用駢文儷句,深典僻字,將讀者設(shè)定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精英階層,借此與“引車賣漿者流”的白話小說劃分界限,提高小說的文化地位。如《月夜彈琴記》敘述節(jié)婦趙氏祠的荒涼景象,全用駢體:“但見鼠穿敗壁,苔繡空街。谷變陵遷,悵貞魂之已遠(yuǎn);時(shí)殊事異,慨老屋之之僅存。”句式雖雅,然語(yǔ)義重復(fù),破壞了敘事的流暢性、含蓄性。又如《聽經(jīng)猿記》,敘述禪師睡覺“樸握暖足,伊尼衛(wèi)床”,簡(jiǎn)短的八個(gè)字,就用了兩個(gè)較為生僻的典故,“樸握”指兔子,典出蘇軾詩(shī)《游徑山》;“伊尼”指鹿,典出黃庭堅(jiān)詩(shī)《德孺五丈和之字詩(shī)韻難而愈工輒復(fù)和成可發(fā)一笑》。此類炫弄學(xué)識(shí)的小說敘述,簡(jiǎn)直就是給小說制造閱讀障礙,讀者如非博學(xué)大家,只能不知所云了。
不僅如此,李昌祺還把駢體和典故大量運(yùn)用于作品中的人物對(duì)話,常常不顧及人物的身份和說話的語(yǔ)境。如《賈云華還魂記》中老婦向魏鵬介紹娉娉:“語(yǔ)顏色則若桃花之映春水,論態(tài)度則若流云之迎曉日;十指削纖纖之玉,雙鬢綰嫋嫋之絲;填詞度曲,李易安難繼后塵;織錦繡圖,蘇若蘭豈容獨(dú)步!”文辭雖華麗整飭,但出于老婦之口,總是有些別扭造作。再來看該文寫侍女福福奉勸娉娉的話:
小姐稟賦溫柔,幽閑貞靜,其性不可及,一也。天資美艷,絕世無(wú)雙,其貌不可及,二也。歌詞流麗,翰墨清新,其才調(diào)不可及,三也。諳曉音律,善措言辭,其聰明不可及,四也。至于考究經(jīng)史,評(píng)論古今,然如貫珠,灑灑然若霏雪。……矧又為薊公之孫,平章之女。母有邢國(guó)之賢,弟又令尹之貴。四德俱備,一族同推,行配高門,豈無(wú)佳婿?……誠(chéng)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妾時(shí)恥之,無(wú)面目將去也。
這段長(zhǎng)篇宏論,思路清晰、語(yǔ)言典雅、立場(chǎng)正統(tǒng),與一個(gè)貼身侍女的身份嚴(yán)重不符,更像一個(gè)大家族長(zhǎng)的道德說教。曹雪芹批評(píng)才子佳人小說“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紅樓夢(mèng)》第一回),移諸《馀話》,頗為恰當(dāng)。
《馀話》詩(shī)文化改造的另一個(gè)表現(xiàn)是,在小說中穿插了數(shù)量龐大的詩(shī)詞文賦,小說幾乎變身為一個(gè)收藏詩(shī)文的容器,敘事則成了串聯(lián)詩(shī)文的繩索。全書21篇作品,篇篇都有詩(shī)文的羼入,羼入詩(shī)文的篇幅比例全部超過小說全文的10%⑧,其中3篇超過了50%,極端者如作者頗為自負(fù)的《至正妓人行并序》,詩(shī)文所占比例超過80%。《馀話》中所羼入的詩(shī)文種類非常之多,文類有啟(《聽經(jīng)猿猿記》),有論(《何思明游酆都錄》),有書信、答書(《鸞鸞傳》),有祭文(《賈云華還魂記》),有檄文(《胡媚娘傳》),有銘文(《何思明游酆都錄》),有制誥(《泰山御史傳》),彈劾文(《泰山御史傳》),有撒帳文(《洞天花燭記》);詩(shī)類有近體詩(shī),有古體詩(shī),有樂府,有詞曲,有楚辭體,有回文詩(shī),有步韻詩(shī),有聯(lián)句,有集句,有仿《長(zhǎng)安古意》的模仿詩(shī)《峨眉古意》(《江廟泥神記》)、仿《胡笳十八拍》的《悲笳四拍》(《鸞鸞傳》)、仿《琵琶行》的《至正婦人行》等等。誠(chéng)如劉敬子《序四》里所稱的,“有文、有詩(shī)、有歌、有詞”,符合詩(shī)文的審美要求,可以“漱藝苑之芳潤(rùn),暢詞林之風(fēng)月,錦心繡口,繪句飾章”,甚至被譽(yù)為“辭藻之盛,未有過于此者”(《至正妓人行·跋四》)。
誠(chéng)然,《馀話》中的詩(shī)文本身有一定審美價(jià)值,錢謙益《列朝詩(shī)集》選李昌祺詩(shī)有《馀話》中的《至正婦人行》及《月下彈琴記》里的集句詩(shī),并在《列朝詩(shī)集小傳》中引安磬的評(píng)價(jià),肯定《馀話》中部分詩(shī)文“對(duì)偶天然,可取也”⑨。但是,從小說的角度來看,這些詩(shī)文大多數(shù)都屬于駢拇枝指,與情節(jié)、人物、情感等皆無(wú)關(guān)聯(lián),給人一種“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shī)艷賦來”(《紅樓夢(mèng)》第一回)的印象,破壞了敘事的明晰性、流暢性,造成敘事的拖沓、冗長(zhǎng),大大減弱了小說的故事性、趣味性和倫理意義。如《田洙遇薛濤聯(lián)句》《江廟泥神記》這類人鬼戀故事情節(jié)單薄,毫無(wú)動(dòng)人心魄的感染力,只有才華的賣弄;《記月夜彈琴記》過多的集句減弱了節(jié)烈的主題;《洞天花燭記》也許當(dāng)作一本婚禮應(yīng)用文的匯編更為合適。在整部《馀話》中,反而是插入詩(shī)文較少的《芙蓉屏記》,寫出曲折起伏的感人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當(dāng)李昌祺《馀話》把小說寫作引向詩(shī)文化道路的時(shí)候,小說自身的敘事特征被抹掉了,小說最終喪失了獨(dú)立身份,淪為詩(shī)文的附庸。齊裕焜認(rèn)為瞿佑、李昌祺的小說詩(shī)文化創(chuàng)作“在語(yǔ)體方面,與唐傳奇相比,似有所倒退”⑩。陳大康也說:“自瞿佑、李昌祺之后,作品中多羼入詩(shī)詞便成了明代初中期文言小說創(chuàng)作的重要特點(diǎn)之一,然而,盡管那些詩(shī)文盡受時(shí)人稱贊,小說的地位在實(shí)質(zhì)上并未提高,反而是將其自身弄得文體復(fù)雜,體例不純。”李昌祺的聲譽(yù)甚至因《馀話》而受影響,“景泰間,韓都憲雍巡撫江西,以廬陵鄉(xiāng)賢祀學(xué)宮,昌期獨(dú)以作《馀話》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歟!”
二、《閱微草堂筆記》:體卑焦慮下的“著書者之筆”“著書之體”實(shí)驗(yàn)
同樣是在小說體卑壓力下進(jìn)行的小說創(chuàng)作,紀(jì)昀《閱微草堂筆記》(以下簡(jiǎn)稱《閱微》)選擇了另一種小說雅化的路徑:把小說從“才子之筆”引向“著書者之筆”,進(jìn)行小說文體的學(xué)術(shù)化改造,以幫助小說度過體卑的困境。
紀(jì)昀(1724-1805)乾隆十九年進(jìn)士,官至禮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xué)士,曾任《四庫(kù)全書》總纂修官。這樣的身份和經(jīng)歷,無(wú)疑給他的文論思想帶來官方正統(tǒng)的色彩,限制了他小說觀念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紀(jì)昀對(duì)小說體卑的現(xiàn)實(shí)有清醒的認(rèn)識(shí),他主持修纂的《四庫(kù)全書》收錄小說僅限于少數(shù)文言小說,完全沒有收錄白話小說。他主筆的《四庫(kù)全書總目》對(duì)小說文體也時(shí)有貶低,如論及《大唐新語(yǔ)》時(shí)認(rèn)為該書“繁蕪猥瑣……有乖史家之體例,今退置小說家類”,意謂小說卑于史傳,且與“繁蕪猥瑣”為伍。在他的小說《閱微》卷十八第38條后有一段議論,“青衣童子之宣赦,渾家門客之吟詩(shī),皆小說妄言,不足據(jù)也”。此處“小說妄言”一詞顯然是隨手拈來,但這四字的習(xí)慣組合,證明了在當(dāng)時(shí)文化背景中“小說”與“妄言”已成近義詞,都面臨“不足據(jù)也”的價(jià)值危機(jī)。因此,喜歡小說的紀(jì)昀,才會(huì)情不自禁地在《閱微》里一而再、再而三地為小說價(jià)值申辯:
小說稗官,知無(wú)關(guān)于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于勸懲。(《灤陽(yáng)消夏錄序》)
念古來潛德,往往籍稗官小說,以發(fā)幽光。因撮厥大幾,附諸瑣錄,雖書原志怪,未免為例不純;于表章風(fēng)教之旨,則未始不一耳。(卷十四第61條)
此當(dāng)是寓言,未必真有。然莊生、列子,半屬寓言,義足勸懲,固不必刻舟求劍耳。(卷十八第7條)
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辭,魯史皆然,況稗官小說。……惟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勸懲之旨,不顛倒是非如《碧云騢》,不懷挾恩怨如《周秦行記》,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huì)真記》,不繪畫橫陳如《秘辛》,冀不見擯于君子云爾。(卷二十四第18條)
寓言滑稽,以文為戲也……偶一為之,以資懲勸,一無(wú)所不可;如累牘連篇,動(dòng)成卷帙,則非著書之體矣。(卷二十二第17條)
觀其大旨,紀(jì)昀似乎頗糾結(jié)于小說內(nèi)容的不真實(shí),但又對(duì)小說的教化功能寄以厚望,不同意對(duì)小說全面否定。在《四庫(kù)全書》的小說歸類及其《總目》里的小說家評(píng)論中,紀(jì)昀對(duì)小說文體的看法和態(tài)度有更為具體的表現(xiàn)。
《四庫(kù)全書》把小說列入“子部”,這可視為對(duì)《漢書·藝文志》傳統(tǒng)的繼承,但其中也暗藏玄機(jī),因?yàn)榧o(jì)昀所面對(duì)的小說創(chuàng)作現(xiàn)實(shí),與劉歆、班固時(shí)期的小說已有很大的差別。古典文言小說發(fā)展至宋明,出現(xiàn)了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以敘事為宗”的傾向,附庸于“史部”;一種是以“述道見志”為主的傾向,依托于“子部”。胡應(yīng)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里將小說分為六類,三類屬史,三類屬子,充分體現(xiàn)了小說在子、史之間搖擺不定的歸屬困境。紀(jì)昀把小說列入“真?zhèn)蜗嚯s,純疵互見”的子部,一定程度上回避小說文體真實(shí)性不足的“缺陷”,減輕小說體卑帶來的創(chuàng)作焦慮感。《閱微》“題詩(shī)二首”中提醒讀者“稗官原不入儒家”,其意也應(yīng)在此。
《四庫(kù)全書總目·小說家類》的敘述中,紀(jì)昀對(duì)小說文體有一段概括:
跡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yǔ)也。唐、宋而后,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真、妖妄熒聽者,固為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cuò)出其中。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fēng)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然則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雜廢矣。
紀(jì)昀首先指出早期小說的三個(gè)派別:雜事、異聞、瑣語(yǔ),這是他把小說劃歸子部的理論依據(jù)。接著,他在此基礎(chǔ)上歸納出小說的三大功用:“寓勸戒”“廣見聞”和“資考證”,藉此解決了小說在儒家文體價(jià)值體系中的合法性問題。這三大功用成為紀(jì)昀小說觀的核心,也是《閱微》這部小說文體實(shí)驗(yàn)的指導(dǎo)原則。
“寓勸戒”是指小說可以承擔(dān)起道德教育功能,這是紀(jì)昀對(duì)小說價(jià)值最為看重的一方面。他始終把倫理訓(xùn)誡放在著書的第一位,“儒者著書,當(dāng)存風(fēng)化,雖齊諧、志怪,亦不當(dāng)收悖理之言”(《閱微》卷六第31條),聲稱他的小說,“大旨期不乖于風(fēng)教”(《姑妄聽之序》)。《閱微》里涉及倫理的故事非常之多,古代社會(huì)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各種倫常關(guān)系,在小說中都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示,整部小說寫鬼事而不廢人事,處處散發(fā)“神道設(shè)教”的影子。《閱微》每敘述完一個(gè)故事,作者都會(huì)給出一段評(píng)價(jià),通常是他直接介入評(píng)價(jià),有時(shí)則是借用親友同僚之言乃至小說中狐鬼之言來完成,目的在于闡發(fā)故事大義微旨,實(shí)現(xiàn)風(fēng)教目的。
敘事里夾雜教訓(xùn)勸善的情況在明清小說中并不少見,但大多陳腐平庸,成了裝樣子的套話擺設(shè),而《閱微》里的議論卻是小說的精華所在,每每抉奧闡幽,詞明理正,展示一種智慧之美。《閱微》的議論常常涉及許多倫理難題,表現(xiàn)了學(xué)術(shù)探究的旨趣。如卷一第44條論地形吉兇與立身正邪之矛盾,卷二第13條關(guān)于身體、情感與誠(chéng)信的矛盾,卷七第21條人律與獸律等例,其思考的深度與廣度,遠(yuǎn)在時(shí)人之上。
“廣見聞”,“錄之亦足資博物也”(《閱微》卷十九第4條)是紀(jì)氏對(duì)小說的第二個(gè)要求。小說的魅力之一是記載各種神鬼奇事以饜足人們的好奇心,許多小說記載下奇異怪事就結(jié)束了,但《閱微》作為學(xué)者之文、“子部”之書,為了實(shí)現(xiàn)“資博物”的功能,不滿足于“知其然”,還努力“知其所以然”。《閱微》常常對(duì)所記異事“揆以天理”“以理推求”,展開質(zhì)疑、思考和解釋。如卷一第21條紀(jì)氏以為“此事荒誕,殆尊漢學(xué)之寓言”,然后分析漢學(xué)、宋學(xué)意氣之爭(zhēng),指出其“非無(wú)因而作也”。又如卷五第14條討論鬼是否有輪回,卷十三第5條質(zhì)疑“不識(shí)天下一灶神歟?一城一鄉(xiāng)一灶神歟?抑一家一灶神歟?”卷二十一第6條借狐精論生男生女之“原理”,卷二十一第21條論夢(mèng)之產(chǎn)生原因等例,無(wú)不表現(xiàn)出好學(xué)深思的“著書者之筆”特色。
“資考證”顯示了紀(jì)昀對(duì)小說價(jià)值的矛盾態(tài)度。盡管他深知小說“妄言”傳統(tǒng)而將之歸于子部,但學(xué)者的慣性使得他非常珍視文獻(xiàn)的考證價(jià)值,禁不住要為小說尋找到考證層面的意義,故將“資考證”列小說三功能之末位,意為小說記載的部分內(nèi)容可以用于學(xué)術(shù)考證,而不是要求小說直接承擔(dān)考證的功能。“資考證”的學(xué)術(shù)意識(shí),以及作者的博學(xué)多才,使得《閱微》敘事中呈現(xiàn)出一種學(xué)術(shù)化、考證化的傾向。《閱微》在議論中喜歡旁征博引,考鏡源流,具有一定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然而,小說內(nèi)容多涉神怪無(wú)稽之說,故《閱微》中多數(shù)考證僅是徒具形式,并無(wú)實(shí)質(zhì)內(nèi)容。如卷十三第30條,對(duì)族叔見怪獸一事,引《博異傳》《史記》《列異傳》《枯樹賦》《祭纛文》等三教九流之文論證此怪獸為女夜叉,雖材料宏富,結(jié)論荒唐可笑。此外,《閱微》講述故事時(shí),作者常會(huì)對(duì)筆下許多相關(guān)人物、地理、詞語(yǔ)補(bǔ)上“自注”,體現(xiàn)了學(xué)者的嚴(yán)謹(jǐn),然而有些“自注”似無(wú)必要,如卷二十三第23條:“余十歲時(shí),聞槐鎮(zhèn)一僧”,隨后自注:“槐鎮(zhèn)即《金史》之槐家鎮(zhèn),今作淮鎮(zhèn),誤也。”這樣的注釋對(duì)小說的理解并無(wú)幫助,只是一種學(xué)術(shù)習(xí)慣的流露。
《閱微》的創(chuàng)作體現(xiàn)了紀(jì)昀小說觀念,是紀(jì)昀對(duì)當(dāng)時(shí)流行的“才子之筆”小說進(jìn)行反擊的文體實(shí)驗(yàn)產(chǎn)品。盛時(shí)彥在《姑妄聽之·跋》里透露,他的老師紀(jì)昀對(duì)《聊齋志異》“盛行一時(shí)”的現(xiàn)象頗有微詞,認(rèn)為這類小說在敘事上過于詳盡,在倫理上、學(xué)術(shù)上站不住腳,“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必戲場(chǎng)關(guān)目,隨意裝點(diǎn)”,“今燕妮之詞、媟狎之態(tài),細(xì)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wú)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見而聞之?又所未解也”。紀(jì)昀把《聊齋志異》為代表的小說文體稱為“才子之筆”,而他心中的小說正統(tǒng)卻是“著書者之筆”。盛時(shí)彥評(píng)論說,《閱微》“辨析名理,妙極精微;引據(jù)古義,具有根柢,則學(xué)問見焉”,“灼然與才子之筆分路而揚(yáng)鑣”,這一附在《閱微》書中的評(píng)論是經(jīng)過紀(jì)昀同意的,顯然《閱微》是紀(jì)昀有意識(shí)樹立一種學(xué)術(shù)化小說的文體榜樣。
紀(jì)昀把小說劃入子部,在回避史部的真實(shí)性問題的同時(shí),也失去了史部以敘事為中心的文體認(rèn)同,造成了《閱微》“過偏于論議”、敘事粗疏的文體缺陷。而紀(jì)昀在《閱微》中進(jìn)行的小說議論化、學(xué)術(shù)化嘗試同樣沒有改變小說體卑的命運(yùn)。盛時(shí)彥稱贊《閱微》“雖托諸小說,而義存勸誡”。此一“雖”字,已含有為老師寫小說的行為進(jìn)行辯解之義。稍后的張維屏(1780-1859)說得更為明白:“或又言文達(dá)不著書,何以喜撰小說?余曰……稗官小說,搜神志怪,談狐說鬼之書,則無(wú)人不樂觀之。故文達(dá)即于此寓勸戒之方,含箴規(guī)之意。托之于小說而其書易行,岀之于諧談而其言易入。……觀者慎無(wú)以小說忽之。”他們認(rèn)為《閱微》志不在小說,而在“勸誡”。他們?cè)诰S護(hù)紀(jì)昀人格的同時(shí),忘記了紀(jì)昀對(duì)小說價(jià)值的肯定,忽略了《閱微》改造小說的苦心。《閱微》在后世之聲譽(yù)甚高,并非其小說文體改革的成功,而是紀(jì)昀的高才卓識(shí)難以企及,“雋思妙語(yǔ),時(shí)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故服膺、嗜好《閱微》者皆為學(xué)者文人。對(duì)于那些文化層次較低的典型小說接受群體而言,以“才子之筆”寫就的《聊齋志異》才是他們?yōu)橹耐耨Y的小說典范。
三、《聊齋志異》:克服焦慮的“孤憤之書”、“異史”之文
《聊齋志異》(以下簡(jiǎn)稱《聊齋》)創(chuàng)作時(shí)間早于《閱微》,但從文學(xué)敘事的角度來看,《聊齋》更像是后來居上、后出轉(zhuǎn)精的成功之作。其成功的諸多原因中,值得關(guān)注的是蒲松齡創(chuàng)作《聊齋》時(shí)的文體心態(tài)與文體理念。
蒲松齡(1640-1715)博學(xué)多才,科場(chǎng)失意,直到71歲,才按例補(bǔ)為貢生。坎壈的一生使他與官方正統(tǒng)意識(shí)形態(tài)始終保持一種疏離感,卑微的身份讓他對(duì)底層大眾文化生態(tài)有了深切的體驗(yàn)和認(rèn)識(shí)。他常常以草根的視角來看待通俗文化,積極參與通俗文化的創(chuàng)作,公開編寫了大量“田夫野豎矢口寄興”的俚曲。可想而知,寫作《聊齋》這樣的文言小說,對(duì)他來說沒有什么顧忌的了。《聊齋自志》中記錄了他對(duì)《聊齋》這部文言小說的看法: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zhǎng)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托曠懷,癡且不諱。展如之人,得勿向我胡盧耶?然五爺衢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頗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廢者。松懸弧時(shí),先大人夢(mèng)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粘乳際。寤而松生,果符墨志。……集腋為裘,妄續(xù)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從首兩句“披蘿帶荔”和“牛鬼蛇神”的用典看,“不擇好音”當(dāng)指《聊齋》語(yǔ)涉鬼神。小說文體常因此類“不雅馴”內(nèi)容為人所詬病,故此處“不擇好音”可視為蒲氏對(duì)當(dāng)時(shí)盛行的小說體卑觀念的表面承認(rèn),但在背地里他卻以屈原、李賀兩大天才詩(shī)人自比,把《聊齋》當(dāng)作“天籟”,可見他在心底深處對(duì)《聊齋》這部小說有著足夠的自信。當(dāng)然,在那樣一個(gè)時(shí)代,他的小說免不了會(huì)遭受“展如之人”(保守道德家)的指責(zé)和批評(píng),但他并不放在眼里,以狂放、“不諱”應(yīng)之。他相信自己是“病瘠瞿曇”(窮病和尚)轉(zhuǎn)世,與儒家本不相干,故能將儒家等級(jí)觀念擱置一旁,公然把《聊齋》這樣的“幽冥之錄”,當(dāng)成是自己一生最為重要的“孤憤之書”,在書里盡情地“遄飛逸興”“永托曠懷”。對(duì)蒲松齡來說,《聊齋》就是他的《史記》,不僅可以“償前辱”,還要“藏諸名山,傳之其人”。
蒲松齡對(duì)文言小說的態(tài)度也隱含于《聊齋》中刻意標(biāo)舉的“異”字之中。《聊齋》的書名“志異”并非隨手而寫,其間有微言大義。高珩《聊齋志異·序》說:“志而曰異,明其不同于常也。”這個(gè)“常”,當(dāng)指文字寫作理應(yīng)符合禮法倫常,以“六經(jīng)之文,諸圣之義”為范本,它們是儒家話語(yǔ)體系中得到確認(rèn)的經(jīng)典文體。體卑的小說顯然是被排斥在“常”之外的,一般的小說作者對(duì)此都諱而不言,《聊齋》卻公開宣稱自己是違背“常”的,是正統(tǒng)文體的異類。與此相應(yīng),在《聊齋》各篇的結(jié)尾,蒲松齡刻意地創(chuàng)造了“異史氏”這一特殊的稱謂來充當(dāng)故事的評(píng)論者,進(jìn)一步凸顯了他的小說獨(dú)立意識(shí)。從文體上看,“異史氏曰”這一說法至少雙重意義:一方面,“異史氏曰”體例與《左傳》“君子曰”、《史記》“太史公曰”類似,都是放在故事的結(jié)尾表達(dá)對(duì)事件的評(píng)價(jià)和感嘆,闡發(fā)敘事的意義。《聊齋》顯然有意識(shí)繼承經(jīng)、史中偉大的敘事傳統(tǒng),堅(jiān)持小說以敘事為中心,然后用“異史氏曰”來彌補(bǔ)敘事文體意義不足的缺陷。與李昌祺和紀(jì)昀分別從文字修辭和學(xué)術(shù)議論上尋找小說文體的意義的方案相比,蒲松齡顯然更高一籌。另一方面,“異史氏曰”的“異”字提醒我們,這個(gè)《聊齋》的權(quán)威評(píng)論者不屬于史家,暗示《聊齋》不屬于史學(xué)著作,《聊齋》只是在技術(shù)上繼承了經(jīng)、史的敘事,但內(nèi)容上、立場(chǎng)上與經(jīng)、史著述不同,“別是一家”。“異史氏曰”顯示了蒲松齡《聊齋》有意與正統(tǒng)的經(jīng)、史宏大敘事保持距離,確以保小說敘事的自由空間,最終實(shí)現(xiàn)了文學(xué)敘事的突破。
《聊齋》以敘事為中心的小說寫法,今天看來理所當(dāng)然,當(dāng)時(shí)卻是一個(gè)頗為大膽的實(shí)驗(yàn)。紀(jì)昀嘲諷《聊齋》“燕妮之詞、媟狎之態(tài),細(xì)微曲折,摹繪如生”,正是不滿意《聊齋》敘事過多;寫過文言小說《子不語(yǔ)》的袁枚也對(duì)《聊齋》敘事太“繁衍”頗有異議;甚至十分欣賞《聊齋》的馮鎮(zhèn)巒,也認(rèn)為《聊齋》是“以傳記體,敘小說之事”(《讀聊齋雜說》),其潛臺(tái)詞是:敘事技術(shù)為史部傳記的專業(yè)本行,狐鬼志怪的內(nèi)容才是小說文體的本質(zhì)所在,《聊齋》的敘事雖精彩,手法上卻越出小說文體的界限,侵入了史學(xué)的領(lǐng)地。也許是意識(shí)到這個(gè)表達(dá)所隱含的小說偏見,魯迅《中國(guó)小說史略》才改為“用傳奇法,而以志怪”來概括《聊齋》,以糾正馮鎮(zhèn)巒的說法。魯迅用“傳奇法”替代“傳記體”,意謂敘事并非專屬于史部,唐傳奇等古小說早已有之;以“志怪”替代“小說之事”,意為“志怪”只是“小說”題材中的一個(gè)類別,“志怪”不能完全涵蓋“小說”的內(nèi)容。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蒲松齡《聊齋》中關(guān)注敘事的重大意義,它突破了當(dāng)時(shí)正統(tǒng)小說(文言小說)的陳規(guī)慣例,為時(shí)人所不解,卻與現(xiàn)代小說觀念遙相契合,展示了超越時(shí)代的眼光和魄力。
從敘事的角度來看,《聊齋》的場(chǎng)景描寫、人物刻畫及情節(jié)安排都是十分出色的,馮鎮(zhèn)巒贊嘆“《聊齋》之妙,同于化工賦物,人各面目”,“寫景則如在目前,敘事則節(jié)次分明,鋪排安放,變化不測(cè)”。《聊齋》雖時(shí)有用典,但總體上采用簡(jiǎn)潔優(yōu)雅的文言來進(jìn)行敘事和描寫,有時(shí)能化用口語(yǔ)俚語(yǔ),生動(dòng)自然,富有表現(xiàn)力,如《王成》說王家之窮,“王呼妻出見,負(fù)敗絮,菜色黯焉”,寥寥數(shù)語(yǔ),給人印象深刻。又如《翩翩》里花城娘子戲言“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mèng)幾時(shí)做得?”與白話小說的沒有多大區(qū)別了。在情節(jié)安排上,作者在選擇題材和下筆時(shí)始終注意情節(jié)的曲折有味,力求寫法變化多端,緊緊地吸引住讀者。如《葛巾》“不惟筆筆轉(zhuǎn),直句句轉(zhuǎn),且字字轉(zhuǎn)”,故事緊扣人心。甚至在很短的一段文字里也可以做到懸念迭起,如《西湖主》書生陳明允誤入花園,等待主人處罰的過程一波三折,戲劇性極強(qiáng)。相比之下,《閱微》“專為勸懲起見,敘事簡(jiǎn),說理透,不屑屑于描頭畫角”,敘事略具梗概而已;《馀話》則志在詩(shī)文,敘事只是串聯(lián)詞章的線索,情節(jié)十分單薄。《聊齋》敘事中也有插入詩(shī)文的現(xiàn)象,但其比例遠(yuǎn)遠(yuǎn)低于《馀話》,且部分詩(shī)文還兼有重要的敘事功能,如《續(xù)黃粱》中的彈劾疏奏文字,兼敘曾孝廉得勢(shì)后的種種罪過,是故事發(fā)展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聊齋》在內(nèi)容選擇、文筆刻畫和價(jià)值取向中都表現(xiàn)出對(duì)主流、正統(tǒng)的倫理秩序一定程度的疏遠(yuǎn)和抗拒。盡管《聊齋》的立場(chǎng)未能完全脫離那個(gè)時(shí)代的忠貞孝悌觀念,但其故事情節(jié)的主要敘述驅(qū)動(dòng)力已不再是禮教的維護(hù)和追求,而是來自于情感與欲望,形成了所謂“多言鬼狐,款款多情;間及孝悌,俱見血性”(馮鎮(zhèn)巒《讀聊齋雜說》,會(huì)評(píng)本卷首)的尊情宣欲傾向。以作品的特色而言,如果說《馀話》是以文炫人,《閱微》是以理服人,那么《聊齋》最成功的地方,也許就是以情感人、以欲誘人。《聊齋》正面描寫了很多“狂人”“癡人”“癖人”,有情癡(《阿寶》)、棋癡(《棋鬼》)、花癡(《葛巾》)、書癡(《書癡》)、詩(shī)癡(《白秋練》)、石癡(《石清虛》)等等,記載了很多為了情和欲“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的例子,在禮教倫常之外發(fā)現(xiàn)了人生的價(jià)值。因此,《聊齋》的故事最為感人,《促織》令人憤慨,《趙城虎》讓人感嘆,《縊鬼》使人悲傷,《翠云仙》大快人心,《嬰寧》忍俊不禁,七情六欲在這里宣泄,壓倒了正面的陳腐說教。《聊齋》的“異史氏曰”也有異于經(jīng)、史正統(tǒng)的理性姿態(tài),言辭激情洋溢,形象鮮明,讀者恍若見“異史氏”或手舞足蹈(《鏡聽》),或怕案而起(《伍秋月》),或童趣盎然(《紅玉》),或沉痛哀戚(《縊鬼》),或熱潮冷諷(《金和尚》)。這些評(píng)論雖不如《閱微》冷靜深刻,卻具有前者所不具備的文學(xué)色彩,與文中的敘事相映成趣。
擺脫文體焦慮的蒲松齡獲得了文體創(chuàng)作的自由,在《聊齋》中充分發(fā)揮了他的敘事才華,最終寫出了享譽(yù)后世的文言小說杰作。但這種輕松的寫作心態(tài)也給《聊齋》的文體實(shí)驗(yàn)帶來一些不足,使得《聊齋》寫作不夠嚴(yán)謹(jǐn),出現(xiàn)“體例太雜”的問題。書中除了那些優(yōu)秀的長(zhǎng)篇敘事文章外,也有短不成章記異小文;“異史氏曰”有時(shí)議論過長(zhǎng),有蛇足之嫌;羼入詩(shī)文也偶有無(wú)關(guān)緊要的賣弄文字,然瑕不掩瑜。
總之,在蒲松齡的筆下,文言小說成了“孤憤之書”、“異史”之文,獲得了獨(dú)立的文體意義與價(jià)值。《聊齋》的敘事因此不再屈身于經(jīng)、史的藩籬之下,也無(wú)須用詩(shī)文或?qū)W術(shù)來裝扮自己,在主流話語(yǔ)之外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獨(dú)特生存空間,“司風(fēng)教者,重務(wù)良多,無(wú)暇彰表,則闡幽明微,賴茲芻蕘”。在自信的心態(tài)下,蒲松齡跳出宋明以來的文言小說規(guī)范,直接承接唐傳奇的敘事,大膽借鑒“低俗”白話小說的敘事手法,重啟了文言小說的敘事之路,最終形成了以情感欲望為內(nèi)核的虛擬敘事文體,造就了現(xiàn)代意義的文言小說經(jīng)典。
綜上所述,盛行于明清時(shí)期的小說體卑觀念給文人們的小說創(chuàng)作帶來一種焦慮心理,促使他們?cè)趯?shí)名創(chuàng)作的文言小說中進(jìn)行有意識(shí)的文體改革,力圖提高小說文體地位。考察這些文言小說的創(chuàng)作心理及其在文體上的成敗得失,為我們的理解和把握明清文言小說提供了一個(gè)觀察的視角。
注:
① 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guó)小說書目》卷六,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第127頁(yè)。
②③ 程毅中《古體小說論要》,華齡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45頁(yè)。
④ 王恒展《中國(guó)小說發(fā)展史概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頁(yè)。
⑤⑥ [明]瞿佑等著《剪燈新話》(外二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122、120頁(yè)。
⑧ 此處數(shù)據(jù)參考了陳大康《明代小說史》的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見該書第114頁(yè)。但氏著在統(tǒng)計(jì)時(shí)認(rèn)為《何思明游酆都記》一文詩(shī)文比例低于10%,似乎忽略了此文所引“何思明”《警論》的大量文字,這些文字和后面的銘文加起來約占全文篇幅的20%,故此把《何思明游酆都記》也算在10%以上之內(nèi)。
⑨ [清]錢謙益《列朝詩(shī)集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191-192頁(yè)。
⑩ 齊裕焜《明代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頁(yè)。
責(zé)任編輯:王思豪
*本文為國(guó)家社科基金重大項(xiàng)目“中國(guó)古代文體學(xué)發(fā)展史”(108LZD102)階段性成果。
廣東技術(shù)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