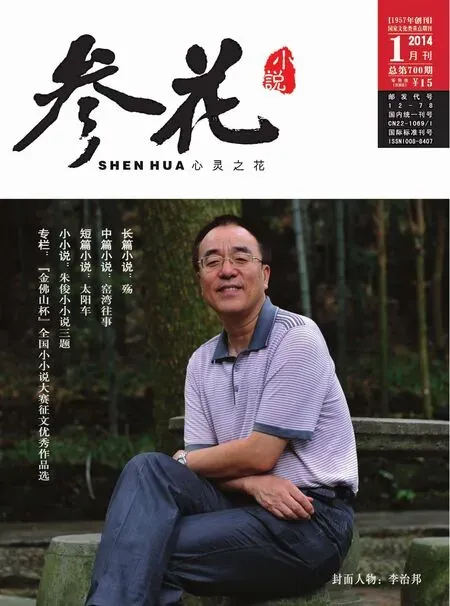阿呆的幸福
◎紫菀月
阿呆的幸福
◎紫菀月
阿呆其實不叫阿呆,可人們都習慣了喊她阿呆。
阿呆人有點懶,也有點傻。做姑娘時,連她6歲不到的侄女也跟著大人喊她的綽號“阿呆”。別家姑娘個個心靈手巧——紡紗,刺繡,納鞋底,織毛衣,樣樣都信手拈來。只她不會,刺繡讓人家幫著開了個頭就擱在那兒沒動靜了,一件毛衣打了3年還沒打成。
當與她同齡的姑娘們一個個都穿上嫁衣時,她還是待字閨中。用現在的話來講是“剩女”了,她在哥哥嫂子的眉高眼低下生活了好多年。終于,在她26歲那一年,有人做媒,把她嫁給了鄰村一個下鄉的大齡知青。那知青長得眉清目秀,戴著一副眼鏡,文謅謅的,一看就知道是個有文化的人。知青不但人長得俊秀,有文化,而且手也巧。他會干很多女人的活計,比如織毛衣,他織的毛衣很漂亮,那圖案、那花紋、那配色,一點也不遜于精于女紅的姑娘們。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還會疼人,不像村里的一些大男人粗粗咧咧。
那還是集體生產的時候,村里新來的媳婦一個個卯足了勁地比賽:插秧,種地,采桑葉,喂蠶……看誰做得又快又好。每一次,阿呆總是落在最后一個。別人說她,拿她當笑料,她不急也不惱,不慍也不怒,憨憨一笑就過去了。
一年后,阿呆為知青老公添了一對雙胞胎兒女。
阿呆在丈夫的疼愛中幸福地生活著。
日子過得飛快,集體生產結束了,開始了承包到戶。阿呆的一雙兒女也在一天天長大。阿呆的日子過得比村上一般的小媳婦滋潤多了。她的知青丈夫每過一年半載都會帶她去他的老家——上海大都市去轉轉,每次回來都會帶回很多新奇的東西:比如說裹著漂亮包裝紙的水果糖啦;比如說香噴噴的讓人聞了直流口水的奶油蛋糕啦;再比如說她給兒子買的小火車玩具啦……
那年夏天,一幫小調皮去她家玩,剛碰上她老公帶她從上海回來,她從包里抖出一些很漂亮的布料子,那絲綢一樣亮亮軟軟的料子啊,真羨煞了那些在場的小媳婦,她們一個個看得眼睛都發直了,這里摸摸,那里揉揉,真恨不得裹在身上穿了去。阿呆還樂呵呵地從包里掏出大把大把的大白兔奶糖分給村里的孩子們,那個年代的孩子們真叫饞啊,連糖紙都舔得干干凈凈。
村人的日子漸漸富裕起來。阿呆家前后左右漸次造起了樓房。那前后左右的樓房把阿呆家低矮的平房圍裹著,很多年,阿呆家都窩在這樣的洼地里,頭頂只有院子大的四方的天。于是,阿呆再一次成為那些精明能干的長舌婦們的飯后笑資。
這樣又過了很多年,那一年,阿呆老公的一個在大城市做生意的姐姐寄來了大把大把的鈔票,讓他們把樓房給蓋起來。于是,阿呆住上了新樓房。她老公的姐姐又資助了阿呆兒子所有上學的學費。那一年,阿呆兒子剛上初中。
日子就這樣不急不緩地過著。
阿呆的女兒出嫁了。
阿呆兒子高考了。
阿呆兒子考上了師范學院。
阿呆兒子畢業了。
阿呆兒子分在了市級中學當了老師。
阿呆兒子又調到了高一級的學校,并成為那所學校的骨干教師。
阿呆的兒子娶媳婦了,是同校的一位老師,賢惠通達。
正當村里當年談論阿呆的那些長舌婦整日里與媳婦們鬧得雞飛狗跳的時候,小兩口把阿呆老兩口接到了城里。阿呆美美地過起了城里人的生活。最美的是,阿呆的媳婦待阿呆如自己的親生母親一般,“媽,媽”叫個不停,這讓本來一輩子笑呵呵的阿呆更是樂得合不攏嘴了。阿呆的兒媳常對阿呆說:“媽,謝謝您培養了這么好的兒子,讓我找到了這么好的老公。”
“哎,有福的阿呆!”在阿呆去了城里之后,村里的長舌婦們總是這樣感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