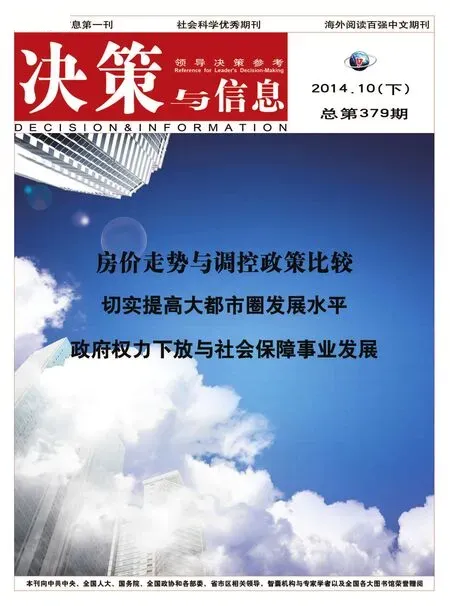錄音保全公證若干法律問題研究
刁姝
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證處 四川成都 610015
錄音保全公證若干法律問題研究
刁姝
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證處 四川成都 610015
隨著現代社會信息化的發展,視聽資料這種證據形式越來越常見的出現在訴訟中。在民事訴訟活動中,一些當事人為了證明待證事實,以私人秘密錄音的方式記錄當事人之間或與其他人之間的談話內容。然而,私自錄制的談話內容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可能侵犯對方的隱私權,其證據能力未置可否,現有的相關法律解釋中也否定了部分私人錄音的證據能力,錄音的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問題在學術界中也眾說紛紜。根據證據法學中的相關經驗法則,經過公證的證據其證明力一般大于其他普通證據。因此,許多當事人尋求通過公證的方式確認證據的證據能力及證明力,但錄音證據存在諸多問題,其公證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錄音保全;公證;法律效力
1、公證的效力
近些年來,我國的公證事業實現了快速的發展,這說明公證在市民生活中被應用的越來越廣泛,不論是財產關系還是身份關系中,公證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張衛平教授認為,公證具有證明效力、執行效力和要件效力,而證明效力無疑是最為重要的核心效力。[1]在我國,公證機構是唯一、合法的公證主體。根據《公證法》的規定,公證機構是依法設立,不以營利為目的,依法獨立行使公證職能、承擔民事責任的證明機構。“證明機構”的性質說明了公證活動是證明客體的真實性、合法性。例如在遺囑公證中,遺囑經過公證被證明了其合法性和真實性,并且由于法律的規定,其效力高于其他一般遺囑。可見,公證活動的證明效力公證機構的權威性來源于法律的授權,“依法獨立行使公證職能”是公證機構具有社會公信力的基礎,因而其所作出的公證文書才具有較高的證明力。公證民事責任承擔的主體是公證機構,公證的公信力也由公證機構予以保證。
從證據法上看,證據應當具有合法性、客觀性和關聯性。公證是公證機構對民事法律關系中事實的合法性和客觀性予以證明的活動。雖然公證文書本身不是證明待證事實的證據,但都加強了公證的事實或證據的合法性和客觀性。根據《公證法》和《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的相關規定,經過公證的事實和文書,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依據,但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的除外。
從法律的規定可以解讀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公證的證明效力是法定的。公證的程序和效果由法律規定,它排除了法官的自由心證。經過公證的法律事實,屬于免證事實的范疇,其效力甚至強于作為科學證據的鑒定意見,具有完全的證明力。其次,公證的證明效力優先于其他證據。當存在多個證據證明同一事實之時,經過公證的證據事實,其證明力大于其他證明材料。以《繼承法》為例,除遺贈扶養協議之外,公證遺囑的效力大于自書、代書、錄音、口頭遺囑,即使這些遺囑是后于公證遺囑作出的,也不得撤銷或變更公證遺囑,除非再次通過公證的方式。最后,公證的公證效力具有一定的相對性。公證程序是由申請人與公證機構參與的活動,公證機構在對公證事實的審查時可能由于申請人的“一面之詞”,僅對部分內容進行證明,脫離事件的整體,所以可能造成公證文書最終僅能證明某一個時間點某一個單純性的事件的客觀性,客觀性背后的真實情況不能通過公證書達到目的。同時,公證員作為法律執業人員,難免由于主觀因素對公證的事項出現錯誤或偏差,正如在對抗訴訟程序中的法官一樣,不可能百分之百保證其判決的正確。因此,不能將公證的證明效力絕對化。公證的事實也只是法律上的推定,是“可反駁的推定”,[2]只要有足夠充足的證據,可以推翻已經公證的事實。
總的來說,公證的證明效力仍然是一種強效力,在很多領域中,都占據著排他的地位。在我國,當事人依據經過公證的債權文書可以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足以見得其效力之大。因此,公證機構在對公證的事實或材料進行審查時需要嚴格慎重,對其真實性和合法性負責。
2、錄音證據的認定問題
以《民事訴訟法》對證據形式的分類,錄音證據屬于視聽資料。視聽資料形式證據的出現是伴隨著信息化的發展而來的,而且視聽資料該種證據形式在訴訟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視聽資料是借助多媒體才能夠展現其內容的證據,常見的視聽資料就是錄音和錄像兩種。一般來說,錄音錄像資料能夠客觀地記錄和反映發生的事實,能夠生動、直觀地展示出人物和環境等信息,對信息的描述和展現也具有連續性、準確性的特點。[3]在錄音證據中,錄音往往記錄的是談話內容,而這些談話內容一般同時也以言詞證據的形式呈現在法庭上。所以,錄音證據的作用往往在于加強或反駁言詞證據。
然而,錄音證據卻并沒有因為上述優點容易被法官接受,在錄音證據的認定仍然受制于其他因素。首先,錄音所使用的多媒體設備直接影響錄音的效果。由于設備所限,錄音的效果千差萬別,很多錄音難以辨別談話內容,而有些使用手機進行對通話錄音的只有其中一方的聲音。其次,錄音的環境也影響錄音效果。談話環境比較嘈雜的情況下,同樣也不易辨別談話內容。再次,電子性證據的性質也使得錄音容易被剪切、篡改。不同的語境下,同樣的一段話會被理解為不同的意思表示。某些關鍵談話內容被剪切后,意思就可能完全改變。即使錄音未被剪切,不完整的錄音也有導致歧義的危險。最后,當事人私自偷錄的錄音可能侵犯談話對方的隱私權,錄音在合法性上存在瑕疵,不能在法庭中適用。
可見,錄音證據在司法實踐中可能會存在爭議,尤其是偷錄的錄音是否符合證據的合法性要求,則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雖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認定了私自錄制談話內容行為的不合法性,但從學理上講依然值得商榷。有學者指出不能以言論自由為由妨礙權利救濟,尤其是當私自錄音成為抑制違法行為、進行權利救濟的必要甚至是唯一可選手段之時。[4]筆者也認為,私自錄音并非一定侵害了對方的合法權益,因此不能一概而論。
因此,錄音證據在法庭中往往也是以輔助證據的定位出現,對已有的事實進行鞏固或反駁。但是相對于言詞證據來說,錄音的主觀性并不強,因而被認可的錄音所反映的事實比較難以被推翻。可見,錄音證據在訴訟中仍然處于不可棄置的地位。
3、錄音公證的合理界限
根據《公證法》的規定,公證機構可以根據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的申請辦理保全證據的相關事項。證據保全原本是指在民事訴訟開始之前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對可能滅失或今后難以取得的證據進行調取和固定保存的行為。公證保全同樣依照這一法理,由公證機構對證據進行提取、收存和固定,其效果在于保持了證據的證明力。
為了使錄音在法庭上更加容易被法官采納,許多民事訴訟當事人選擇以公證的方式將錄音資料保全固定。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規定》,經過公證的證據其證明力一般大于其他證據資料。該規定中的表述反映了法官在認定事實過程中所運用的經驗法則,可見,公證機構在保全證據的同時同樣應當負擔起與法官相同的,對證據進行審查的責任。證據保全的公證一旦作出,法官將受到公證效力的約束,甚至可能直接影響案件裁判的結果。《辦理保全證據公證的指導意見》中為公證員的實踐操作提供了依據,但現實中,公證員在對當事人提出采用錄音方式取得談話內容時是否應當表明身份、對于當事人談話對象的真實性等問題存在著爭議,因此公證機構對申請人辦理錄音證據保全公證相當審慎。
首先,嚴格審查申請理由。證據保全的適用情形有限,是為了防止證據滅失。換句話說,保全的證據必須有可能滅失或難以提取的情形。在錄音證據中,申請人必須證明進行錄音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以及該錄音所要證明的事實。目前錄音公證的市場需求比較高,但是由于錄音證據的特點,接受辦理的公證機構較少,公證機構多要求當事人在公證員面前撥打電話。近年來,“安存語錄”錄音平臺建立了給當事人提供了一段時間內電話錄音的服務,申請人可以向公證處申請對其賬號上的某一時間段的電話錄音申請保全,對于公證機構來說,這種保全脫離了見證當事人撥打電話的過程,僅僅證明了從錄音平臺上截取錄音片段的事實,也并非錄音保全公證。
其次,嚴格遵守公證程序。公證機構在錄音過程中應當保持中立,不得參與到錄音中。錄音結束后,公證機構應當對錄音資料予以審查,確保其完整性,并在此基礎上出具公證書,對該錄音予以公證保全。錄音的公證保全作出后,公證機構還必須注意對錄音資料的妥善保管,防止錄音資料在存放過程中被篡改。
再次,錄音方式必須合法。證據的合法性是證據具備證據能力的關鍵,使用法律禁止的方式和手段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依據。偷拍偷錄的證據應當把握限度,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錄音的器材也只能限定在日常使用的錄音設備,不得使用特殊的竊聽器材。威脅、引誘、欺騙等手段取得的錄音,不能違背他人的真實意志。
最后,確保錄音的真實。由于證據保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的心證,公證機構必須對錄音過程的真實性負責。錄音中談話雙方的身份、主要話題、錄音場合等因素,公證機構必須保證其客觀真實。但是對于錄音中的談話內容所反映事實的真實性,公證機構并不負責。電話公證錄音中往往難以確定通話對方的身份,因此公證機構在受理時務必持慎重的態度,避免申請人與他人串通,騙取錄音證據的保全。
[1]張衛平.“公證證明效力研究”,《法學研究》,2011年第1期,第98頁.
[2]黃祎.“關于我國公證效力的解析”,《政治與法律》,2006年第5期,第115頁.
[3]宋石.“試談‘偷拍偷錄’視聽證據的認定”,《河北法學》,2002年第4 期,第72頁.
[4]黃耀明.“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從最高法院關于錄音證據的司法解釋談起”,《現代法學》,2002年第3期,第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