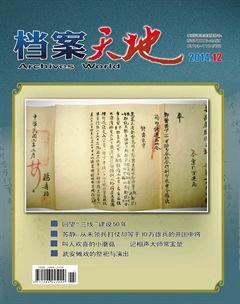回望“三線”建設(shè)50年
郭紅敏
“三線建設(shè)”,曾經(jīng)是一個響亮的名字。從1964年開始,面對復(fù)雜的國際形勢變化,國家在河南等13個省份的崇山峻嶺間展開了規(guī)模巨大的“三線”建設(shè)。河南南召、魯山、濟源等地的深山腹地就布局有諸多軍工企業(yè)。它們曾極其神秘,出于保密需要,這些生產(chǎn)炮彈等武器的企業(yè)對外都有自己的代號;它們曾一度輝煌,一個軍工企業(yè)就是一座功能完備的“軍工城”。50年過去了,這些“三線”建設(shè)者們在這里如何度過了他們青春和暮年?
“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
1970年10月,21歲的馬保清以一名民工的身份,到河南濟源參加國內(nèi)著名的531國防工程建設(shè)。出生于陜西寶雞的馬保清,喜愛文藝演出。來之前,他是新鄉(xiāng)地區(qū)文工團的一名演員。1973年,馬保清考入東北工學(xué)院自控系,1977年重返531工程總指揮部,負責(zé)自控系統(tǒng)的設(shè)計安裝調(diào)試運行。
擁有13個分指揮部的531工程,東西跨度近100公里,南北寬度近50公里,橫跨濟源、孟州、洛陽吉利區(qū)三地。仿佛是一夜之間,昔日人跡罕至的王屋山下,涌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兩萬多建設(shè)大軍和來自河南各地的民兵團和建筑工人。沒有地方住,有的就在山坡上搭個帳篷。馬保清在《531贊歌》回憶錄中寫道:1970年開始興建的531工程是當時我國建設(shè)的最大的火炮廠。為了防止蘇聯(lián)和美國對531工程的破壞,于是,這個巨型軍工企業(yè)就選址在太行山南側(cè)的千溝萬壑之中。有人梳理建國60年中國流行語發(fā)現(xiàn),“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成為1964年的流行語。與之匹配的還有“好人好馬上三線”、“深挖洞、廣積糧”等口號。
1964年5月之后,由于蘇、美加緊了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中央決定將全國劃分為三類地區(qū):前線、中間地帶和后方,分別稱為“一線”、“二線”和“三線”。今后,要重點開發(fā)和建設(shè)中西部地區(qū)的三線地域,轟轟烈烈的“三線建設(shè)”由此展開。1969年發(fā)生珍寶島之戰(zhàn),全國備戰(zhàn)氣氛日趨濃厚,“三線建設(shè)”速度加快。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三線建設(shè)自1964年至1980年歷時17年,涉及我國中西部13個省、市、自治區(qū),國家累計投資2052億元,先后安排了1100個大中型建設(shè)項目。國家對河南投資高達109億元,建設(shè)了100多個大中型骨干項目。
地處伏牛山腹地的魯山縣,被國防部秘密定為“戰(zhàn)爭及緊急狀態(tài)指揮中心”,簡稱“07號基地”。那時,南召縣以云陽鎮(zhèn)為核心建成了國營紅陽機械廠、國營紅宇機械廠、國營向東機械廠,方城縣建成了國營中南機械廠,鄧州建成了國營星光儀器廠,鎮(zhèn)平建有國營華夏儀器廠和國營云光儀器廠等一批隸屬于國家的軍工企業(yè)。其中,紅陽廠、紅宇廠、向東廠、中南廠生產(chǎn)各種炮彈,星光廠、華夏廠和云光廠等生產(chǎn)軍用照相機、望遠鏡和炮鏡。
“三線人”的青春印記
在那個火熱的年代里,馬保清能為自己參加“三線建設(shè)”而激動不已。那時,工地上到處張貼著“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把三線建設(shè)好,讓主席睡好覺”的標語。
1971年7月,馬保清被531工程總指揮部特招,在一分部進行文藝演出。他隨一分部文藝宣傳隊,走遍了13個分部。一分部散落在濟源市虎嶺河谷地帶的幾十條山溝之中,廠區(qū)長約15公里,是531工程中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分部。座落在九里溝大峽谷的二、三分部的生產(chǎn)區(qū)、辦公區(qū)、生活區(qū)、服務(wù)區(qū)已經(jīng)全部建成。后因林彪叛逃事件,工程停工,這里曾一度成為中央第二政法干校和河南省第四監(jiān)獄所在地。現(xiàn)在,這里一片凄涼,鐵路專用線已經(jīng)沒有鋼軌,廠房已經(jīng)荒廢。四分部位于濟源蟒河上游峽谷,近萬名職工和家屬至今還生活在這里。十一分部位于焦枝鐵路黃河鐵路大橋西側(cè)的山溝里,這里要建成全國最大的炮彈引信廠。人馬撤走后,幾十棟建筑散落在黃河北岸的溝溝壑壑間。十三分部是531工程中唯一沒有建在山區(qū)的分部,它建在黃河灘上,一眼望不到邊。531工程的最終產(chǎn)品——各種火炮,將在這個靶場做各種試射。
除了連綿不絕的廠房外,531工程一分部和四分部還相繼建成了職工住宅樓、文化宮、職工醫(yī)院、學(xué)校、招待所等諸多配套設(shè)施。這里,就是一座設(shè)施齊全、功能齊全的“軍工城”。
上世紀70年代初期,為了對531工程實行有效的管理,國家決定在其管轄范圍內(nèi)成立地市級的河濱市。林彪出事后,531工程停建,河濱市也成了一紙空文。后來,河南省決定在531工程范圍之內(nèi)成立濟源工區(qū),和地市平級,下設(shè)各級管理機構(gòu)。那時,濟源工區(qū)辦公樓已經(jīng)建成,工區(qū)文工團也已成立,后來又因故不了了之。
1971年9月至1972年1月期間,馬保清成為531工程總指揮部采購組成員,他和軍代表一起外出采購。那時的馬保清,充滿激情,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因為工作敬業(yè),吃苦耐勞,時任531工程總指揮部總指揮、河南省軍區(qū)副司令員的彭輝,親自獎給他一件藍色勞動布工作大衣。這在當時可是一件了不起的獎品,這件藍大衣一直陪伴了馬保清10年。1992年,馬保清調(diào)入鄭州中原制藥廠,2009年退休。不管他身在何處,在兵工廠的這段日子,已經(jīng)成為他一生中最珍貴的記憶。
不能穿帶釘子的鞋
“三線建設(shè)”,有“大三線”和“小三線”之分。隸屬于機械工業(yè)部的企業(yè)俗稱“大三線”,省屬地方軍事工業(yè),俗稱“小三線”。
根據(jù)中央部署,河南省委、省軍區(qū)確定1965年至1966年在豫西伏牛山東麓的魯山、南召、宜陽等縣境內(nèi)布局和建設(shè)8個輕武器及彈藥工廠,同時還規(guī)劃建設(shè)與之配套的項目。
于是,輕機槍廠、槍彈廠、工具廠、鑄鍛廠、紅旗醫(yī)院6個項目建在了魯山;迫擊炮廠、迫擊炮彈廠建在了南召;手榴彈廠、硝銨廠、雷管導(dǎo)火索廠建在了宜陽。
遵照 “靠山、分散、隱蔽”的方針,河南把保密性較強的輕武器及彈藥工廠,規(guī)劃建在較為隱蔽的山區(qū),把服務(wù)性工廠設(shè)在半山區(qū)或交通便利的縣城附近。
相關(guān)資料顯示,截止1969年底,12個河南地方軍工企業(yè)和一個戰(zhàn)備醫(yī)院基本建成。它們分別是:設(shè)計年產(chǎn)100萬枚木柄手榴彈和10萬枚地雷的黃河機械廠,年產(chǎn)25000支半自動步槍的中新機械廠,年產(chǎn)1500挺輕機槍的華原機械廠,年產(chǎn)1500門迫擊炮的長江機械廠,年產(chǎn)1億發(fā)槍彈的興州機械廠等。第七機械工業(yè)部為這些兵工廠擬定了工廠代號,華原機械廠代號為“9676”,長江機械廠代號為“9617”,興州機械廠代號為“9641”。531工程在緊張施工之時,國營東風(fēng)機械廠已經(jīng)建成投產(chǎn)。雄踞在南召縣深山里的東風(fēng)機械廠,是一個迫擊炮彈廠,對外代號是“9623”,設(shè)計年產(chǎn)迫擊炮彈5萬發(fā)。endprint
1967年5月,30歲的劉應(yīng)保成為國營東風(fēng)機械廠的一名職工。劉應(yīng)保是河南鄧州人,他從部隊復(fù)員后被分到山西工作,成為國營763廠的一名技工。國營東風(fēng)機械廠籌建后,根據(jù)需要,他被調(diào)到這里。那時,這里一片荒蕪。最初,劉應(yīng)保住在搭建的帳篷里,后來借住在太山廟公社的衛(wèi)生院里。公路修好后,在山坳里建起了幾排職工宿舍。幾個月后,劉應(yīng)保和參加培訓(xùn)回來的職工一起搬進了職工宿舍。
1969年底,該廠生產(chǎn)的迫擊炮彈,在附近的靶場試射成功。1970年初,東風(fēng)機械廠正式生產(chǎn),劉應(yīng)保曾擔(dān)任東風(fēng)機械廠火控機械車間副主任。1982年,東風(fēng)機械廠停產(chǎn),開始上馬鋼瓶生產(chǎn)線。1992年,劉應(yīng)保退休。劉應(yīng)保告訴筆者,東風(fēng)機械廠非常注重保密教育和安全教育,廣大職工時刻防止間諜竊取情報。廠里還要求,在火控機械車間上班的職工,不能穿帶釘子的鞋,一律穿膠底鞋。
蕭條的“軍工城”
短短幾年內(nèi),南召、魯山等地的大山深處崛起了一座座“軍工城”。一個軍工企業(yè),就是一個城市部落。每個企業(yè)除有大規(guī)模的住宿樓和廠房外,還有各自的文化宮、電影院、溜冰場、游泳池、舞廳、醫(yī)院、學(xué)校、招待所、郵局、銀行等配套設(shè)施。一些建筑已經(jīng)成為刻有那個年代鮮明印記的工業(yè)遺產(chǎn)。
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魯山崛起了10家制槍造炮的兵工廠。魯山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軍事要地。每個兵工廠除建有辦公樓、住宿樓和生產(chǎn)廠房外,均有各自的配套服務(wù)設(shè)施,廠區(qū)社會功能十分完善。據(jù)統(tǒng)計,江河機械廠、興州機械廠、達昌機械廠等10家軍工企業(yè)占地5278畝,建筑面積30多萬平方米,職工3萬多人。另外,魯山縣還建有國營259儲備庫、某部隊油庫、某部隊軍械庫等戰(zhàn)備倉庫和武漢空軍航修廠、地下軍事指揮中心、魯山機場等軍事基地。
1968年,國營向東機械廠在南召縣云陽鎮(zhèn)境內(nèi)選址興建,職工來自全國各地。向東廠主要生產(chǎn)火箭彈,對外的代號是“5143”。
在那個火熱的“三線建設(shè)”年代,向東廠涌現(xiàn)出了一批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據(jù)統(tǒng)計,出席省市重要會議的代表9人,省市以上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49人,廠級勞模和生產(chǎn)標兵共計37人。
1980年以后,隨著國際形勢緩和,河南軍工企業(yè)開始“軍轉(zhuǎn)民”。現(xiàn)在,這些以前鮮與外界聯(lián)系的神秘兵工廠,有的繼續(xù)承擔(dān)生產(chǎn)少量軍工產(chǎn)品的任務(wù),有的實行政策性破產(chǎn),有的實行改制。于是,一些職工下崗,一些職工買斷工齡外出打工,老廠變得愈發(fā)蕭條。這是眾多軍工企業(yè)的歷史宿命。
上個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400萬知識分子、技術(shù)骨干構(gòu)成的“三線人”,衍生出了數(shù)千萬后代,他們曾在崇山峻嶺間的兵工廠里學(xué)習(xí)、生活甚至工作。如今,大部分二代、三代“三線人”紛紛到外地打拼。對他們來說,在兵工廠生活的那段時光,雖然遙遠但仍很眷戀。
有網(wǎng)友在《我們都是兵工廠的孩子》一文中寫道:我們是在兵工廠長大的孩子,從在廠里醫(yī)院出生的那一刻,你我就在這個小小的世界里開始了人生。每天早上,我們被家長送到托兒所的門口,開始了一天的生活。我們從小說著普通話,在這個廠里長大。我們知道什么是齒輪,知道什么是粉末冶金,知道什么是熔銅兵工廠人……
一些已經(jīng)離世的“三線人”,有的魂歸東北等故鄉(xiāng),有的就葬在兵工廠附近的山坳里。每年春節(jié)和清明節(jié)時,他們的后代就從全國各地回到這來祭奠長眠在這里的先輩們。
暮年時的心理失落
天剛蒙蒙亮,72歲的徐繼民就穿衣起床。他在屋里忙碌了一陣后,去文化宮前的廣場上鍛煉身體。
這是10月中旬的一天,靜靜地躺在南召縣皇后鄉(xiāng)群山懷抱中的紅陽廠,如一位老人,沉睡了一夜后,睜開了惺忪的眼睛。穿越廠區(qū)的這條河流,依舊終年流淌不息;徐繼民眼前那些連綿起伏的山嶺,依然滿目青翠。轉(zhuǎn)眼間,40多年過去了,徐繼民迎來了退休后每天早起鍛煉的暮年時光。此時,紅陽廠區(qū)寬闊的街道上,冷冷清清,沒有了往昔喇叭里傳出的歌聲和來來往往的人流。在紅陽廠的標志性建筑——文化宮前,徐繼民碰到了幾個熟悉的老哥們,他們互相寒暄著。前幾天,徐繼民回了老家周口一趟,他和大家談起了回家后的感受。
上世紀70年代初期,從部隊復(fù)員分到東北某兵工廠的徐繼民,被抽調(diào)到國營紅陽機械廠工作。當時,徐繼民工資比較高。他姊妹多,家庭生活困難,家人也沒少跟著沾光。
這次回老家,徐繼民發(fā)現(xiàn)家鄉(xiāng)變化很大,一些農(nóng)村的親戚開著小汽車,有的在縣城買房。這讓徐繼民有一種失落感。徐繼民每月領(lǐng)著2000多元的退休金,夫妻倆至今仍住在40多平方米的職工公寓里。一個兒子在紅陽廠上班,一個兒子在外打工。在紅陽廠干了一輩子,徐繼民沒有能力為兒子買一套商品房。在近20年的時光里,徐繼民也有過滿足感。在紅陽廠上班,他端的是鐵飯碗,福利也多。他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工廠發(fā)的。職工們吃的好,穿的也好。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這里的職工們還穿著令人羨慕的锃亮皮鞋。那時,有6000多職工的紅陽廠不但配套設(shè)施齊全。當時在南召縣,紅陽廠的教學(xué)質(zhì)量和醫(yī)療技術(shù)有口皆碑。
如今,夕陽下的紅陽廠,如一位容顏已經(jīng)老去的垂暮老人。在紅陽廠廠區(qū)一面不起眼的墻壁上,寫著“三十年艱苦奮斗兩代同心共筑軍工神奇,新世紀開拓進取五千英杰再創(chuàng)紅陽輝煌”黃色字樣。墻壁前瘋長的一些雜樹,掩蓋了部分字體。站在這里,給人一種英雄暮年的感覺。
著名學(xué)者、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陳東林在其專著《“三線”建設(shè)——備戰(zhàn)時期的西部開發(fā)》中這樣評價:“從西北人跡罕至的荒原沙漠,到西南交通閉塞的深山僻谷,‘三線建設(shè)會戰(zhàn)工地的動人事跡隨處可見,不勝枚舉。正是靠這種高度的愛國熱情和忘我的奮斗精神,‘三線建設(shè)者們建起了我國可靠的戰(zhàn)略后方基地。他們在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物質(zhì)財富的同時,也為我們留下了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財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