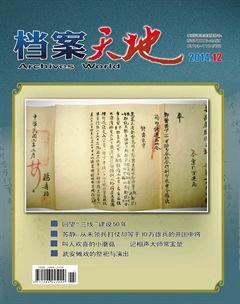叫人歡喜的小蘑菇
烸鉑
常寶堃,藝名“小蘑菇”,1922年5月5日生于河北省張家口市,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常寶堃于1931年拜張壽臣為師學習相聲,后與趙佩茹合作,在京津一帶演出。抗日戰爭期間常寶堃在天津與陳亞南等組織“兄弟劇團”任團長。因編演相聲《牙粉袋》、《過橋票》等而遭國民黨政府迫害。新中國成立后,編演了《新燈謎》、《思想問題》等新相聲,擅演曲目有《五紅圖》、《批三國》等。1951年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同年4月23日在朝鮮光榮犧牲。
“口外”出了個小蘑菇
1922年5月,常寶堃出生在張家口。他幼年學藝,從小就聰明伶俐,招人喜愛。不到一歲的時候,兩個小手托著個破鑼找人要錢,因為大家喜歡,誰見了都給他錢。有的人還要逗逗他,故意不給他,看他怎么辦。小寶堃主意很多,誰也沒教過他,就知道給人家抓抓撓、打個哇哇什么的,把人家逗得哈哈大笑。剛滿六歲,就手提裝水的破鐵筒,冒著口外的寒風,跟著父親流浪街頭巷尾“畫鍋”變戲法,圍觀的人們身穿棉衣、老羊皮襖揣著手,可是他卻光著突露肋骨的小脊梁表演“翻膀子”,兩手攥緊一跟小棍兒,從前胸硬掰到后背。他的小脊梁凍得發紫,小臉兒凍僵,小嘴兒索索發抖。年邁的老大娘看著孩子心疼地說:“快把膀子放下來吧!”還有人質問我父親:“這不是你的親孩子吧?”常寶堃翹起大拇指說:“這是我的親爸爸,沒錯兒。”他的話引起人們一陣辛酸的笑聲。接著,爺兒倆說上一小段相聲。每次都是變一套,說一段,久而久之,群眾漸漸地熟悉了他。因為張家口出產蘑菇,后來漸漸地,“小蘑菇”就成了常寶堃的藝名。小蘑菇這個愛稱有兩層含義:蘑菇是張家口一寶;口蘑,味道非常鮮美!暗喻他嘴上的活兒好,鮮香。
常寶堃自幼記憶力很強,父親怎么教,他都能一字不錯地記住。父親原是學京戲的,他叫常連安,就是排的“連”字輩。后來因為倒嗓,聲音失潤,才改行變戲法。對于相聲,他當時是門外漢。可是看到常寶堃說相聲比變戲法更靈,也更吸引觀眾,便有了讓他學說相聲的打算。
1930年,快九歲的常寶堃跟隨父親和弟弟一起流浪到天津,在“三不管”撂地賣藝。上世紀三十年代,天津工商業十分發達,各種工廠、貨站、銀行等將近兩萬處,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曲藝演出的繁榮。據不完全統計,在報紙登載演出廣告的藝人就有三百多人,還有更多的是沒有錢登廣告,在街頭賣藝為生的民間藝人。此時,年僅九歲的小蘑菇已經能說三十多段相聲了。他記憶力強,嗓音獨特,好學勤練,和父親的配合更是幽默和諧,贏得了不少觀眾的喜愛。
在名門中精湛技藝
小蘑菇聰明伶俐,也引起了一個藝人的注意,他就是陳榮啟,當年紅透北京的一位評書藝人,學習過京劇和相聲。在連續三天聽了小蘑菇演的相聲后,陳榮啟興奮地找到從小和自己一起長大的好朋友相聲名家張壽臣,希望他能收小蘑菇為徒。作為名家,張壽臣對徒弟的條件要求極為嚴格,比如,必須是北京人,眼睛要大,伶俐且不油滑,能言但不貪嘴,規矩而不木訥。小寶堃的長相好,腦子快,特別規矩懂事,正符合張壽臣的條件。張先生一見到常寶堃,喜歡的不得了,說了一句話:這孩子就是個說相聲的坯子。
從此,小蘑菇常寶堃就開始跟著師傅張壽臣學習相聲,那時,張壽臣的名氣正旺,除了要在小梨園等游藝場演出,早晚還要應付電臺和各種有錢人家里舉辦的堂會演出邀請,每天日程都排得滿滿的。而小蘑菇每個白天也要跟著父親演出,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所以,他們師徒的傳藝、授藝只能在夜里進行。張先生在培育寶堃上費盡了心血,在學藝上嚴格要求,有時候師母都看不下去了,在一旁勸張先生,讓孩子歇會,張先生反而說,我這不也是為他好嗎!我讓他把這段學會了,不也是給他錢嗎!
后來,父子倆放棄了戲法,走上舞臺正式說相聲。那時候常寶堃口齒清脆,童聲洪亮,站在凳子上表演,年齡還不滿十歲。在師父的嚴格要求和手把手的教導下,常寶堃在天津很快就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相聲新星,“小蘑菇”這個名字也在京津兩地引起轟動。從此,小蘑菇常寶堃告別了撂地賣藝的生活,不但進了雜耍園子,還到廣播電臺直播,在影院放映電影前加演相聲。
那時他整天忙碌著趕場演出,時間很緊。每天一大早起來便沖著墻背誦貫口活,練吐詞咬字,睡覺前叨咕著臺詞,走路也想著臺詞。他在電車上背詞兒,不知有多少次坐過了站。有時候,吃著飯停下來,凝神思索著,筷子掉在桌子上還不知道。常寶堃的媽媽理解地說:“寶堃,先吃飯,別背詞兒了!”由于過度的勞累,又不懂科學的發聲方法,他的聲音漸漸沙啞了。有一次,他吐口白沫帶有血跡,他卻若無其事地笑著說:話過千言不損自傷嘛!干咱這行,要學驚人藝,須下苦功夫啊!
常寶堃有一把白折扇,一面的上邊是三十個段子,下面是十五個段子,另一面也是如此,兩面一共是九十個節目。他到了電臺,跟那的人說,這上面的節目我們全會,你們排吧。就這樣,有的時候仨月都可以不重復。著名評書藝人連闊如三十年代寫作《江湖叢談》里面說到:最近我在北平常聽見天津廣播電臺播來的各種雜技,最可聽的玩意兒是常連安、小蘑菇的相聲,一捧一逗,對口相聲,又火熾又嚴,甚為精彩。1935年,勝利唱片公司為他錄制了相聲唱片《小孩語》,這一年他剛十三歲。這么小年齡灌制相聲唱片,可以說是前無古人,至今也后無來者。
1936年,在張壽臣的建議下,常連安不再給常寶堃捧哏,換趙佩茹為搭檔,趙佩如捧逗皆精,以功底深厚、活絡寬闊、用字準確、細致入微而聞名于相聲界。趙佩茹比常寶堃大八歲,是一對特殊、火爆的搭檔,逗中有捧,捧中有逗,這是二人特殊的關系造成的。有的相聲常寶堃說,趙佩茹捧。有的相聲調個兒,趙佩茹說,常寶堃捧。從此,小蘑菇常寶堃和趙佩茹珠聯璧合,常寶堃機敏灑脫,趙佩茹左右逢源,兩人表演起來旗鼓相當、嚴絲合縫,創造了一種緊湊、熾熱、明快、引人入勝的藝術風格。
在1936年11月8日的天津《益世報》上登載著這樣一則廣告,按照當時演員的排名規則,一號演員的名字登在中間,二三號演員的字號稍小,分別登在一號演員的右側和左側,其他演員依次類推。排名的前后不僅標志著演員的聲譽和地位,而且決定著演員的收入。從那天的廣告來看,那場演出的一號演員是京韻大鼓藝人小彩舞駱玉笙,二三號演員則分別是當時最紅的相聲藝人張壽臣和他年僅十四歲的徒弟小蘑菇常寶堃。endprint
對于小蘑菇名氣的日益上升,師傅張壽臣感到喜悅和欣慰,他把如今名聲大震的徒弟常寶堃稱作是自己的名徒,而小蘑菇自己也始終保持自己謙虛好學的精神。一次,相聲藝人侯一塵在《天聲報》上公開批評小蘑菇的某些表演有低趣之處,常寶堃見報后馬上誠懇接受,并在報上做了回復:今蒙各方愛護以誠,出以不客氣之指教,非常感激。此后,決遵諸公意旨,向上努力,決向藝術進一新境,方不負輿論諸公諄諄愛護之至意。
那時候,他雖然不曾認識到相聲必須改革、創新,但卻懂得迎合“潮流”,這“潮流”里邊就包括了人民群眾的需要。有一次他演出之后,在回家的路上遇見一個乞丐在商店門前敲著牛棒子骨唱數來寶。他停了步,聚精會神地聽著。隨后,他把這個唱數來寶的讓到家一起吃飯,說要和他交個朋友,約好時間請他每天到家來即興唱幾段數來寶。唱數來寶時,他是那樣入神地聽啊、學啊!他送給這個唱數來寶的一些衣服和錢,真的成了好朋友。過后我才知道,這是他編演相聲《改良數來寶》的生活來源。《改良數來寶》曾錄制了唱片,一直保留到今天。
違行規與育新人
常寶堃收蘇文茂為徒,是首次打破自相聲傳承以來所遵循的“師徒合同”中的一些約定。
蘇文茂,生于北京,滿族鑲藍旗人,祖上享受世襲官位。在蘇文茂父親那一代,家道開始沒落。父親去世后,他與母親相依為命。因家境貧寒,十二歲的蘇文茂只身來到天津,在一家名為“久春堂”的藥鋪學徒。蘇文茂很喜歡聽常寶堃、趙佩茹的相聲,日久成迷,主動要求拜常寶堃為師。他常利用閑暇時間到常寶堃的兄弟劇團所在的慶云戲院去幫忙,與演員們一起裝臺、搬道具,而且細心地學習老演員們的表演。他的嗜學精神感動了常寶堃,一九四四年,十五歲的蘇文茂在天津南市“泰華樓”正式拜常寶堃為師,掀開了他藝術生涯新的一頁。
常寶堃收徒,按行規應簽訂“師徒契約”。今日看來,拜師還要訂合同,似乎笑話。然而,在過去是必須要簽訂的。如果用今日的眼光來看,過去的“拜師契約”一定會被叫做“霸王條款”。為何?因為在整張“契約”中,只有“師父管徒弟的吃住”(有的徒弟不住師父家,例外)這一條,是站在徒弟一邊的。至于其它方面,維護的全部是師父的利益。比如:學徒期間,徒弟生死患病,投河覓井,概與師父無關;學徒期間,師父可以任意使喚徒弟,進行日常家務勞動等等。
蘇文茂是在1943年拜師常寶堃的,契約要訂,但常寶堃毅然決然地要對老祖宗留下的“師徒契約”進行改革,他果斷地提出,舊契約中“生死患病,投河覓井,打死勿論”一類的詞語,絕不能寫進合同。之前,幾乎所有的合同都有這樣的詞語。常寶堃卻不讓寫進這些,這是相聲藝人的覺悟表現。
相聲行業有按“字”排輩的習俗,也可以說是“規定”。排字從第四代藝人開始,用的是“德”字,下一代藝人排“壽”字,再下一代排“立”字,如張壽臣的徒弟馮立樟、康立本、葉立中、田立禾等。可是這一代藝人,因為常寶堃(藝名常立桐)社會影響極大,故許多藝人用了他的“寶”字,如侯寶林、趙寶琛(即趙佩茹)、孫寶才(藝名“大狗熊”,趙藹如的徒弟)等。
“立”或“寶”字輩的下一代是“仁”字,蘇文茂拜師,是謝芮芝(謝派單弦的創始人,也說相聲,是謝天順的祖父)給起的藝名:蘇伯光。而不久,他的師爺張壽臣認為“伯”字不妥,再給他起藝名:蘇仲仁。這樣,加上”蘇文茂“,他就有了三個名字。到底該用哪個?常寶堃非常開明,他讓徒弟自己定。為了讓在北京的母親方便找他,蘇文茂上舞臺就沒有用藝名,用的仍是原名。然而,“蘇文茂”這個名字響了,于是,他這一代演員就用“文”字了,如楊少奎有十一個徒弟用了“文”字做藝名。
常寶堃視徒如子,不讓蘇文茂在自己家中做家務,要求他多到劇場看別人的表演,可是,他又怕蘇文茂在自己家吃飯時間沒保證,所以每天給他兩元錢,讓他在外邊吃好。蘇文茂演出有了收入以后,按行規,徒弟學藝期間,其收入歸師父。而蘇文茂在學藝期間的演出收入,師父讓他自己支配。
與一些藝人相比,蘇文茂“出道”較晚。14歲開始演出,也算是“大器晚成”。可是他剛一“出道”,就“小荷初露尖尖角”,藝術天賦加上刻苦,讓眾多的前輩喜歡他,認定他是說相聲的一塊“好料兒”。蘇文茂出師,按“師徒契約”,應孝敬師父一年,即在這一年內所有的演出收入全部歸師父。這時,常寶堃又宣布取消“孝敬一年”的規定。
常寶堃的屢屢“違規”,感動著蘇文茂,蘇文茂也沒有辜負師父的期望。他既繼承了師父常寶堃的精湛演技,又繼承了師父高貴的人品。
黑暗中遍嘗屈辱
盡管常寶堃從小就上舞臺,可是相聲藝人們在政治上絲毫擺脫不了低下的地位。小的時候,常寶堃跟著父親出入深宅大院、高樓廣廈,為有錢有勢的人們走堂會演出,常常遇到叼著雪茄煙的老爺、闊少們用煙頭在他光頭上燃燙取樂。剝削和凌辱,在常寶堃幼小的心靈上深深地刻上了烙印。對于這一切,他雖然怒在心里,可是為了糊口,還得忍氣吞聲,笑在臉上。
常寶堃成長在勞苦大眾之中,他愛勞動人民之所愛,恨勞動人民之所恨。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因為編演的相聲節目觸犯了日寇、漢奸、偽警察,給他帶來了不幸的遭遇,曾經兩次被捕,一次遭受毒打。
他第一次被捕,是在日本投降前夕,大約是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之間。這時候日寇為了強化侵略戰爭,強迫老百姓獻鐵獻銅。當時他演了一段傳統相聲《耍猴兒》。在這個節目里,他加上一段現掛的詞句。因為耍猴要敲鑼,他向捧哏的說:“咱倆耍猴兒的話,我得用嘴模仿鑼的聲音了。”捧哏的問:“你的鑼呢?”他說:“我的鑼獻了銅了。”這一來可捅了馬蜂窩,第二天,他就被敵偽警察局扣留了。第二次被捕,在這之后不久,是因為演出了諷刺敵占區物價飛漲的相聲《牙粉袋兒》。這個段子是他弟弟常寶霖寫的,在北京演過。常寶堃知道了這個段子,他要了來加以充實修改,在天津慶云戲院又演了。相聲里說的是隨著日本鬼子搞的一次又一次“強化治安”,每袋洋面一次比一次落錢,不過袋兒也很小,也就跟牙粉袋似的。由于這個段子狠狠地打中了敵偽的要害,他下場后,又一次被抓走。又有一次,他針對偽警察敲詐勒索老百姓的罪行,自己創作了一段相聲《打橋票》。在當時演的時候,效果相當好,因為說出了人們的心里話。“打橋票”是什么意思呢?橋指的是天津的解放橋,因為是在法租界里,當時叫法國橋。橋上有幾個警察輪流站崗,凡是過這個橋的人,都得給他們送點錢或者東西。不然的話,你是過不去這橋的。這段相聲演出后,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和喜愛。那些偽警察知道了,便約了一幫人張牙舞爪地跑到劇場尋釁鬧事。進了門就叫:“小蘑菇,聽說你有個新節目啊,給我們演演!”跟他們怎么說也不依不饒,非聽《打橋票》不可。這幾個警察坐在離舞臺二、三米遠的包廂里,說這段相聲的當中,其中一個愣把茶壺飛上舞臺。接著幾個警察都上了臺,把常寶堃拉到后臺毒打了一頓,又給他定一條規矩:他只要通過這個橋,就得給這幾個警察鞠躬,不是讓他道歉一次,而是要他永遠道歉。這件事更激發起常寶堃對侵略者及其幫兇的刻骨仇恨。endprint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常寶堃也曾寫過一些比較好的相聲段子。譬如上邊提到的《改良數來寶》,就是諷刺有錢有勢的人如何揮霍奢侈,同勞動人民饑寒交迫的生活形成鮮明的對比。當時國民黨也曾侈談什么“文藝改革”,還曾經威脅利誘他編演諷刺共產黨、八路軍的節目。寶堃斬釘截鐵地回答:“我編不出來。”
為國灑熱血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此時,已是名滿津門的相聲藝人小蘑菇常寶堃正帶領著因為戰事緊張,劇場關閉而失去演出場所的藝人們在海河邊上開臨時地攤。滿大街慶祝解放的歡快氣氛感染著他,他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正在來臨。
1949年4月,天津軍管會文藝處召開梨園界座談會,剛剛二十七歲的常寶堃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成立“改革舊制委員會”。為了盡快地接受革命理論,常寶堃還參加了軍管會文藝處舉辦的講習班。1949年7月2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八百二十四名不同風格流派的新文藝界與舊文藝界的代表相聚在一起,小蘑菇常寶堃作為天津曲藝界的代表也參加了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小蘑菇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國家領導人,作為一個曾經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藝人,他十分激動,從此,他的創作熱情被激發起來。他還認為,凡是黨號召的事,他都積極響應。
參加第一次文代會后,他常常思考今后怎么辦。過后,從他的工作實踐中,人們看到了答案。他在相聲藝術上更加自覺地、勤奮地探索創新、改革的道路。他幼年失學,寫字困難,便刻苦學習文化,克服一切困難,堅持編演新節目。他根據傳統相聲《打燈謎》改編的《新燈謎》,熱情地歌頌了工農兵學商新的生活和精神面貌,生動地表達出他在新社會的親身體驗和深切感受。
他把一些傳統相聲的節目積極進行新的改編,比如說他把傳統節目《婚姻與迷信》融入新的內容。解放之初,男尊女卑的思想還很嚴重,婦女沒有地位,辦喜事用的詞都不一樣,像“弄璋之喜”、“弄瓦之喜”,這些東西,在新的節目中都被拿掉。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開始。為了慰問志愿軍將士,第一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總團曲藝服務大隊在北京組成。消息傳到天津后,常寶堃、趙佩茹等人提出申請,希望能參加赴朝慰問團。他報名時說:抗美援朝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我們人人有責任,我雖然不是拿槍的戰士,但是我可以用相聲去慰問我們最可愛的人,也是間接打擊美帝國主義嘛!就在這一年,他們二位加入了第一屆赴朝慰問團并組織曲藝分隊,常寶堃任隊長。在朝鮮的演出,大部分是在樹林子里進行的,也經常和美軍的飛機遭遇,一看見飛機扔照明彈,演出就停止了,首長就讓慰問團趕快休息,以保證慰問團的安全。后來常寶堃發現,慰問團的成員躲避起來了,戰士們怎么不動呢?經詢問部隊首長,才得知是因為戰士們有經驗了,知道上面的飛機看不到他們,一會就飛走了。常寶堃就跟部隊首長說,飛機看不到戰士,我們在那里演出不也是看不見嗎?戰士們不動,我們也能不動。演。戰士們當然歡迎了,熱烈鼓掌歡迎,這時候常寶堃就使了個現掛,說咱們得感謝老美,天黑了,知道大家看不清楚,一指天上,那個照明彈,給咱們安了幾個臨時電燈。這樣一個包袱,把緊張氣氛一掃而盡。
1951年4月23日,赴朝慰問團已經勝利完成了任務,踏上返回祖國的歸程。中午,慰問團在三八線附近的沙里院休息,突然遭到四架美國飛機的襲擊。常寶堃擔心大家的安全,就站起來喊道:誰都不要出去,別暴露目標!話音未落,敵機就開始掃射,隨著“轟轟”巨響,房子里充滿了濃煙和焦臭,屋頂上的茅草也燒了起來。過了好一會兒,與常寶堃同在一個屋內的趙佩茹從昏迷中蘇醒過來,此時濃煙已經消散,只有屋頂上著火的茅草還在一團團地往下掉,他不顧自己胳膊上的傷痛,一邊爬一邊喊著常寶堃的名字。先看到了已經犧牲的天津著名琴師程樹棠,隨后,他在門旁發現了常寶堃,但他頭上中彈,已經停止了呼吸。這位相聲表演藝術家剛剛29歲,就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1951年5月12日,常寶堃和程樹棠兩位烈士的靈柩被護送到天津。5月15日,在馬場道第一公墓殯儀館舉行公祭,那天一大早,靈堂外面就人山人海,人們佩戴著黑紗,爭先恐后地瞻仰烈士遺容。5月18日,舉行了隆重的送葬儀式。幾十萬天津老百姓自發的扶老攜幼走上街頭,送他們心目中可親可敬、為國捐軀的相聲大師最后一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