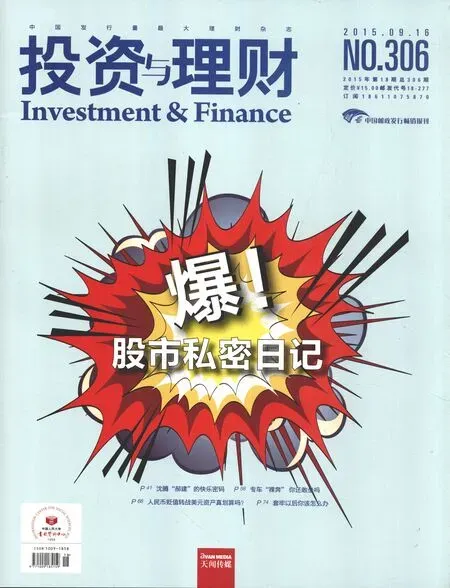碎念之火
任海丁
這幾年,王煜的創(chuàng)作開始和現(xiàn)今復(fù)雜的思想——意識場域做搭接,似乎他想要清理之前感性的某種混沌,而把自己藝術(shù)的現(xiàn)實能動性和話語銳度強(qiáng)化出來。他的藝術(shù)關(guān)鍵詞——在他的寫作中——有兩個可能比較重要:一個是碎念,一個是作為事件(的水墨)。
關(guān)于碎念,王煜這樣寫道:“世界是片斷的集合,是瑣碎的象征??片斷式的集合方式,呈現(xiàn)某種斷裂的表征。斬斷畫面故事與意義線性時間的流動,在此刻,時間結(jié)構(gòu)不斷被拆解,作為時間的碎片存留著,猶如鏡頭的閃回,無因果、無中心、感知殘留,在片斷與片斷間的裂縫間隙浮現(xiàn)意義。”而作為事件(的水墨),則是:“現(xiàn)實感瞬間被突發(fā)事件切斷和阻隔,作為常規(guī)的例外出現(xiàn),其恰恰撕開了生活表面,而顯現(xiàn)其真實的一面,并賦予藝術(shù)的形式。特別是以水墨的表現(xiàn)載體揭示出來,顯示了作為古老畫種的當(dāng)代發(fā)生??正是水墨本身的矛盾地被觀看與探討,同時水墨本身又具備歷史的證明與今天的缺憾的糾結(jié),恰好能夠勝任為其自主性建立的突破口。作為‘事件’的水墨,打碎了線性的現(xiàn)實本身,在間隙中顯示自主的獨立,重構(gòu)瑣碎的現(xiàn)實,使之成為水墨的自主化,進(jìn)一步確立藝術(shù)的主體性。”
以我看,碎念的意思,除字表義外,應(yīng)該是指某種無法整體一貫的生命經(jīng)驗,不得不作為一個集合,被納入主體認(rèn)知的情態(tài)——因為生命體必須指認(rèn)一個精神的全形結(jié)構(gòu)(如同每個人不可更易的獨個身體),來完成自我的存在形象。在這個集合中,主體意識事實上是一種各為其是的乃至于矛盾的、分裂的碎片樣態(tài)。毫無疑問,這就是現(xiàn)代性語境下的主體意識失敗的某種描述。而所謂“事件”,王煜是借用了巴迪歐(Alain Badiou)的概念。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巴迪歐所言的“事件”,是艱難抵達(dá)“計數(shù)為一”的真理程序——事件是偶然的、凸出的,它本身沖決、威脅真理相關(guān)的種種律法和秩序,但真理偏偏又在事件造成的開裂危機(jī)中普遍發(fā)生出來。我相信,巴迪歐關(guān)于事件-真理的主體思想啟示,也許給了王煜某種堅定的藝術(shù)思路。我甚至認(rèn)為——或者寧愿這樣認(rèn)為,王煜這一時段的藝術(shù)呈現(xiàn),就是試圖借用碎念與事件兩個詞連接所產(chǎn)生的語義場,以水墨繪畫的方式作為表征,來對抗現(xiàn)代主體意識的失敗以及水墨的藝術(shù)衰落。
這一時段王煜的創(chuàng)作,諸如《純粹的表征》系列(2013)、《碎念》系列(2013-2014)、《美麗背后》系列(2013-2014)等,從畫面主題和敘事上來看,大都是主體經(jīng)驗的迷局——個體存在深度與經(jīng)驗深度的自我尋找和模塑。這足以說明他相當(dāng)敏感于現(xiàn)代主體意識的失敗。就像他碎念的描述,我們今日已經(jīng)無法確知什么是永恒、什么是須臾,什么是真實、什么是虛假。經(jīng)驗之為經(jīng)驗,已經(jīng)不能給予自身有效的證明與保障了:只能在一念之“片斷與片斷間的裂縫間隙”中,把握“浮現(xiàn)意義”的契機(jī)。但在王煜這里,這一念之機(jī)立刻被賦予了巴迪歐所言事件的性質(zhì)——“片斷與片斷間的裂縫”就是事件的偶然凸出之象,從而鼓舞了真理程序的啟動。對于巴迪歐,事件是一種激進(jìn)的挑戰(zhàn),是真理完成自身的一次必經(jīng)。巴迪歐斷言:“獨特的真理都根源于一次事件??甚至在我們的個人生活里,也必須有一次相遇,必然沒有經(jīng)過深思熟慮、不可預(yù)見或難以控制的事情的發(fā)生,必然有僅僅是偶然的突破。”無關(guān)評價,這的確是一種兩刃相交“劫毀-生生”的激烈思想,王煜卻把它借用到了對現(xiàn)代主體意識的“自主”藝術(shù)拯救中。必須賦予碎念之信,作為一個楔子,楔入主體意識的碎片廢墟,去尋找、發(fā)現(xiàn)乃至構(gòu)造出包孕未來主體的可能。對王煜來說,這個楔子,就是畫面上水墨即時發(fā)生的“例外”:每個貌似毀壞水墨常規(guī)的瞬間——繼而,他把這個瞬間作為水墨的事件展現(xiàn)出來。比如,在《美麗背后》之四(2013)的畫面上,無論是形象的描繪和水墨呈現(xiàn),都和一個尋常的“速寫”很相似,而有意無意地,他在人物的旁邊注上了搶眼的英文名字,注明這個被草率勾畫出來的形象,是著名的政治家昂山素季。形象和水墨呈現(xiàn)的雙重的潦草,既造成了一個公眾人物的被如何認(rèn)知的事件,也造成了一個水墨的表達(dá)事件:一是,提示現(xiàn)代公眾人物的形象,是在社會網(wǎng)絡(luò)諸種作用下的關(guān)系存在,不打斷這種關(guān)系注視,主體意識就是無能的;二是,不具備審美返祖意識的水墨呈現(xiàn),使水墨之為水墨的當(dāng)代存在問題益發(fā)緊迫起來。
這里應(yīng)該說,這一碎念之信的藝術(shù)愿景,發(fā)生在水墨繪畫場域,意義尤為特殊。眾所周知,水墨繪畫今天仍然作為體制化的穩(wěn)固知識系統(tǒng)被看待,人們認(rèn)為,水墨只要保持與自身歷史的象征性的聯(lián)系,就會擁有傳統(tǒng)綿延的神圣性。但是請記住阿多諾的提醒:“倘若綿延過于有意而為,倘若它利用純粹堅不可摧的形式或普遍的人類價值觀這樣不可捉摸的東西,以驅(qū)除被認(rèn)為是短命的東西,那么它就是與自個過不去,從而縮短了而不是延長了作品的生命力。對綿延的錯誤理解會使其仿效概念性,這對不同的內(nèi)容來講,是一個永恒的圓周或外殼,渴望取得某種靜態(tài)的永久之物。所有這一切與藝術(shù)作品的張力特性是不相容的。這便是它們?yōu)槭裁聪龅迷娇欤炊较胫苯拥孬@得綿延的原因。形式概念意味著綿延,但綿延對該概念來講并非本質(zhì)性的。處于危險境地、似乎輕率地冒毀滅之險的作品,與那些為了安全起見的顯赫一時的作品相比,更有機(jī)會幸存下來。古典主義的禍根在于持續(xù)不斷地產(chǎn)生一種空洞的藝術(shù),因此而告衰落。”
盡管有時在藝術(shù)表現(xiàn)上,王煜的部分作品可能并不算完全成功——但這正是現(xiàn)代個體經(jīng)驗的應(yīng)有征候:現(xiàn)代經(jīng)驗個體想要如實地再現(xiàn)自身,也是困難重重的。2012年,王煜畫了一幅名為《本雅明的火焰》的畫,畫面信息復(fù)雜。我問他,他說,是一種亂象吧。回答出奇的簡單。但我想他肯定知道本雅明的這個比喻:作品是燃燒的柴堆,火焰本身才是作品的秘密——要向著火焰而不是去到灰燼里發(fā)現(xiàn)和尋找。王煜的藝術(shù)目的也許是,抓住碎念那點飄忽不定的星芒,為的是點燃主體意識的自主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