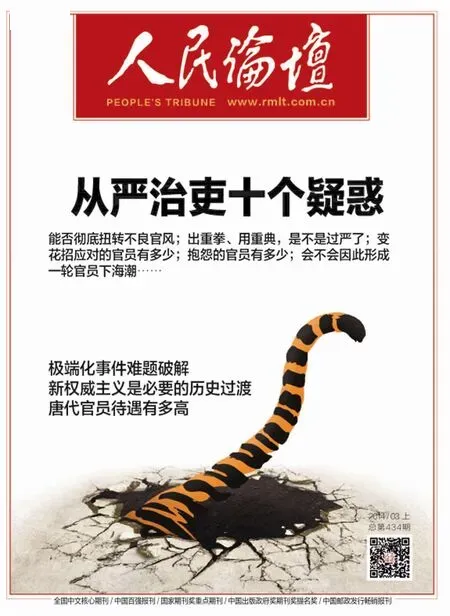反腐制度設計要給人以合理期待
——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人民論壇記者 袁 靜
反腐制度設計要給人以合理期待
——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人民論壇記者 袁 靜
中國的腐敗不僅僅是官場現象,整個社會都存在著,反腐敗一定要現實,法律政策都要現實
人民論壇:您如何看待近一年多來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高壓反腐、從嚴治吏,出重拳、用重典的舉措?
鄭永年:官員越腐敗,執政合法性就會越低。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周期率也跟腐敗密切相關,所以反腐敗確實十分重要。但是要反腐敗,首先必須分層進行。該不該反?這就要看你的目標是什么,然后一層一層來。全面反腐敗很重要,但現實不可能,“蒼蠅”、“老虎”哪能抓得完?更重要的是,在中國“蒼蠅”、“老虎”具體是如何規定的?目前看來對此還沒有明確的界限。當前腐敗立案的規定,例如一些法律法規和政策性的東西,很多都已不大適應時代的發展。比如1988年規定構成貪污罪、賄賂罪的數額一般為2000元;1997年通過的刑法規定,貪污賄賂犯罪的起刑點是5000元,這一規定一直沿用至今。但是中國是人情社會,老百姓之間送禮如今超過這一標準已屬正常。就此看來,中國的腐敗不僅僅是官場現象,整個社會都存在著。尤其在基層的腐敗中,很多人可能已經把它當成工作中一種常態化的存在。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可能干不了什么事情。所以反腐一定要現實,法律政策都要現實,太理想化,反腐敗轉化不成制度優勢。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有那么多反腐敗條規,如果任何一條都適用,或許就沒有人不腐敗了。腐敗也就沒法反了。反了那么多誰給你干活?我最近幾次去中國的幾個地方調研,接觸的很多地方官員都很擔心,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哪一天會被“提溜”起來。
反腐敗的第一要義不僅僅要反腐敗,而要換一個思路,給清廉人一個機會
人民論壇:在近期我們所做的“官風整治十大疑惑”的調查中,不少受訪者反映,此次官風整治與之前有很大不同。總體來看,給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鄭永年:事實上,反腐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負面”來說的政治行為,也就是你做錯了事情,就應受到懲罰。“正面”的政治行為還是鼓勵你去做事情。這個“做事情”一定要肯定,因為如果沒人給你干活了,會更麻煩。你要知道,腐敗是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制度不健全,才會有好多人去腐敗,形成不腐敗便沒法生存的局面。所以要實行“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這方面我提了很多年了,也公開發表文章討論過。反腐敗的第一要義不僅僅要反腐敗,更需要換一個思路,給清廉人一個機會。如果清廉人的機會都沒有,不腐敗就沒法工作,就要“出局”,不能腐不敢腐的機制建設就是一句空話。從這一點來看,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提法就很好,包括禁止提拔裸官的規定,就是要給新任的人一個清廉的機會。
觀點摘要
●制度的建立首先就要給人一個合理的期待,才能使之制度化。如果對人不合理,要求人人沒有自己的利益,全部大公無私,那就沒法制度化,就不需要制度了
●依靠黨內反腐敗,必須界限清晰。反腐敗的目標不僅僅是要把腐敗官員清除出來,而且要干部干活好、好干活,把改革推向前去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教育給民眾過高的期待,官員被當成道德的化身,可以不吃不喝,民眾發現實際上并不是這樣,當然會有情緒。人都是有自己利益的,沒有利益就不會負責任
反腐敗不是目的,清廉政府才是目的。地方官員更擔心的其實是怎樣改革、怎樣解決問題
人民論壇:您剛剛提到很多地方官員很擔心會反到自己頭上,是不是意味著對中央高壓反腐,他們主要在采取一種觀望態度,等待著這陣風過去?
鄭永年:我覺得這不是觀望的問題,這種現象確實很普遍。關鍵是你怎么反的問題。首先要明確的是反腐敗本身不是目的,反腐敗只是一個手段、一個構建新制度的手段,這點非常重要。現在反腐敗大家都很贊同,但要是一直沒有新制度的建設,反而可能會演變成為一種政治上的惡斗,大家互相掌握競爭對手腐敗情況,我揭露你、你揭露我。
事實上,很多地方官員更擔心的是怎樣改革、怎樣解決問題。改革難就難在要觸動自我的利益,讓官員自己損害自己的利益,不大可能。這也是為什么現在規定紀檢部門下管一級,省的由中央來管理,市的由省來管。因為自己不會砍自己的手,只有讓別人來砍。反腐敗也不會是自我來反的。這進一步說明制度設計很重要,關鍵在于如何在反腐敗的基礎上使政府清廉起來——建設清廉政府才是反腐敗的目的。因為抓人是很容易的,而防止新人不腐敗則很難。現在這個階段主要是把腐敗分子挖出來,這其實并不是最難的。怎樣預防腐敗,才是更重要的。
制度的設計必須基于一個合理的區間,給人以合理的期待。如果人人都大公無私,就不需要制度了
人民論壇:調查中我們發現也有少部分的干部和公眾認為反“四風”過嚴了,分別為22.77%和7.75%,對此您怎么看?
鄭永年:任何事情走過頭了,就可能會物極必反。反“四風”也好、反腐敗也好,反得過頭了,可能回過頭來會貪得更厲害。反“四風”,問題不在于嚴格,而在于如何執行。現在大家支持度很高,可能是因為前面很多年貪得比較多,對一些官員來說,“減減肥”也好。總體來說,制度的設計一定要有一個合理的區間。人都是普通人,干部是普通人,公務員也是。一點自私自利都沒有,什么好處都不要,怎么可能?當然,這里說的是合理合法的范圍內的好處。共產黨人不是特殊材料,對共產黨干部的要求遠遠超出對常人的要求,那樣會更麻煩。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教育給民眾過高的期待,加上中國傳統中,幾千年來官員始終被當成道德的化身,可以不吃不喝、什么都可以犧牲,這樣就給了民眾一種錯誤的期待。現在老百姓為什么情緒很大?就是因為長期以來的教育就是共產黨都是好樣的,最后老百姓發現實際上并不是這樣,當然會有情緒。人都是有自己利益的,沒有利益就不會負責任,有利益才會負責任。制度的建立首先就要給人一個合理的期待,才能使之制度化。如果對人的期待不合理,要求人人沒有自己的利益,全部大公無私,那就沒法制度化,更加不需要制度了。
我是比較同情很多普通官員的。在中國,普通官員往往都是一線政府、一線官員,縣鄉一級尤其如此。中國財權比較集中,錢都在中央政府手中,市政都叫基層去做。但錢從哪里來?基層官員工資上不去,政府規模又這么大,行政體制改革要如何進行?如果反腐敗又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也沒有明確的界限,那么大家自然都會擔心自己明天會不會就被抓起來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很積極推動改革,可是目前看不到地方太多的動力,很多官員可能都在觀望、等待,老百姓也一樣。
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不能理想化,必須理性,理性就是實事求是地探索該怎么走,而理想就是這個不對、那個不對
人民論壇:據我們調查,中央從嚴治吏后不少企業家擔心官員“不收錢也不辦事”了,您覺得從嚴治吏會不會影響經濟發展?
鄭永年:政府和企業的關系不能理想化。舉例來說,早期的日本也好,后來的亞洲“四小龍”也好,政府與企業都是有關系的。因為這些國家或地區都是后發型的,在發展過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作用也比較大。像日本和韓國,雖然不像中國這樣有國有企業,但政府資助民營企業,也是一樣的。政府把企業養大了,企業越來越有它的自主權,該如何轉型?“政企分開”不可能百分之百實現,畢竟對于地方政府來說,這個企業是我資助成長起來的,向它要點錢也是理所當然;而對于企業而言,政府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相當于“父親”的角色。怎么可能完全分開?
對這類問題,一些人往往缺乏理性的態度,太多的理想、太少的理性。理性是什么?就是實事求是地探索該怎么走。而理想就是這個不對、那個不對。在對待反腐敗問題上也是同樣,社會常常以理想化、道德化的方式要求官員,政府也好、左派右派也好,每一個人現在都在搶占道德制高點。每一個人把自己道德化了,似乎就沒什么大問題了。這個邏輯就跟宗教極端主義類似,它也是把自己道德化了,于是懲罰的對象都是異教徒。中國這么大的社會,各種利益之間互相競爭、互相叫罵,就是從不交流。到哪個地方看都能發現有人在罵、到處充滿恨:孔子有人罵,毛澤東有人罵,國民黨有人罵,美國的自由女神像也有人罵。對于現在的中國來說,有很多沒有解決的問題,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看到國家有好多東西沒有做好,就會變得激進。比如以前兩口子一起努力就可以買個小房子,現在房價那么高,再怎么努力也達不到這個最低限度,這樣人就會變得激進起來。而當每一個個體激進化之后,整個社會就會激進化。所以對于媒體來說,最重要的就是灌輸理性精神。
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并未表明動力來自頂層。反腐敗最終是為了推進改革,對目標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人民論壇:您覺得如何才能使從嚴治吏制度化?這種制度化的動力又是從何而來?
鄭永年:中國和其他國家不一樣,反腐敗是為了推進改革。對于那些不愿意改革的官員,可以把他調動到其他地方,同樣級別也好,升一級也可以,甚至直接把腐敗且不想改革的官員抓起來也行。這也是共產黨的一種方法,尤其是在國企。如此,改革的動力從何而來?我們說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并未表明動力來自頂層。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央組織宣講團去推動改革,我看成效有限。回顧改革開放初期,中央還沒有動作起來,老百姓就已經動起來了。安徽的家庭聯產承包制也好、民營化改革也好,都是如此。反腐敗也是同樣,我們知道在中國的體制下,往往能干的人也容易是腐敗的。所以,決策者一定要目標清晰、態度理性。尤其是依靠黨內反腐敗,必須界限清晰。首先務必要明確,反腐敗的目標不僅僅是要把腐敗官員清除出來,而且要干部干活好、好干活,把改革推向前去。
現在更重要的可能是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問題。在我看來,如今的中國已經得了改革疲乏癥。哪怕政府做了很好的事、真的是要改革,老百姓還是可能不信任你。而老百姓一旦不信任你,你就一點優勢也沒有了。這也是為什么說弄清楚為何反腐敗如此重要。反腐敗可以贏得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但還是那句話,反腐敗本身不是目的。改革只能是依靠找突破口,在中國就叫“綱舉目張”,而首先就是必須找到綱在哪里。
責編/劉建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