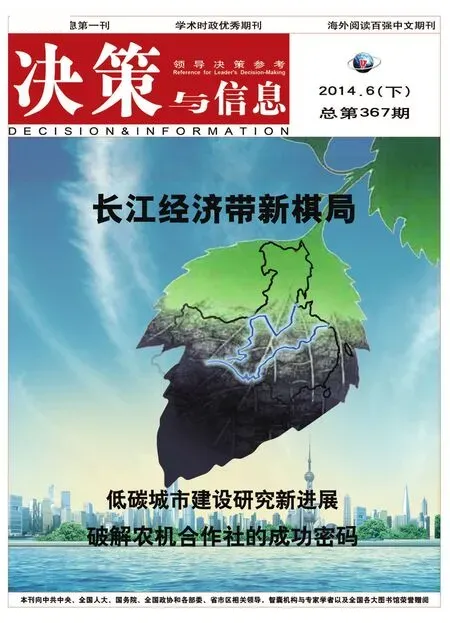亞信會議:從會議到組織還有多遠(yuǎn)?
劉恒章
中國政法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
亞信會議:從會議到組織還有多遠(yuǎn)?
劉恒章
中國政法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
2014年5月20日在上海舉行的第四次亞信峰會,把亞洲相互協(xié)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會議”)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自1992年亞信會議舉行以來,它的組織化程度與當(dāng)初建立者把它建成亞洲的地區(qū)組織這一目的是相距甚遠(yuǎn)的,究竟是哪些原因?qū)е铝诉@樣的局面,對于作為輪值主席國的中國來說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促進(jìn)亞信會議的組織化進(jìn)程,本文將做淺析。
一、亞信會議的由來
冷戰(zhàn)結(jié)束后蘇聯(lián)解體導(dǎo)致的地區(qū)安全問題凸顯是亞信會議形成的主要原因。蘇聯(lián)分裂成為15個(gè)國家,原先北約華約兩極對峙格局掩蓋下的許多沖突時(shí)有發(fā)生,例如民族矛盾、領(lǐng)土糾紛等。與此同時(shí),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如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問題十分嚴(yán)重。這些復(fù)雜的地區(qū)安全隱患以及全球格局,促使政治家們思考如何推動新型國際安全觀的形成、重建地區(qū)及世界安全信任體系。
通過地區(qū)合作以解決地區(qū)安全問題、促進(jìn)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是冷戰(zhàn)后各地區(qū)采取的措施。比如歐洲有歐洲共同體,但當(dāng)時(shí)的亞洲沒有類似的組織。雖然有亞洲有東盟等區(qū)域性的組織,但這幾個(gè)區(qū)域性的合作組織各自所代表的僅僅只是亞洲的一部分。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哈薩克斯坦總統(tǒng)納扎爾巴耶夫考慮效仿歐安組織,在亞洲也建立這樣一個(gè)能夠代表整個(gè)亞洲、以安全為重點(diǎn)的論壇機(jī)制形式。隨后,在1992年第47屆聯(lián)合國大會上,納扎爾巴耶夫又正式提出了關(guān)于建立亞信會議的倡議,這也被人們視為亞信會議的“誕生”。
二、亞信會議的組織化成果
目前對于國際組織的構(gòu)成要素,國內(nèi)外學(xué)者有不同的觀點(diǎn),但對于國際組織的主要構(gòu)成要素是一致的。一般來說,國際組織有著這樣幾方面的特征,包括多國性、工具性、非營利性、制度化和一定的獨(dú)立性。亞信會議符合多國性、工具性和非營利性特征是很明顯的。但是對于制度化,國際組織和臨時(shí)性的多邊國際會議是不同的,它要實(shí)現(xiàn)組織成員所議定的職責(zé)就必須建立一系列能夠承擔(dān)持續(xù)職責(zé)的常設(shè)機(jī)構(gòu)。一般的常設(shè)機(jī)構(gòu)包括最高機(jī)構(gòu)、執(zhí)行與主管機(jī)構(gòu)和行政管理結(jié)構(gòu)。但是對于亞信會議而言,常設(shè)機(jī)構(gòu)目前只有2006年設(shè)置的秘書處,主要負(fù)責(zé)貫徹執(zhí)行與亞信會議宗旨原則相適應(yīng)的政策職能。既然亞信會議沒有一套成熟的常設(shè)機(jī)構(gòu),就更不用提它在國際舞臺上的獨(dú)立性了。
三、阻礙亞信會議組織化進(jìn)程的原因
1.亞信會議內(nèi)部成員國數(shù)量眾多。從亞信會議建立到現(xiàn)在,其擁有24個(gè)成員國,包括中國、阿富汗、阿塞拜疆、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土耳其、烏茲別克斯坦、泰國、韓國、約旦、阿聯(lián)酋、越南、伊拉克、巴林和柬埔寨。還有13個(gè)觀察員,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美國、卡塔爾、烏克蘭、日本、孟加拉國、菲律賓、斯里蘭卡,以及聯(lián)合國、歐安組織、阿拉伯國家聯(lián)盟和突厥語國家議會大會。成員數(shù)量的龐大,導(dǎo)致成員國之間利益協(xié)調(diào)難度加大。
2.亞信會議各成員國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不一。亞信會議內(nèi)部成員既包括像韓國一樣的發(fā)達(dá)國家,也包括像中國、印度一樣的發(fā)展中國家;既包括像伊拉克、蒙古一樣依靠資源出口的國家,也包括像越南依靠農(nóng)業(yè)的國家。由于各成員國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不同,所以各方的經(jīng)濟(jì)利益訴求就是差別很大,并且各方的互補(bǔ)性不是很強(qiáng),在協(xié)調(diào)各方的經(jīng)濟(jì)利益時(shí)變得尤為棘手。
3.各成員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tài)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在亞信會議內(nèi)部成員國之間存在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差異,中國作為世界上的做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它的政治制度就是社會主義;俄羅斯作為世界上領(lǐng)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它實(shí)行的就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同時(shí)在亞信會議內(nèi)部也存在著意識形態(tài)的差別,有以中國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有以基督教為信仰的國家,也有伊斯蘭教派的信仰國家。
4.部份成員間在領(lǐng)土、宗教等問題上存在著復(fù)雜的爭端,這些爭端既有歷史遺留產(chǎn)生的,也有近期顯現(xiàn)的。比如東亞和南亞的“海權(quán)競爭”迅速升溫,東亞地區(qū)因歷史原因而形成的領(lǐng)土領(lǐng)海爭端長期存在,化解困難。領(lǐng)土和海洋權(quán)益爭端涉及多個(gè)亞信會議成員。
四、促進(jìn)亞信會議組織化進(jìn)程的措施
那么,亞信會議要從會議身份轉(zhuǎn)變?yōu)橐粋€(gè)運(yùn)轉(zhuǎn)有力,富有成效的組織,我認(rèn)為需要一下幾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加強(qiáng)成員國對于共同認(rèn)可原則和規(guī)范的認(rèn)識,尤其是安全問題。創(chuàng)立之處,對于亞信會議的定位就是一個(gè)有關(guān)安全問題的多邊論壇。所以亞信最為重視的就是在安全領(lǐng)域,這就要求要有一種各方認(rèn)可的新的安全觀。這種安全觀是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協(xié)作的新安全觀,既重視本國的安全,又顧及別國合理安全關(guān)切,尊重彼此核心利益。
第二,需要成員國,尤其是大國的協(xié)力推動。亞信會議建立是為了是成員國通過多邊合作的方法促進(jìn)亞洲的和平、安全與穩(wěn)定。不能是大國戰(zhàn)略競爭的平臺。一旦如此,必然與“亞信”成立的初衷背道而馳,“亞信”的生命力也就自然消失。但是,只有大國才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公共產(chǎn)品,承擔(dān)更多的責(zé)任和義務(wù),深化彼此間合作,所以作為地區(qū)的大國必須意愿去為地區(qū)的安全穩(wěn)定做出犧牲。所以,大國可以為亞信會議的發(fā)展提供最核心的驅(qū)動力。
同時(shí),作為亞信會議成員國中的中小國家,也應(yīng)積極參與“亞信”活動,并就地區(qū)安全和發(fā)展提出更多的倡議。營造互利共贏的氛圍,不只是大國的責(zé)任,也需要中小國家積極參與進(jìn)來,形成命運(yùn)共同體意識。
第三,在亞信會議機(jī)制的形成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有步驟、分階段地選擇合作點(diǎn),由少至多,由點(diǎn)及面,逐漸實(shí)現(xiàn)在各個(gè)領(lǐng)域的協(xié)調(diào)一致。
亞信會議要發(fā)展,就不能僅停留在“信任建立”的階段,不能僅停留在建立之初的傳統(tǒng)安全領(lǐng)域,更為重要的是在傳統(tǒng)和非傳統(tǒng)安全領(lǐng)域開展具體的、務(wù)實(shí)的合作,可以通過傳統(tǒng)安全領(lǐng)域的合作帶動非傳統(tǒng)安全領(lǐng)域的合作,同時(shí)非傳統(tǒng)安全領(lǐng)域的合作促進(jìn)傳統(tǒng)安全領(lǐng)域的合作。要實(shí)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既要探索建立運(yùn)轉(zhuǎn)靈活的平臺和機(jī)制,又要有通暢、快捷的合作路徑和方法。現(xiàn)階段,在非傳統(tǒng)安全領(lǐng)域,包括災(zāi)害救助、打擊販毒、人口拐賣、反恐和能源安全等,開展合作尤為必要。
同時(shí),亞信會議要持續(xù)發(fā)展,離不開成員國在軍事、政治、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人文等廣泛領(lǐng)域的合作。通過這些領(lǐng)域的合作形成全方位、廣領(lǐng)域的合作,這樣就可以更好的促進(jìn)亞信會議的組織化進(jìn)程。
5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xí)近平在第四屆“亞信”領(lǐng)導(dǎo)人峰會主旨發(fā)言時(shí)闡述了以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及可持續(xù)安全為內(nèi)核的“亞洲安全觀”,并寫入會后發(fā)表的《亞洲相互協(xié)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第四次峰會上海宣言》。中國也正式接任2014年至2016年“亞信”主席國。在主席國中國的積極推動下,在亞信會議各成員國的努力下,亞洲互信、安全、和平、發(fā)展的前景是光明燦爛的,亞信會議會朝著組織化的方向不斷前進(jìn)。
劉恒章,中國政法大學(xué),1987.6,男,山東省鄒平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