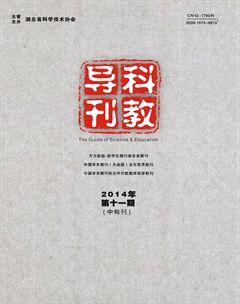具身道德:來自潔凈方面的實驗證據
陳瀟 江琦
摘 要 潔凈與道德的實驗研究促使了具身道德的發展。本文從具身道德的概念、潔凈與道德的研究出發來探討具身道德的已有實驗證據、存在的問題。在未來的研究中需要擴展具身道德的研究內容、探究具身道德研究結果的重復性與文化一致性以及采用多種研究技術等方面以進一步豐富具身道德。
關鍵詞 具身道德 身體潔凈 道德
中圖分類號:B84-09文獻標識碼:A
Embodied Morality: The Experimental Evidences from Self-cleanness
CHEN Xiao, JIANG Qi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ore the embodied morality from self-cleanness and moral studies, now the researches have some problems need to notice. Future researches need to extend the contents of embodied morality, to test the results of researches and use a variety of techniques to enrich the embodied morality.
Key words embodied morality; self cleanness; moral
1 具身道德的概念
具身道德(embodied morality)是指身體在道德認知、道德情緒和道德行為中起著重要作用,身體經驗等內容決定了個體道德心理的發展與變化。葉浩生(2010)在具身認知的分類中,明確的將潔凈與道德作為一個單獨的內容,構成具身認知與道德之間的聯系。近年來,對潔凈的相關研究進一步擴大了其內容(Schnall, Haidt, Clore, Jordan, 2008)。由此,閆書昌(2011)認為,具身道德是對身體潔凈與道德關聯性研究共同衍生構建出來的一個新的理論問題。
傳統的道德判斷機制認為,道德判斷或道德決策是由理性加工所決定的,表現為在一定道德情境中,道德推理直接導致了道德判斷的結果。認知革命后,道德判斷機制從重視理性主義轉向情緒直覺模型。道德判斷的直覺模型肯定了身體外源性所引發的具有生理意義的基本情緒的重要作用。
而具身道德觀不同于傳統道德判斷理論與社會直覺模型,它認為道德的抽象思維根植于身體潔凈這一具體的身體經驗之中(閆書昌,2011)。也就是說,身體潔凈狀態決定了個體在涉及相關道德情境時,如何進行道德認知、獲得何種道德情緒以及做出怎樣的道德行為,身體經驗由此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2 潔凈的具身道德研究及其理論解釋
2.1 潔凈與道德判斷
自我潔凈與道德判斷具有復雜的關系,這種關系主要表現為自我潔凈狀態使得道德判斷更加嚴格,同時自我潔凈狀態的消失會減輕道德判斷的嚴格性。
2.1.1 自我潔凈狀態對道德判斷更加嚴格
身體更潔凈,其道德純潔性也更高,潔凈自我與道德自我之間的隱喻關聯性,由此提升了個體的道德自我覺知,從而做出更嚴格的道德判斷。Zhong等(2010)通過研究驗證了身體潔凈與道德的關聯性。在實驗中,他要求實驗組的被試在實驗前清潔雙手,控制組的被試則不作要求,并進行道德判斷。結果都表明,自我潔凈的條件下被試做出更加嚴格的道德判斷,而控制條件無明顯差異。
2.1.2 身體潔凈狀態的消失減輕對道德判斷的嚴格性
身體的自我潔凈會使道德判斷更加嚴格,這一結論得到了論證。那么身體潔凈的消除,對道德判斷有何影響? Schnall等(2008)用實驗證明了潔凈狀態的消除會減輕道德判斷的嚴格性(實驗二)。首先讓被試進入第一個房間看一段視頻激發厭惡情緒,之后在進入第二個房間前告訴洗手組房間很干凈并需要清潔雙手以保持整潔,然后進行道德判斷。結果發現,相對于控制組,洗手組道德判斷相對不嚴格。對此,zhong等(2010)認為這種結論可能與厭惡相關。已有研究論證了厭惡在道德判斷中的作用(厭惡使道德判斷更嚴格),而偶然的厭惡會消除潔凈感(如洗手)。具體來說,洗手減少了影片中殘留的厭惡感,阻止它影響接下來的道德判斷,厭惡與潔凈的相互“抵消”,就減輕道德判斷的嚴厲性。由此在類似實驗中,研究者們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研究結果。
2.2 潔凈與道德情緒
在莎士比亞的經典悲劇《麥克白》中,麥克白夫人由于感到罪孽深重而反復洗手來減輕罪惡感的行為方式,就被稱為“麥克白效應(Macbeth effect)”。麥克白效應主要通過潔凈方式來緩和不道德事件所引發的不道德情緒,如回憶不道德事件產生的厭惡。關于潔凈與道德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被喚起的不道德情緒在潔凈后都能得到緩解(Lee, Schwarz,2010),通過潔凈(如,洗手)讓個體在身體清潔的同時感到心靈的“洗滌”,從而減輕或消除此時此刻由不道德事件所引發的“骯臟感”,回歸道德的純潔,并形成了心理補償機制。
2.3 潔凈與道德行為
2.3.1 不道德行為促使潔凈行為發生
對身體和道德純潔的研究表明, Zhong (2006) 讓被試回憶一件符合倫理道德或不符合倫理道德的事件,之后做W_ _H等填詞游戲;第二個實驗中,讓被試抄寫道德和不道德的故事,然后對兩類產品(清潔類、非清潔類)進行評估。第三個實驗在第一個實驗的基礎上,讓被試回憶事件(道德、不道德)之后,選擇濕紙巾(清潔用品)或者鉛筆(非清潔用品)其中一樣作為禮物。三個實驗都表明,在回憶不道德事件后被試都傾向于選擇與潔凈有關的單詞或是進行潔凈行為。
2.3.2 潔凈后減少補償行為
不道德行為不僅會促使潔凈行為的發生,并同時在潔凈行為發生前產生補償性的利他行為。而在潔凈行為后,個體心靈完成“洗滌”,重新變成了“道德純潔”的人,由于減少了補償性的利他行為。在 Zhong 等(2010)的第四個實驗中,回憶不道德行為并評估自我情緒狀態后,清潔雙手的被試更少做出補償性行為。
2.3.3 潔凈促使道德行為
Liljenquist等(2010)通過實驗驗證了潔凈狀態會促使互惠行為的發生。在實驗中采用一次性匿名信任游戲,將被試隨意分為發送者和接受者。發送者將全部金額給接受者,將會使金額增長3倍,之后接受者選擇剝奪發送者的利益或通過返回部分金額以表對信任的感謝。結果發現,在清潔氣味房間的條件下,被試更多選擇給發送者部分金額,即互惠行為發生。由此,潔凈促使道德行為有了實驗性依據。
2.4 身體潔凈研究的理論解釋
具身認知觀認為認知內容是由身體提供的,“人們對身體的主觀感受和身體在活動中的體驗為語言和思想部分地提供了基礎內容”(Gibbs, 2006)。而在道德判斷中,道德的知情行也是由身體經驗、身體的感受等身體內容所主導的。具身認知的隱喻觀認為,隱喻是人們以一個事物來感知、體驗和表達另一事物的過程,普遍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抽象概念(如道德)大部分是隱喻性的(Lakoff &Johnson, 1999)。長久以來,人們把身體純潔作為源概念,道德純潔作為靶概念,來理解兩者的關聯,由此構成了身體純潔與道德純潔之間的關系。在《麥克白》中,麥克白夫人通過清潔雙手來減輕違背道德的壓力等行為都證明了身體純潔與道德純潔之間的映射匹配,即隱喻。
3 問題與展望
近幾年來,潔凈與道德的進一步研究促進了具身道德的發展,但是在發展的同時,具身道德仍然存在很多棘手的問題。
首先,具身道德概念模糊。具身道德研究范圍依舊過窄,甚至目前僅僅限于對身體潔凈與道德之間的關聯,這對于具身道德的發展還遠遠不夠,還需要不斷的豐富具身道德的內容。其次,具身道德研究結果矛盾重重。如閆書昌(2011)用中國被試的實驗與Zhong等(2006)的實驗結果也并不一致。由此可見,除了實驗本身的差異性,具身道德的跨文化一致性也值得注意。最后,具身道德研究技術的單一難以全面探討復雜、多層次的具身道德內容。未來研究中,研究者應更多采用核磁共振、腦電、生物反饋儀等技術進行具身道德研究。
參考文獻
[1] 閆書昌.身體潔凈與道德.心理科學進展,2011.19(8):1242-1248.
[2] 葉浩生.具身認知:認知心理學的新取向.心理科學進展,2010.18(5):705-710.
[3] Lakoff,G.,& Johnson,M.(1999).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New York: Basic Books.
[4] Lee, S. W. S., & Schwarz, N.(2010).Dirty hands and dirty mouths: Embodiment of the moral-purity metaphor is specific to the motor modality involved in moral transgress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1423-1425.
[5] Schnall, S., Haidt, J., Clore, G. L., & Jordan, A. H. (2008).Disgust as embodied moral judg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 1096-1109.
[6] Zhong, C.-B., & Liljenquist, K.A. (2006). Washing away your sins: Threatened morality and physical cleansing. Science,313,1451-1452.
[7] Zhong, C. B., Strejcek, B., & Sivanathan,N.(2010) A clean self can render harsh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46,859-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