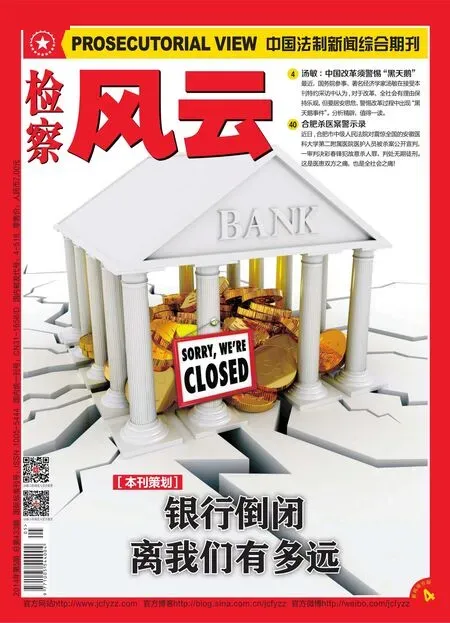自貿區倒逼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文/沈桂龍
簡政放權作為2014年的“當頭炮”,繼續成為十八大后新一屆政府上臺后力推的重要改革,在規范清理的基礎上,再次取消和下放生產經營領域行政審批事項,為2013年以來的第四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事項。
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為何反復拉鋸,行政審批事項為何割掉一茬又生出一茬,癥結到底在哪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被改革者同時又是改革的“主刀者”,改革沒有容納更多的“利益相關者”,未能形成改革的博弈和相互監督機制。而改革打破現有利益格局,又必然會受到有關利益集團的阻撓。更重要的是,《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保留部分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的通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的法律權威,使得行政審批事項的增加有了可以利用的“后門”。這就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徘徊和拉鋸的深層次原因。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以下簡稱“自貿區建設”)作為一項國家戰略,通過開放倒逼改革,努力實現制度創新,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為制度創新的著力點,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突破提供了大好契機。
它可以在國家層面政策支持的基礎上,進行頂層設計,統籌規劃和協調,避免政策間沖突和相互間設置的“木馬”。同時,又由于自貿區在28.8平方公里土地上進行有限范圍的嘗試,因此,可以避免對利益格局的過大震動。這必然會減少改革的阻力,有利于通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小范圍突破,在穩定的基礎上進行推進和復制。
自貿區實踐層面的破冰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已經決定,授權國務院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內暫時調整《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規定的有關行政審批,并提供了具體目錄,調整的試驗運行期限為三年內。
自貿區建設所帶來的開放倒逼為引入更多“利益相關者”,更好地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提供了微觀層面的動力基礎。如果說美國參與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等更高層次的關系協定,是在宏觀層面構成推動自貿區建設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宏觀壓力,那么更多外資企業的進入以及中國美國商會、中國歐盟商會的進一步強大,也就給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提供了更強大的微觀動力。
自貿區建設將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在更高層次上與國際規則接軌提供試驗場所。自貿區將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形成公開透明的政府運作模式,為中國加入多邊貿易和投資做好相應準備工作。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行政審批制度將實行“前輕后重”的整體轉向,探索和完善“負面清單”和“備案制”,真正落實黨的十八大強調的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并為全國的改革實踐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