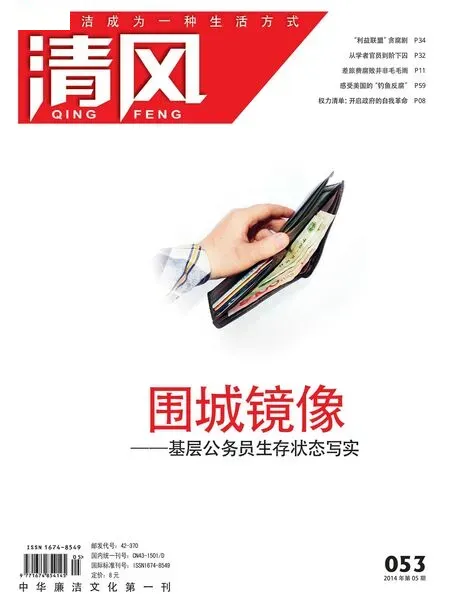禮治、官本位與應酬政治
文__謝明德
禮治、官本位與應酬政治
文__謝明德
一直以來,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對于公務接待的規定可以說非常詳細。然而,往往由于規定的剛性不足,或者制度設計的不切實際,效果不明顯,容易走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死胡同。而在中國的黨政機關中,一些公務人員一邊抱怨官場飯局之累,一邊又對“公款大吃大喝”樂此不疲,皆因在一些地方,公務接待成為“人情關系功利化的一種體現,提供了把組織關系轉化為私人關系,把組織事務轉化為私人事務的媒介,成為政府處理公務的人情成本”。 久而久之,公務接待演化成了一種“應酬政治”。
所謂“應酬政治”,是指把官場應酬作為獲取各種資源的手段。這種官場文化現象的形成和危害,值得思考。北宋史學家司馬光說:“稽古以至治。”鑒古資治,通古察今,歷史思考總是包含著現實考量。筆者試圖通過對古代公務接待的考察,揭示當今國內公務接待異化的歷史、文化原因。
古代的禮治
當下的官場,雖然與古代不可同日而語,但深受古代官場文化的影響。我國的古代公務接待文化,是基于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文化基礎的價值觀念、群體意識、行為規范和傳統等的總結及其在接待活動中的反映,又是我國古代社會政治文化、行政文化的一部分。官僚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的特性,決定了公務接待文化的價值取向,進而形成習慣和傳統。
在我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中,“禮”作為治則與治道之本,是其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的基本特征。儒家推崇以禮治國,孔子說:“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記?經解》)所謂禮治或人治,必須以權利的不平等和權力的不制衡為前提,建立貴賤有等、上下有序的社會政治秩序和道德倫理秩序。孔子及后之儒者特別強調等級名分,要求每個人的行為必須符合自己由政治社會所規定的身份。
早在西周時期,禮作為立國安邦的基本原則和具體制度就已經確立,目的是鞏固宗法貴族等級統治。由春秋開始,中國古代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革與轉型,周室衰微,諸侯并起,“天下大亂”“禮壞樂崩”。隨著秦始皇創立大一統帝國確立專制集權政體和官僚政治制度,禮作為治則與治道被注入封建內涵。皇帝高踞政治和社會權力結構的金字塔頂端,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官僚成為社會主體架構和支配階級。官貴民賤。在官僚內部又以品、階、勛分高低,因等級不同而待遇各異。兩漢以后,儒家的價值觀占據了統治地位,成為中國文化的主導思想。“治之經,禮與刑。”(《荀子》)禮與刑,行政管理與刑事治罪,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政權大廈的兩大支柱。“貴以臨賤,賤以承貴”(司馬光:《通鑒?周紀一》),成為處理社會人際關系的基本原則。
禮治下的消費等級制
禮治模式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將體現政治等級差別的禮或禮儀貫通和覆蓋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而使政治等級差別無處不在。如在《周禮》這部記述西周“政制”并成為歷代政治家取法楷模的儒家大典中,有不少職官是專為國王和宮廷貴族私人生活而設,僅為飲食服務的職官,就有天官中的膳夫、庖人、亨人、臘人、酒正、酒人、漿人、鹽人等等;在春官中還有司尊彝、司幾筵等。周禮規定“凡王之饋,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饈)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禮記》)。周禮還詳細規定了貴族飲宴列鼎的數量和鼎內的肉食種類:王九鼎(牛、羊、乳豬、干魚、干肉、牲勝、豬肉、鮮魚、鮮肉干),諸侯七鼎(牛、羊、乳豬、干魚、干肉、牲肚、豬肉),卿五鼎(羊、乳豬、干魚、干肉、牲勝),士三鼎(乳豬、干魚、干肉)。其他如服飾、房舍、輿馬、禮節、喪葬等等,都有等級差別,任何人不得違反。
禮或禮儀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全面覆蓋,一方面形成消費等級制,不是經濟條件,而是政治地位和特權最終決定一個人的經濟利益和消費狀況,有什么樣的政治地位和特權就有什么樣的消費待遇,從而為統治階級的享樂特權提供了制度保證;另一方面,個人怎樣飲食起居本是一個私人問題,由此被政治化、制度化。也因此,盡管歷代儒家倡導禮以節欲,但這種制度安排下,主導消費選擇的主要不是節儉,而是取決于是否符合規定的等級差別。進一步說,它使消費不能反映人的真實需要,異化為面子消費或權力消費。比如,一個一品官乘驛按規定可以使用8匹驛馬——這是唐時律令規定的標準,即使他不需要使用8匹驛馬,通常不會考慮只使用6匹驛馬。因為,這樣做等于自降身份,而且,還可能要承擔由此被官場視為“另類”的風險。禮或禮儀的生活化和日常生活消費的政治化,以及消費等級制的制度安排,事實上起到刺激面子消費、炫耀性消費的作用。
“官本位”下的接待規則
“官本位”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官職,本是一種行政職位,在古代社會卻是個人的一種權利、身份和地位體現。官貴民賤,官役民作。官僚們在薪俸之外,依照等級被授予種種優待,進而成為特權階層,由此形成官本位的政治價值取向和人生價值取向。同時,嚴格的上下層級制度,使上級對下級擁有絕對的權力;下級則完全聽命于上級,一切只對能決定其個人命運的上級負責。長官意志、權力至上、依附意識、遵循傳統和習慣,等等,成為古代官場的生態特征并形成了一種氛圍,有力影響和塑造古代官僚群體的性格和心理,并必然影響和制約接待過程及價值取向。以上級是否滿意為工作原則和標準,規章制度由此形同虛設,接待往往在提供適當服務的同時異化為違反規定的“應酬”。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舉制既造就了文官政治,為中國歷朝發掘、培養了人才,在一定意義上推動了民間的讀書風氣,但也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強化了官本位的政治價值取向和人生價值取向,使讀書做官成為知識階層的最終目標。讀書為做官,“黃金屋”“顏如玉”“千鐘粟”等各種待遇,權力、利益、特權均可以通過讀書做官獲得,這成為普通讀書人個人奮斗的目標和動力。
封建官僚政治制度和政治、行政文化的性質和特征,決定了古代公務接待文化的基本面。接待腐敗是無法治愈的痼疾。腐敗能在一定時期被遏制,取決于自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以及官員個人的人格操守。
一個富有深意的例子,是張居正在其父病逝后奉旨歸葬。從北京回湖北江陵,一路上各級官吏無不興師動眾,按不低于帝王的規格隆重接待。張居正對沿途經過官署、驛站所提供的飲食極為挑剔。明?焦竑《玉堂叢話》記載:“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為無下箸處。而錢普無錫人,獨能為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僅得一飽耳。’此語聞,于是吳中之善為庖者,召(招)募殆盡,皆得善價而歸。” 一餐飯上供奉菜肴上100種之多,竟然“無下箸處”。直到來到直隸真定府,知府錢普煞費苦心,最后確定以自己的家鄉無錫菜(也叫“蘇州菜”)為主打,終于聽到從張居正嘴里說出“吾至此僅得一飽耳”的肯定的話。早就在四處打探消息,了解張居正的生活習慣和愛好,以提前做好接待準備的各州縣官署、驛站,紛紛高薪聘請擅長烹飪無錫菜的廚師,以致吳中之善為庖者一時間招募殆盡。而錢普也因為接待得好,此后不久,張居正把他從知府任上升調進京任工部右侍郎。張居正這位曾經以鐵腕懲治腐敗包括推行郵驛改革而著稱的萬歷朝內閣首輔,在反對別人腐敗的同時,自己卻也在腐敗。
封建官僚政治制度和政治、行政文化的性質和特征,決定了古代公務接待文化的基本面。接待腐敗是無法治愈的痼疾。腐敗能在一定時期被遏制,取決于自上而下的政治高壓,以及官員個人的人格操守。讀歷史便可知,歷代王朝進入中后期,隨著政治日益腐敗,自利取向逐漸主導官僚群體,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消失殆盡。接待中的腐敗現象滋生蔓延,不過是吏治腐敗的一個方面。官僚們出于利益關系而互相結交,通過互相吃請聯絡感情、培育和發展關系,導致“應酬政治”的產生和盛行。迎送應酬成為官僚們日常的、重要的功課。無論你是情愿的,還是不情愿的;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都必須適應這一官場生存法則。
自乾隆后期起,曾經盛極一時的清王朝開始走上衰敗的道路。林則徐所處的嘉慶、道光時期,各種社會問題日益嚴重,機構臃腫,吏治敗壞,賄賂公行,督撫提鎮以致道府官員出巡,利用公驛恣行享樂,糜費公帑,州縣官除了盛情款待,還要饋送“站規”“門包”,以及有所謂“程儀”或“程敬”,以送禮為名向上司行賄,以便得到關照或升遷。這些贈送公務旅行者的財禮,成為官員陋規收入的重要來源。接待成為縱欲與賄賂的手段。整個大清朝已經病入膏肓,封建專制社會也面臨總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