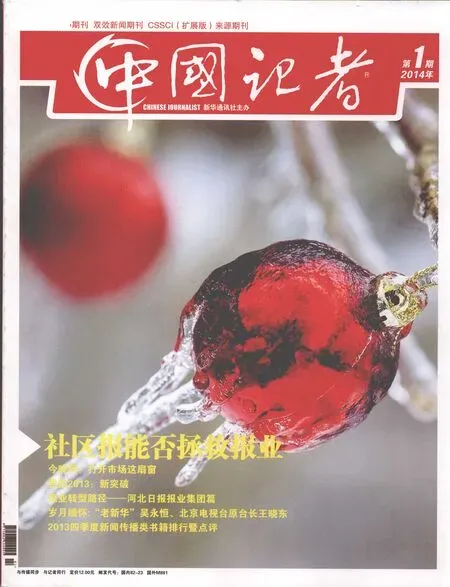聽電視還是看電視?——電視報道的敘事誤區和解決路徑
□ 文/鄭 祎
面對剛入門的電視人,經驗豐富的老編導會告訴他,做節目要學會講故事,在故事中設懸念,吊足胃口。可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大部分節目的懸念都是編導運用解說詞生硬堆砌的。我們究竟是要讓觀眾聽電視還是看電視呢?筆者結合自身的從業實踐,分析電視節目影像敘事的誤區及解除手法。
電視報道的敘事誤區
因電視傳播具有信息稍縱即逝的特點,觀眾記不住解說詞,能記住的只有那些給他留下印象的影像畫面或者現場同期。畫面影像是可以敘事的,即使沒有解說詞,觀眾依然可以通過畫面影像呈現,了解故事發展,通過那些有情節的影像畫面,那些有情感色彩(喜怒哀樂)能產生共鳴的細節呈現,在情感和認知上獲得滿足。
誤區一:“做”敘事而非影像敘事。
在節目中,編導常常是在“做”敘事,而不是影像敘事。我們有很多新聞,是信息通報式的,把文字內容配上空畫面,成為“告知型”新聞;又或者是在事件性報道中,所有的信息都是一種碎片化的狀態,只是交待狀態沒有細節,觀眾無法去體驗,只能試圖理解、了解,顯然達不到傳播效果。
誤區二:將解說替代影像敘事。
那解說能否等同影像敘事呢?答案是否定的。在節目中,很多好片子甚至連一句解說都沒有,全是現場,提供過程和提供動態的現場非常震撼,屬“無聲勝有聲”。
要做到影像敘事,對于記者就提出了要求。采訪前“抓瞎”,采訪時“眉毛胡子一把抓”,采訪回來后用解說充數,那樣根本無法做到影像敘事,最終在現場沒能捕捉到的信息,只能用解說詞生硬地提煉,再貼上空畫面,如果沒有細節,觀眾看到了什么不會記得,最后得到的結果就是觀眾只能聽電視,而看不到有用的信息。
電視敘事的三個階段
如何運用影像來敘事呢?影像敘事是有其特定結構的,分為三個階段。
首先是起因,即概述性說明(新聞五要素:何時、何地、何事、何因、何人)。可是在有些新聞節目中卻常常缺少起因,為什么?因為沒拍到。這就需要記者具有一定前瞻性,也就是提前開機,對于矛盾沖突、現場狀況有比較準確的預判。有些突發新聞也許無法拍到事件發生的起因,記者趕到時記錄下的已經是發展或是高潮階段了,這時怎么辦呢?等記錄完現場之后,必須補充起因,交代事件發生的背景,完成影像的信息缺憾。
第二階段是發展,也就是常說的矛盾沖突最激烈或高潮部分。矛盾沖突是我們在現場捕捉的,而高潮可以不需要沖突,只是情感的高潮,這可以是主觀營造的。當然,無論是矛盾沖突還是情感高潮,都是通過影像來實現的,而不是通過其他手段。
一個敘事到最后是一定要畫句號的,告訴觀眾這事怎么樣了,最后的結果是什么,這在敘事中叫回歸,是第三階段。然而在很多的新聞報道中回歸是做得最差的,高潮結束,自以為意猶未盡,留給觀眾思考,其實事情還沒說清楚。
電視敘事的多元表達
影像敘事有三大關鍵詞:現場、細節、環境。構成了影像敘事的基本元素。
1.現場
現場意識,即選擇現場的能力,是否能夠把握最具典型意義或最本質的現場,直接決定創作的成敗。央視記者柴靜關于小學生集體自殺事件的新聞調查《雙城的創傷》,在結尾部分采訪一個曾經服毒的孩子,孩子始終不愿意與柴靜進行正面交流,在采訪進行不到幾分鐘的時候就起身離開。攝像沒有關機,一直跟拍,孩子跳下土坡后,消失在鏡頭外,攝像又把鏡頭搖回來,對著正在思索一臉凝重的柴靜。幾秒鐘后,柴靜在鏡頭前進行了獨白,告訴人們孩子內心的封閉是集體自殺的原因,打開孩子的心靈是每個大人需要面對的問題,然后鏡頭搖向天空,片子就結束了。整個過程看似一段沒有完成的不成功的采訪,但實際上是攝像抓住的典型性現場段落,恰恰蘊含更豐富、更真實的信息,這或許比一場成功的訪談更有意義。這表明,真正的新聞往往發生在開機之前和關機之后,因此在編導開口之前開機,在編導結束采訪之后繼續記錄,是記錄現場的一個竅門。
首先,過程性記錄是現場感的呈現方式。過程性的關鍵段落,往往是敘事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信息,而單個鏡頭,即使是現場攝錄,一旦離開畫外解說詞的支持,任何組接都無法完成敘事的功能。北京電視臺攝制的《吳若甫被綁架案偵破紀實》中,每個現場都是完整段落,譬如刑偵隊會議討論,駕車搜尋犯罪嫌疑人的落腳點,最后沖進綁架窩點解救人質,包括中間地點轉換的開車過程,所有現場都是帶有完整同期聲的相對連續過程性段落,這些段落完全可以構成一個連續的事件,并在節奏、氣氛上形成一致,產生一種極強的“場”效應。
其次是記者在場感。電視可以提供給觀眾的是視和聽兩感,記者在現場代替觀眾去體驗和感受,要充分調動嗅覺、味覺、觸覺,給觀眾全方位立體的感知。央視《新聞調查》和《焦點訪談》將“記者在現場”作為節目中一種必不可少的固定樣式,每一期節目中都大量地出現記者在現場的感受采訪段落,引領觀眾進入一個又一個現場,一步步深入揭示新聞事件本質。
最后是需提高場面調度能力,實現多樣化轉場。在多個現場和影像敘事段落之間,需要有各種影像組接點,也就是轉場畫面,有了轉場畫面的承接轉合,才會使電視作品段落過渡自然,整體結構順暢。
2.細節
這里所說的細節不是簡單的特寫鏡頭,還包括宏觀細節。
首先,單一細節不敘事,這就要求細節成組。單一細節容易產生歧義,同時電視是線性傳播,單一細節容易令觀眾忽視,所以在拍攝細節時需拍攝與細節相關聯的其他細節,成組呼應,形成特寫蒙太奇效果,才能客觀反映事物全貌。其次,強調微觀細節和宏觀細節相結合。微觀細節和宏觀細節構成的兩極鏡頭,表現了細節的兩個方面,宏觀細節傳達“勢”的力量,營造氛圍;微觀細節指向性極強,傳達“質”的信息。張藝謀在《北京申奧宣傳片》中,大全景和大特寫的反復交替出現,將兩極鏡頭運用到了極致,極具視覺震撼效果。
3.環境
在敘事中強調環境意識,即環境表達要簡潔凝練。紛繁復雜的環境只能弱化畫面的本質信息,因此,在人物采訪時有時會故意用長焦鏡頭將繁雜的背景虛化,形成相對簡潔的環境效果,以此突出主體人物,選擇典型性環境。例如,央視新聞聯播目前不斷改進報道方式,將典型性環境作為主題報道現場切入的主要方式,在“落實科學發展觀”主題系列報道中,《東北振興篇》的大豆加工廠、《淮河治水篇》的水利廳防汛會現場,都選擇了能夠表現主題的典型環境,為情節化敘事做好了鋪墊。現場環境并不一定都是背景、前景或陪體,有時也能夠轉化成主體。而且環境具有極強的隱喻功能,對增強畫面的表現力、表現題材內涵和創作主題都很重要,因此選擇的環境要有“最終轉化為現場”的能力。例如,曾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的長消息《胡錦濤和老區群眾一起過春節》,記者著重選擇了胡錦濤在農戶家中和大家一起包餃子的特定環境,畫面從包餃子的特寫配畫外解說過渡到胡錦濤詢問農戶吃飯問題的現場同期聲段落,這時候,包餃子的場景從環境交代直接轉化為新聞事件的現場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