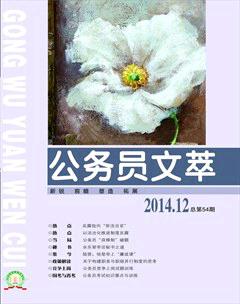崔永元:“我其實一點都沒有變”
劉子倩
離開央視以后,崔永元的曝光率似乎比之前更高。辭職前幾年,他主持的節目大多在零點前后徘徊,辭職后,他像一匹脫韁野馬,躍過禁錮的藩籬。他會在微博上與人對罵,甚至連飆糙話;他自費百萬四赴日本、美國調查轉基因,拍攝紀錄片,被貼上反轉基因“斗士”的標簽;他簽下2億天價代言,表態要全部捐出,仍飽受爭議。
這都發生在離開央視之后。對于這位微博上擁有570萬粉絲的大V來說,他在微博上“過激”的語言,總會引來網友的驚愕、質疑甚至是揶揄。
“我其實一點都沒有變。”崔永元說,現在過的才是最快樂的日子。
“就是得盡快轉行”
從正門進入中國傳媒大學,右拐再走一二百米,有一座四層白灰色的樓,中國傳媒大學老圖書館。這里是崔永元口述歷史研究中心。
在這座四層的博物館里,崔永元一共建立了包括口述歷史博物館、電影博物館等在內的七個館室,他將把自己收藏的30萬件物品全部展出。與其他博物館只供參觀不同,在崔永元的計劃中,學生可以通過網上預約系統,在博物館里上自習。“坐著一百多年前的椅子,用著一百多年前的桌子,那看書是什么感覺?”他有些得意。
事實上,入駐中國傳媒大學已是兩年前的事。2012年2月27日,中國傳媒大學與崔永元簽約,合作成立口述歷史研究中心及口述歷史博物館。7個月后,在中國金鷹電視藝術節上,他證實了欲離開央視赴傳媒大學教書的傳聞。“我希望五年后評全國十大教授。”當年,崔永元曾這樣說。
“你們愛說什么說什么”
崔永元辭職的原因簡單,“精神壓力大,不太適合做節目。”
2013年12月18日,他在微博上承認已正式辭職,赴中國傳媒大學任教。在此之前的十余天時間中,他正實施著一場即將引發公眾高度關注和爭論的行動——赴美拍攝轉基因調查紀錄片。
這一切源于2013年9月8日的一條微博。
當時,他看到一則新聞,有人稱“要創造條件讓國人天天都吃轉基因”。他對這樣的語言模式很反感。他在微博中寫道:你可以選擇吃,我可以選擇不吃。你可以說你懂“科學”,我有理由有權利質疑你懂的“科學”到底科學不科學。
他未料到,這是一場口水“戰爭”的序幕。難聽的話很快布滿了評論,這讓他覺得“這里面肯定有大事,否則對方怎么這么快就亮劍呢?”一向“軸”的崔永元正式跟轉因基杠上了。他決定赴美拍攝紀錄片。當他把自費100萬人民幣拍攝的40小時的素材剪輯為69分鐘的紀錄片在網上放出后,褒貶聲接踵而至,支持者認為客觀中立理性,反對方認為調查不科學,預設立場。小崔不干了,“我是學新聞的,什么是預設立場,我拿五萬塊錢雇人在美國找些反轉基因的人隨便拍拍不就得了,我可以投機取巧,但那不是我為人做事的風格。”
他說,他反對的不是轉基因,而是公眾缺乏知情權和選擇權。“我去美國調查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他們可以選擇一輩子吃或不吃轉基因食品,因為所有食品都是明確標注的,而我們就做不到。”
然而,網上的質疑和謾罵聲并未停止。遇到講理的,他會跟對方理論幾句,碰上出口成臟的,他也不含糊,甩出幾句粗話。網民對他的應對方式感到錯愕。
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評價。“之前你們說我是中國最好主持人,什么媒體良心,現在又說是小丑、公知,你們愛說什么說什么,跟我有什么關系呢?我會因為你們改變自己嗎?”
“時代分化得很厲害,我的觀念
還沒有轉過來”
微博是崔永元與外界相連的最便捷的途徑。他也用微信,主要是與海外的朋友聯系,遇到老物件可以隨時溝通。
30多萬件藏品,也考驗著崔永元的記憶。在二樓的電影博物館里,中央擺放著大型電影放映設備,墻上掛著1923年的電影海報和1930年代的旗袍,展柜里放著周璇用過的墨盒和胭脂盒,1950年代拍《白毛女》時用過的鐮刀,阮玲玉去世時守靈照以及被崔永元稱為國寶的《武訓傳》的劇本。
崔永元把收集到的史料中頗有意味的內容摘錄下來,貼在墻上。
在旁邊一間館室里,大多展出的是新電影的道具,《十月圍城》里孫中山的帽子,《山楂樹之戀》中的鋼筆和臉盆,《三槍拍案驚奇》開場出現的波斯大炮,囿于空間無法展出的《太陽照常升起》里的拖拉機。
在眾多道具中,有一個破舊的銅號,那是馮小剛《集結號》中的標志道具。2003年,馮小剛《手機》上映后,崔永元對這部電影的批評曾被媒體熱炒,在公眾心中,二人一度失和。崔永元認為這個標志事件令他如夢方醒。他說,他的初衷只是文藝批評,并誤認為社會依舊有這種氛圍,但媒體的反響和周邊人的反應讓他絕望,崔永元日后猛醒,“其實是早就進入互聯網時代了,而我還沒有做好準備。”
在此后長達十年時間,或許算作崔永元對網絡時代的適應期。如今,對于網絡的喧囂,他習以為常。但似乎仍然難以與這個時代無縫對接。崔永元也發現了與時代的某種代溝。他問90后的女兒和80后的助理,會不會去看電影《歸來》。兩人異口同聲地拒絕了。崔永元馬上想到一位韓國導演問他的問題:如果沒有禁區,你會拍什么電影?崔永元想都沒想:“粉碎‘四人幫和‘9 ·13事件。”這位導演說,他們曾想拍光州事件,但解禁之后,拍出來卻沒有人看了。“這個時代已經分化得很厲害,但我的觀念還沒有轉過來。”
“我不愿匯入這個洪流”
離職勾起他對那個黃金年代的懷念,“想想當年的《焦點訪談》《實話實說》《新聞調查》,那多有力度。至少在引領社會的一個思考方向。現在的追求就是完成任務,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內在的精神品質和追求不斷下降。”
當然,環境也在改造著崔永元。1990年代,他是憤青,領導斃他的選題,他會天天去找領導拼命,這幾年,他發現自己也在變化,選題不通過,那就多報幾個,節目敏感,就在凌晨播出。“我已經五十歲了,我學會了妥協。”
然而,對于原則問題,他仍然還會拒絕。他主持《謝天謝地你來啦》,劇組想把即興表演的劇情提前向演員透露,崔永元堅決反對,“即興就是即興,否則就是欺騙觀眾。”
在中國電視主持人的譜系里,崔永元毫無疑問位于譜系的塔尖,無論主持什么節目,他都會展現詼諧幽默的主持風格,他的節目鮮有爭議,更多的是溢美之詞。盡管他節目的收視率越來越低,但這并不影響他在譜系中的地位。
離開央視,他不再憤青,保持微微的憤怒,學會了妥協,但離開央視后,他可以自由地掌控妥協的尺度。而同時,他也延續著做新聞時的理想主義。
在傳媒大學,他開了口述歷史的課程,負責講口述歷史概論,一年只授課四次,頭一次課就來了三千多人,他不得不更換教室,把授課改成了講座。
這種氛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還成立了公益基金,接了2億代言費的廣告,他試圖向公眾傳遞一種理論,慈善不是施舍,它只是一種生活方式。公益基金遭舉報,主管部門核查后順利過關,但他卻改變了主意,做公益還招人罵,所以媒體不花大力氣“贊美”他,他不會把承諾的2億代言費捐出來,“扣了稅是一億三千萬,我就不捐,你們管得著嗎?”他說,他就想把對慈善的錯誤觀念扭轉過來。
在他看來,一些圈內人士一輩子只做兩件事,出名和維護名聲。但他計劃用三年時間把名聲抹掉,與學生們一起坐在博物館里看書,沒人過來索要簽名。
他仍然喜歡“病人”這個稱呼,“如果我現在是正常崔永元的話,就證明我認可這個社會的病,我寧肯頂著這個稱號,因為我不愿匯入這個洪流。”
(摘自《時代郵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