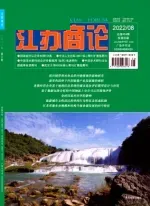基于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的省域邊界區(qū)城市旅游可持續(xù)發(fā)展機(jī)制研究
李友亮
(信陽(yáng)師范學(xué)院 工商管理學(xué)院,河南 信陽(yáng)464000)
一、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與城市旅游系統(tǒng)
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具有三大本質(zhì)體現(xiàn),即“發(fā)展度”、“協(xié)調(diào)度”和“持續(xù)度”。[1-2]可見(jiàn),在旅游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上,旅游者所體驗(yàn)與觀賞的客體不再是單一的景點(diǎn),城市內(nèi)的所有要素都是觀賞對(duì)象,它們之間配合的優(yōu)劣程度以及形成的良好城市氛圍將直接或間接影響旅游者對(duì)該城市的印象認(rèn)知。[3]因此,城市旅游系統(tǒng)主要是以城市空間為依托的一個(gè)大系統(tǒng),該系統(tǒng)的持續(xù)發(fā)展能力不僅取決于城市擁有的旅游資源特色、服務(wù)能力、產(chǎn)品市場(chǎng)認(rèn)知度,而且還依賴于城市旅游產(chǎn)業(yè)價(jià)值鏈上所有參與者的共同努力。
城市旅游經(jīng)營(yíng)管理必須以可持續(xù)發(fā)展理論為指導(dǎo),這是城市旅游經(jīng)營(yíng)管理的內(nèi)在要求。這是因?yàn)閺哪壳俺鞘泄芾韥?lái)看,城市旅游經(jīng)營(yíng)管理主要是指政府等參與主體運(yùn)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手段,對(duì)城市旅游發(fā)展所依托的基礎(chǔ)資源設(shè)施、自然景觀、人文資源、旅游產(chǎn)業(yè)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等進(jìn)行優(yōu)化整合和市場(chǎng)化運(yùn)營(yíng),實(shí)現(xiàn)城市綜合資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改善和提升城市旅游功能,增強(qiáng)城市自身價(jià)值和綜合競(jìng)爭(zhēng)力,提高城市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譽(yù)度,擴(kuò)大對(duì)生產(chǎn)要素的吸引力和聚集度,增強(qiáng)輻射能力,實(shí)現(xiàn)旅游資源與城市建設(shè)發(fā)展度、協(xié)調(diào)度和持續(xù)度的有機(jī)結(jié)合,不斷延伸城市旅游的生命周期,實(shí)現(xiàn)旅游業(yè)在城市經(jīng)營(yíng)管理中長(zhǎng)期貢獻(xiàn)效益。
二、省域邊界區(qū)城市旅游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困境
從系統(tǒng)角度來(lái)說(shuō),城市旅游系統(tǒng)是一個(gè)由眾多要素組成的大旅游環(huán)境系統(tǒng)。在此系統(tǒng)中,旅游流系統(tǒng)是核心。馬耀峰教授(2001)認(rèn)為:旅游流系統(tǒng)是一個(gè)空間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它是游客流、信息流、資金流、物質(zhì)流、能量流、文化流等旅游子流的集合,其中游客流是旅游流系統(tǒng)中的主體。信息流是旅游流產(chǎn)生的主導(dǎo),資金流是旅游流產(chǎn)生的運(yùn)作條件,能量流是旅游流的必然,物質(zhì)流是旅游流產(chǎn)生的保證,文化流是旅游流的結(jié)果。為此,馬耀峰教授認(rèn)為,旅游者選擇城市的標(biāo)準(zhǔn)主要取決于以下幾個(gè)因素:(1)豐富的旅游資源;(2)便捷的交通網(wǎng);(3)完善的城市基礎(chǔ)設(shè)施;(4)較高的知名度;(5)鮮明的城市形象;(6)友好文明的社會(huì)環(huán)境。[4]而張輝教授(2004)認(rèn)為,在旅游系統(tǒng)的“啞鈴經(jīng)濟(jì)”體系中,較之于傳統(tǒng)的“物流”經(jīng)濟(jì)體系,其最大的特點(diǎn)是“人的流動(dòng)而非物的流動(dòng)”。[5]可見(jiàn),城市旅游的持續(xù)發(fā)展不僅取決于城市自身的資源、文化、品牌及形象等獨(dú)特性,更重要的是城市在區(qū)域空間內(nèi)對(duì)身處異地的旅游者能否產(chǎn)生吸引力以及外地旅游者是否具有愿意前往該城市旅游的內(nèi)驅(qū)力。
然而,在“行政區(qū)經(jīng)濟(jì)”為主導(dǎo)的背景下,省域邊界區(qū)城市旅游持續(xù)發(fā)展往往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使得其在區(qū)域旅游發(fā)展中的參與客源競(jìng)爭(zhēng)的機(jī)會(huì)和能力較之中心城市或重點(diǎn)城市相對(duì)較弱,發(fā)展限制條件較多,[6]其中來(lái)自行政邊界屏蔽的制約最為嚴(yán)重。從實(shí)踐來(lái)看,旅游者對(duì)目的地選擇除了內(nèi)在偏好差異外,其主要受到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條件影響很大。其中資源特色、產(chǎn)品品牌認(rèn)知度、交通便利條件、社會(huì)環(huán)境等是主要因素。省域邊界區(qū)城市雖然具有一定的資源特色,但由于行政邊界屏蔽作用,其旅游資源的產(chǎn)品轉(zhuǎn)化能力、交通便利條件、城市綜合發(fā)展環(huán)境(尤其是商業(yè)環(huán)境)等方面均處于一省行政區(qū)內(nèi)的等級(jí)末梢,在“經(jīng)濟(jì)資源配置更多傾向于高層政府所在地的情況下,權(quán)力部門難以或不愿太多考慮行政邊界地區(qū)的發(fā)展,使其邊緣化”。[7]為此在省內(nèi)的旅游產(chǎn)業(yè)政策中,在重點(diǎn)項(xiàng)目布局、稅收、貸款及其他相關(guān)支持條件均處于邊緣化。這將導(dǎo)致邊界區(qū)城市旅游流動(dòng)渠道不暢,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不足。
可見(jiàn),行政邊界的屏蔽作用不僅使邊界區(qū)城市處于省域發(fā)展的邊緣或非中心地位,而且它往往直接導(dǎo)致省域邊界城市旅游形象處于公眾印象的“灰度區(qū)”,這種“灰度區(qū)”一直被“替代效應(yīng)”所籠罩。由于旅游供給的區(qū)域固定性使得旅游區(qū)域競(jìng)爭(zhēng)難以通過(guò)供給體系的空間轉(zhuǎn)移來(lái)化解,因此旅游城市之間的形象替代關(guān)系強(qiáng)弱將直接影響旅游城市的旅游接待規(guī)模和發(fā)展周期。這種替代現(xiàn)象主要包括以下幾種:一是轉(zhuǎn)移性替代。它主要反映的是在城市現(xiàn)代化過(guò)程中,邊界區(qū)城市的發(fā)展速度、檔次與區(qū)域中心城市有巨大差距,其給潛在旅游者所營(yíng)造的旅游氛圍與體驗(yàn)效果完全不同。“嫌貧愛(ài)富”是城市旅游者的本性,在此情況下,更具有現(xiàn)代化氣息和便捷的商務(wù)環(huán)境的中心城市在吸引游客方面遠(yuǎn)超過(guò)邊界區(qū)旅游城市。二是競(jìng)爭(zhēng)性替代。它主要是旅游城市發(fā)展過(guò)程中,彼此產(chǎn)生了新的競(jìng)爭(zhēng)者和替代品,由此造成旅游者旅游選擇機(jī)會(huì)與出游空間擴(kuò)展,它將使邊界城市的旅游資源優(yōu)勢(shì)轉(zhuǎn)弱。三是時(shí)滯性替代。它主要是指旅游者對(duì)旅游城市的形象認(rèn)知與旅游城市自身形象的改變之間并不完全同步的現(xiàn)象。從認(rèn)知心理學(xué)來(lái)說(shuō),人們對(duì)一個(gè)城市旅游形象的認(rèn)知總存在一種“先入為主”的現(xiàn)象,要改變這種心理的“刻板認(rèn)知”并不是旅游城市單方面努力所能完成的。四是屏蔽性替代。它主要指由于旅游城市在眾多城市目的地體系中所占據(jù)的位勢(shì)差異而產(chǎn)生的強(qiáng)勢(shì)旅游地形象屏蔽弱勢(shì)旅游地在旅游者認(rèn)知體系中位置的現(xiàn)象。它往往會(huì)使旅游者簡(jiǎn)單地用強(qiáng)勢(shì)旅游地的形象內(nèi)容代替對(duì)弱勢(shì)旅游地的形象認(rèn)知和判斷。
三、省域邊界區(qū)城市旅游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提升機(jī)制選擇
從可持續(xù)發(fā)展追求發(fā)展度、協(xié)調(diào)度和持續(xù)度“三度”有機(jī)結(jié)合的本質(zhì)特征來(lái)看,省域邊界區(qū)城市旅游可持續(xù)發(fā)展離不開(kāi)各參與主體圍繞旅游客流的吸引力,不斷提升自身作為質(zhì)量,其中政府的主導(dǎo)力、企業(yè)的推動(dòng)力、中介的服務(wù)力則是三個(gè)關(guān)鍵因素。為此,省域邊界區(qū)城市旅游發(fā)展應(yīng)重點(diǎn)提升內(nèi)力與外力的運(yùn)營(yíng)能力。具體表現(xiàn)為外部的“順勢(shì)與借勢(shì)”和內(nèi)部的“育勢(shì)與運(yùn)勢(shì)”。
1、外部的“順勢(shì)”和“借勢(shì)”
省域邊界城市在旅游持續(xù)發(fā)展能力提升過(guò)程中,應(yīng)充分尊重邊界屏蔽存在的客觀現(xiàn)實(shí),積極做到“順勢(shì)而為”,應(yīng)尋找外部機(jī)遇,使城市旅游發(fā)展“自覺(jué)服從和主動(dòng)順應(yīng)”外部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與機(jī)遇。而要真正做到“順勢(shì)而為”和“借勢(shì)而為”,重點(diǎn)的是城市旅游參與主體要正確“審時(shí)度勢(shì)”,即開(kāi)發(fā)主體必須認(rèn)識(shí)到國(guó)家、區(qū)域等不同層次對(duì)于旅游業(yè)發(fā)展的形勢(shì)變化,包括產(chǎn)業(yè)政策、市場(chǎng)需求、法律環(huán)境、區(qū)域合作等宏觀調(diào)控方面的新變化和利好政策取向,積極抓住機(jī)遇,審時(shí)度勢(shì),及時(shí)調(diào)整城市旅游發(fā)展戰(zhàn)略及產(chǎn)業(yè)布局。其中“審勢(shì)”即是要求省域邊界城市一定要與外部環(huán)境的“勢(shì)”保持匹配,順勢(shì)而為。其次還要積極“因勢(shì)而動(dòng)”。“審勢(shì)”只是“坐而論道”,或消極地“順其自然”,各參與主體(尤其是城市政府)要徹底轉(zhuǎn)變觀念,破舊立新,轉(zhuǎn)變發(fā)展方式,創(chuàng)新發(fā)展模式。另外,還要有“乘勢(shì)而上”的勇氣和魄力。順勢(shì)而為的目的在于 “化宏觀約束為現(xiàn)實(shí)機(jī)遇,促成矛盾的轉(zhuǎn)化”,在推動(dòng)城市旅游自身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發(fā)展動(dòng)力、要素支撐等條件優(yōu)化中有所作為。
2、內(nèi)部的“育勢(shì)”和“運(yùn)勢(shì)”
對(duì)于以“旅游客流”為核心的城市旅游流大系統(tǒng)來(lái)說(shuō),其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最大威脅來(lái)自區(qū)域各城市旅游之間的發(fā)展不平衡,因?yàn)檫@種不平衡直接導(dǎo)致城市在區(qū)域的不同的位勢(shì)層次。除了借助外部的機(jī)遇以及外部順勢(shì)與借勢(shì)來(lái)提升自身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外,更要加強(qiáng)自身在區(qū)域內(nèi)的經(jīng)濟(jì)勢(shì)能提升以及參與區(qū)域旅游客源的競(jìng)爭(zhēng)。這主要取決于邊界區(qū)城市自身是否具備積極作為、順勢(shì)而為的能力和條件。這離不開(kāi)自身的“育勢(shì)”和“運(yùn)勢(shì)”能力的提升。所謂“育勢(shì)”和“運(yùn)勢(shì)”,主要是指運(yùn)用已有的、內(nèi)在的、外在的可能不很明顯的優(yōu)勢(shì)和力量,通過(guò)自身努力,直接或間接地鞏固、擴(kuò)大,使之發(fā)展為“利我”的勢(shì)態(tài)。對(duì)于省域邊界區(qū)城市旅游來(lái)說(shuō),關(guān)鍵是要引起事物內(nèi)部矛盾發(fā)生相應(yīng)的變化,最終達(dá)到運(yùn)籌主體順利實(shí)現(xiàn)乘勢(shì)而起的目的。

圖1 邊界區(qū)城市旅游位勢(shì)提升影響因素

圖2 邊界區(qū)城市政府作為質(zhì)量與旅游持續(xù)發(fā)展的關(guān)系
3、提升能力與質(zhì)量
省域邊界城市旅游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提升關(guān)鍵在于這種內(nèi)部育勢(shì)和運(yùn)勢(shì)能力的提升,它主要取決于城市本身的集聚能力、城市形象的感召力和驅(qū)動(dòng)力等綜合能力的匹配與提升水平(圖1)。
可以說(shuō),省域邊界區(qū)城市政府在旅游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產(chǎn)業(yè)政策指向、行為觀念、行為質(zhì)量以及順勢(shì)和運(yùn)勢(shì)能力將直接決定能否將宏觀的外部產(chǎn)業(yè)政策、周邊的競(jìng)爭(zhēng)環(huán)境、市場(chǎng)需求的利好因素轉(zhuǎn)化為本城市旅游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dòng)力,實(shí)現(xiàn)旅游業(yè)在發(fā)展度(數(shù)量上)、協(xié)調(diào)度(質(zhì)量上)和持續(xù)度(時(shí)間上)的持續(xù)激勵(lì)(圖2)。
四、結(jié)語(yǔ)
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體現(xiàn)為發(fā)展能力、協(xié)調(diào)能力和持續(xù)能力的綜合統(tǒng)一。城市旅游系統(tǒng)是一個(gè)以“游客流”為核心的,包括信息流、資金流、物質(zhì)流、能量流、文化流等在內(nèi)的旅游流系統(tǒng),是一個(gè)空間網(wǎng)絡(luò)系統(tǒng)。在“人的流動(dòng)而非物的流動(dòng)”的旅游流系統(tǒng)本質(zhì)的規(guī)定下,城市旅游的發(fā)展關(guān)鍵取于城市在區(qū)域空間內(nèi)對(duì)身處異地的旅游者能否產(chǎn)生吸引力以及外地旅游者是否具有愿意前往該城市旅游的內(nèi)驅(qū)力。
在行政區(qū)經(jīng)濟(jì)背景下,省域行政邊界給邊界區(qū)帶來(lái)的客觀屏蔽作用下,使邊界區(qū)城市旅游一直處于公眾印象的“灰度區(qū)”,這種“灰度區(qū)”一直被“替代效應(yīng)”所籠罩,直接影響邊界城市旅游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為此,省域邊界區(qū)城市旅游發(fā)展應(yīng)重點(diǎn)提升內(nèi)力與外力的運(yùn)營(yíng)能力。具體表現(xiàn)為外部的“順勢(shì)與借勢(shì)”和內(nèi)部的“育勢(shì)與運(yùn)勢(shì)”的有機(jī)結(jié)合運(yùn)用能力。為此應(yīng)重點(diǎn)尋求當(dāng)?shù)爻鞘姓⒙糜纹髽I(yè)和中介組織等三大行為主體的作為質(zhì)量提升途徑,不斷突破行政邊界造成的屏蔽效應(yīng),實(shí)現(xiàn)邊界區(qū)城市旅游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1]中國(guó)科學(xué)院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組.2001年中國(guó)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報(bào)告[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1.
[2]李友亮.基于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的縣域旅游持續(xù)發(fā)展機(jī)制研究[J].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2012,(2):45-47.
[3]吳成基.旅游區(qū)三重旅游環(huán)境系統(tǒng)及其優(yōu)化調(diào)控[J].旅游學(xué)刊,2001,(4):52-55.
[4]馬耀峰.旅華游客流動(dòng)模式系統(tǒng)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4-52.
[5]張輝,厲新建.旅游經(jīng)濟(jì)學(xué)原理[M].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
[6]李友亮.省域邊界區(qū)參與區(qū)域旅游競(jìng)合困境及化解[J].商業(yè)時(shí)代,2013,(6):137-138.
[7]陶希.轉(zhuǎn)型期中國(guó)跨省都市圈區(qū)域治理——以行政區(qū)經(jīng)濟(jì)視角[M].上海:上海社會(huì)科學(xué)院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