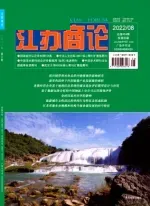我國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問題研究
張建芳,馬穎莉
(南通理工學院,江蘇,南通 226001)
一、研究背景
2011年的個稅改革將扣除數由原來的2000元提升到3500元,目前的個稅制度,工資薪金所得的費用扣除并沒有考慮納稅人家庭負擔等情況,結果往往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三口之家,只有一人工作,養活三口人,每月只有三四千元的收入,本已不寬裕,但仍要繳個稅。我國東西部發展狀況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在“一刀切”的扣除方法下,發達地區的人們只有一部分的生活支出被扣除,不發達地區的情況卻恰恰與之相反。所以,我們應根據不同地方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對扣除數做出相應的調整,采用費用扣除機制浮動化,區域化的形式。
二、我國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存在的問題
1、費用扣除存在缺陷
我國的費用扣除具體涵蓋兩個部分,一是根據生計費用采取固定數額的扣除。這一部分大體包括日常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家庭支出,然而,未區分各個項目。贍養支出、子女教育支出、醫療支出等各項干預稅收機會公平的部分均未體現在扣除金額中。二是所得收入所帶來的費用支出的扣除。廣義上來說,這類扣除的對象為:財產租賃所得、個體工商業戶所得、財產轉讓所得、承租承包經營所得等等,然而,卻不包括:稿酬所得、勞務所得、偶然所得、薪金工資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及股息利息紅利所得。我國根據不同的所得制定不同的扣除標準。比如薪金工資所得計稅根據為每月扣除3500元;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稿酬所得、財產租賃所得、勞務報酬均按標準價格800元和20%扣除;財產轉讓所得的計稅標準為收入總額與稅費、財產原值的差;而全額征稅適用于偶然所得及股息利息紅利所得。我國的扣除標準沒有考慮家庭的因素,也沒有考慮物價指數。個人所得稅法將獲得的工資薪金免征額一致設為3500元。一刀切的征管方式無法符合我國現階段的國情,同時也不利于稅收公正的原則的實現。我國各地的工資水平不同,經濟的發展水平存在著很大的差異。3500元的個稅起征點對不同的地方就有所差異,此起征點適用于貧困落后的西部地區,對上海、北京等一線城市來說就顯得過低。因為納稅人所面對的物價水平、家庭負擔狀況都有所差異,獲得同樣的所得需支付不一樣的成本
2、費用扣除不合理
費用扣除沒有考慮到個人實際的稅負能力。首先,費用扣除數沒有考慮地區差異。
舉例說明:甲和乙兩位大學畢業生,甲畢業之后回家鄉宿遷工作,就職一家外企,在市區租了一室一廳每月租金500元,每月工資6000元;乙某畢業之后在上海一家公司就業,每月6000元在浦東郊區租下一室一廳每月租金1800元。
甲乙的收入相同他們繳納的個人所得稅=(6000-3500)×10%-105=145 元,甲扣除每月支付的房租500元,還剩5355元。乙某扣除稅金和房租之后還剩4055元,不算其他支出,乙某實際所得每月已經比甲某少了1300元,所以不考慮地區差異,不利于稅收的公平。
其次,目前以個人為單位的個稅費用扣除不能把家庭因素放入考慮的范圍。舉例說明,同一個城市有馬某和王某兩個家庭,馬某家庭成員有妻子朱某和兒子,一家三口,陳某和妻子朱某每月收入各5000元,各扣除個人所得稅45元,家庭收入9910元,人均收入3303元;而王某家庭成員只有妻子李某,家庭每月收入情況和馬某家相近,但是王某家人均收入為4955元,第一個家庭馬某家支出多,人均收入反而少1651元,不利于稅收公平。所以,費用扣除公平準則是稅制改革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3、費用扣除額度不隨著物價指數進行變動
物價的變動影響著居民的支出,在我國,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沒能與物價指數掛鉤,稅制缺乏彈性。以1978年的居民消費價格定基指數為100,至2012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定基指數為579.1。

表1 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定基指數
如表1所示,以1978年居民消費價格為定基,至2012年,我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為1978年的5.8倍。但是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的扣除數只從800元提升至3500元4.35倍。物價的上漲與通貨膨脹,相當于降低了費用扣除數。費用扣除數應隨著物價的波動有所改變。
三、完善費用扣除的一些思路
1、細化費用扣除項目
當今,我國沒有一個完整的稅前費用扣除準則,納稅人所面臨的重擔未列入定額扣除的考慮范圍內,費用扣除標準應包括與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活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如:殘疾人、無自主生活能力的人、老年人、重病患者的生活費用,費用扣除的范圍還應包括:投身于慈善事業的、買了房屋的、有在校學生的家庭費用支出,我們應該要細化費用扣除項目。
2、費用扣除數實行指數化扣除標準

表2 我國個稅稅制模式下的費用扣除體系表
最近這段時間,我國不斷調整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這表明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對個人所得稅制的要求不斷提高,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采取固定方式已經不是良策。目前,我國的社會物價逐漸上漲,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改變的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也會由于上漲的物價而不斷抵消,這就使得調整免征額無法改變收入分配的現狀,無法減輕納稅人的稅收負擔。一直不變的免征額使得納稅人的實際稅負不斷飆升,因不斷增長的名義收入,使收入較低本不需要納稅的一部分人不得已而納稅,這樣無法充分發揮個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所以,為適應目前不斷提高的消費品物價,我們應指數化的調整個稅的費用扣除。我們可以依靠各項費用浮升情況及它們相比于基年的指數變化對贍養扶養支出、醫療支出、教育支出做出相應的調整,對于費用扣除采取固定數額的形式,我們應實行指數化調整。全國人大聽證會把確定費用扣除額的標準劃分為幾個指標:經濟狀況良好的地區員工基本消費支出、各個地方納稅人收入的實際水平、全國范圍內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平均水平及全國員工工資薪金的平均值。為充分發揮個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我們的費用扣除標準應定為全國范圍內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平均水平。
從表3可以看出居民人均消費支出隨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而增長,隨著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上漲而下降。一方面,低收入者因為名義收入的上漲而成為納稅人,低收入者因為承擔了一定的稅負,使得其實際收入下降,不利于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的發揮;另一方面,物價上漲迫使居民降低消費性支出,影響了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時間接的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所以需要對個人所得稅的免征額進行指數化調整。2011年,3500元作為個稅費用扣除的新標準,沒有很好地考慮物價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這樣使得扣除標準嚴重滯后于經濟的發展速度,假如頻繁的修改稅法,破壞了稅法的嚴肅性。建議可以對納稅人的扣除標準采用指數化管理,依據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的情況按年度對標準扣除額進行及時調整。在現在的經濟發展情況下,可以這樣操作,當一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幅超過3%的或者連續兩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增幅超過5%時動態調整扣除標準。對于生計扣除標準可以和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步變化,對于不常發生的扣除比如捐贈支出可以在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化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微調。

表3 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比
3、實施地區差異化納稅

圖1 2012年部分地區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費性支出
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情況是,發達地區的居民收入一般都超過了起征點但是這些地區的居民消費也同樣大大超過西部地區。我國目前的“一刀切”的費用扣除標準,就會使物價高、消費高的地區居民的生活實際成本高于費用扣除標準,增加了稅收負擔。對于物價低、消費低地區的居民,生活的實際成本可能會低于費用扣除標準,對于他們就不會承擔個稅,這樣會使得財政收入減少,不利于居民收入的公平分配。
圖1明顯可見較發達的地區上海、北京的居民消費性支出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區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不同地區的消費水平確實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從圖中可以看出上海地區居民消費性支出是甘肅、西藏地區的兩倍多,而現行的費用扣除制度沒有考慮地區消費差異,只是單純的通過收入的高低來決定是否納稅,個稅征收就沒有真正達到調節個人收入差距的目的。采取地方性差異化的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可以使全國納稅人的稅負都相應減少。
四、結論
我國個人所得稅起步較晚,雖然近幾年增長的勢頭迅猛,但是與發達國家還存有一段差距。我國以個人為單位,只關注了個人的納稅能力和收入水平,忽視了家庭成員的組成、受教育的程度、納稅人的婚姻、家庭保險狀況、納稅人撫養小孩、贍養老人時所面對的家庭負擔,納稅人身上承擔著巨大的社會壓力,而卻讓他們拿著自己辛勤勞動所賺的錢來參與再分配,無疑不太公平,很難充分發揮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
[1]郭劍川.CPI波動與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指數化調整[J].商業時代,2010,(21):82-84.
[2]常耀華.我國個人所得稅改革問題研究[D].河南大學,2011.
[3]趙娜.個人所得稅制改革研究[D].吉林大學,2012.
[4]中國統計年鑒,2011.
[5]楊斌.論確定個人所得稅工薪所得綜合費用扣除標準的原則和方法[J].涉外稅務,2006,(1):9-15.
[6]周全林.從稅收公平角度看我國個人所得稅制的全面改革[J].當代財經 2010(11):26-35.
[7]劉軒.我國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和稅率設計問題研究[D].保定:河北大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