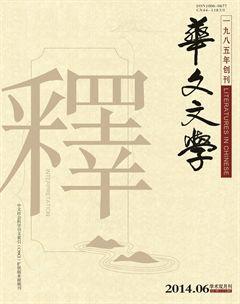歸來的“另類”藝術
歐陽昱 關偉
關偉,1957年生于北京,1986年畢業于首都師范大學美術系,1989年至1993年先后被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藝術學院,堪培拉國立大學藝術學院和悉尼現代藝術中心邀請為客座藝術家。在這之后多次獲得澳大利亞政府藝術基金,包括2008~2010年度澳大利亞政府頒發的最高榮譽藝術基金。2008年在北京建立工作室,此后參與了多項有影響的中澳藝術交流活動,現生活、工作于北京和悉尼。關偉的作品在復雜的象征性繪畫符號中,有力地體現了當今社會、環境的兩重性。他的作品是他豐富的文化儲備,對社會、政治的高度關注,以及他對藝術史的廣博知識的產物。關偉曾在世界各地舉辦了超過50屆個人展覽,如何香凝美術館OCT當代藝術中心“魔咒-關偉2011”;同時還應邀參加了許多重要的當代國際藝術展,如2009年第十屆哈瓦那雙年展。
歐陽昱作為澳大利亞臥龍崗大學“Globalizing Australian Literature”(澳大利亞文學全球化)項目博士后研究員,曾為該項目而于2010年3月18日在北京天倫王朝飯店,以中文采訪了關偉,后譯成英文,此為梁余晶的中文回譯。
歸來:機遇與挑戰
歐:關偉你好,我好像曾采訪過你,那是你在墨爾本做駐地畫家的時候,對不對?
關:對對對。
歐:你現在回到北京了,現在你好像有個重大的戰略轉移,為什么這樣呢?
關:這個有很多原因,我就說幾個主要的吧。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過去跟我合作多年的雪門(Sherman)畫廊從08年開始變成了基金會,從這之后它便不代理藝術家了。我和它一起合作了差不多有十五六年吧。它不代理藝術家,我就沒有畫廊合作了,所以相對來說就比較自由。雪門和我解除了這種畫廊合作的關系,正好我也想開辟一個新的空間,所以決定回中國,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歐:這個地方打斷一下,據我所知,澳洲有些華人畫家都有好幾個畫廊,你可以留在澳洲,再轉一個畫廊。為什么一定要回中國呢?
關:是可以轉好幾個畫廊,但是由于我跟雪門畫廊的關系太深了,像是一個家庭,關系特別好。即使再找別的畫廊,也不可能達到那種關系。我跟雪門畫廊之間能夠互相信任,合作多年,有種很深的感情。當它變成了基金會,不代理藝術家之后,我一方面是有點失落,另一方面,也感到了某種自由,可以去找另外的空間。后來我也找了一個,在悉尼,叫卡利曼(Kaliman)畫廊,去年做了一次個展。所以,這是最重要的原因。再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這幾年的當代藝術發展得非常快,而且朝氣蓬勃,受世界關注的程度要遠高于澳大利亞,并且很多藝術家的作品很有意思。市場各方面也都比較好,這也是一個吸引我回來的原因。因為我每年都回來,每年都看到一些朋友有很大的變化,這就是我回來的部分原因。還有一點,就是有朋友給我推薦了一個很大的工作室,有四五百平方米,而且很便宜,這也特別吸引我回來用這么大一個空間,因為在澳洲不可能有這么大的空間。中國還有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各種材料都比較便宜。再有,就是我太太的父母比較老了,她也需要回來照顧幾年。再就是希望小孩學點漢語,讓他回來上學。我在澳洲已經20年了,各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績,挪個地方也是理所當然的。諸多因素考慮起來,就決定08年回來。
歐:08年什么時候?
關:08年三月,開辟一個新的空間,新的市場,新的機遇,也有很大的挑戰。
歐:什么樣的挑戰?
關:挑戰就是,因為我離開中國20年了,有好幾代新人藝術家都起來了,所以你回來,你就變成了一個新人。好像是白手起家,但不完全是白手起家,因為畢竟在澳洲有一定基礎了。所以,你到這兒來是為了尋找新的商機,還有新的刺激創作的源泉。畢竟,我在澳洲待了很長時間,所以對中國各方面的發展很關注,覺得很有意思,想尋找新的創作元素和刺激。
歐:這是不是意味著你的創作題材與過去在澳洲相比要有所變化了?
關:對,這也是我特別渴望的,這也是一種挑戰,因為我畢竟在澳洲那么多年了,形成了很固定的一個風格。如果沒有很大的刺激和變化,可能還會沿著那個走,我覺得也不具有挑戰性。所以,我回來以后,變了新的空間,一種未知的東西,可能會帶給我新的東西,在我的創作中有些新的變化,這也是我渴望的。
歐:你在澳洲創作了很多和移民有關的,以及澳中兩國歷史互相交錯的作品。我知道,這些作品在澳洲有展出,有收藏,那么這些作品原來或是你這次回來之后在中國有沒有展出?
關:在中國有部分展出。我當時到中國來,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在奧運會的時候,有個展覽公司看中了我在06年和07年在動力博物館做的關于鄭和的“另一種歷史”,他們特別喜歡這個。
歐:Secret Histories?
關:不是,叫Other Histories。他們想把我這個變成奧運的一個項目,當時就給我定在六七月份做一個大型展覽。
歐:他們對這個理解嗎?
關:因為是中國人。他們當時想借助文化來弘揚中國的國力強盛,也想借助文化來作為促進。鄭和正好又是一個中國人走向世界,開放世界,和平崛起(的象征),他們是為了配合這個。所以他們希望我搞這個展覽。我回來的時候,就帶著我的全套助手。
歐:是重新干還是把那個拿過來?
關:重新干。
歐:按照他們的思路搞一個?
關:對,因為那個是針對澳大利亞的,主要是鄭和發現澳洲。回來干的這個,我野心更大,不光是發現澳洲,還發現南美,發現了非洲世界。
歐:所以這是一個更大的項目。
關:對。但由于種種原因,這個項目由于經費問題,由于行政管理的官僚問題,也由于(我)對中國不了解,最后七扯八扯,展覽沒有做成。
歐:本來是應該由中國出資讓你做的?
關:本來他們公司要出資的,我自己出一部分資,然后再找些贊助什么的。
歐:但是沒到位?
關:最后都沒有到位,這是其中一個因素。再一個因素就是他們在宣傳等各方面都很滯后,比如畫冊,最后都沒有落實。種種原因,最后這個展覽就沒有做,作品我都做出來了。部分作品在別的聯展里展覽過一些,但大型的這個最后沒有實施成。
歐:這是不是也屬于你剛才說的挑戰,回到中國這個文化里,也是一種挑戰,對吧?
關:這是沒有料到的一種挑戰。回來后的兩年時間里,我遇到的挑戰非常大,其中有幾個挑戰特別有意思。我08年回來,正好趕上奧運會。奧運過了以后,到九十月份時,馬上就是經濟危機。受影響非常大,不光是我個人,而且整個藝術界的作品市場各方面一落千丈。
歐:所謂“一落千丈”就是沒什么買家了?
關:對。所以,我回來后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大型展覽沒有做成。第二個挑戰就是經濟危機。
歐:對不起,這里打斷一下。你說的買家是指中國買家還是海外的?主要是海外的嗎?
關:主要是海外的,也包括中國的。
歐:中外買家雙方在比例上各占多少?
關:三七開吧,差不多。70%是國外的,30%是中國的。
歐:那中國的比例還是比較大的。
關:是的,中國現在也開始有些買家了。
歐:受影響是兩方都影響,還是只影響國外的?
關:雙方都有影響。然后,經濟危機完了以后,我在工作室剛干了一年半,現在就面臨著整個的拆遷。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投入了很多的錢。現在,等于那些錢都打水漂了。
歐:哦,你投錢是做什么?
關:建工作室啊,你得裝修啊,蓋房子啊之類的。
歐:這耗資大嗎?
關:耗資當然很大了。哪怕是便宜,也有不少耗資。現在那邊已經變成一片廢墟了,我又找了一個新地方。
歐:那就是說之前白搞了。
關:對,那個就白搞了,也沒有賠償。我又搞了個新地方。
歐:是什么原因?經濟原因還是政治原因?
關:這是國家政策的問題,有點政治因素,因為朝陽區有個統一政策,要消滅農村,把整個朝陽區都變成一個公園什么的。朝陽區包含部分農村和城鄉結合部。我們的地方就在城鄉結合部,因為便宜。當時我們不太了解,那些農民占的地都是些非法的地。現在國家要收回,雖然我們和房東簽了十年合同,但等于就是一張廢紙。當時我們不知道這些。現在國家要把這地收回,它要賠償一些,但不賠償我們這些客戶,而是賠償房東。所以最后我們什么錢都損失了,顆粒無收。這個事不光是我個人,而是牽涉到上千個藝術家。這些藝術家還在抗爭,在絕食。最大的事是,已經上長安街游行了。在兩會之前,有幾個人跑長安街去了。這事已經鬧得很大了。但我們屬于比較不愿意找麻煩的,說不行,就自動退出了,因為你也沒有精力時間去跟它去耗去鬧。接著,由于經濟危機的原因,跟我合作的一家新的畫廊最后也因為拆遷的問題而倒閉了,就是不再做了。
歐:是個澳洲畫廊?
關:是韓國的一個畫廊,它退守韓國,把北京的畫廊放棄了。我和它有合作,有安排展覽,因為這個事,也沒有了。所以,自從我回來以后,面臨了很多挑戰。
歐:這些挑戰都是沒有想到的。
關:都沒有預見,都沒有想到。都是很大的挑戰。但我從這些挑戰中學到了很多東西,覺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說,你不知道在中國會發生什么事情。正是因為在中國不知道發生什么事情,才覺得它有意思,才好玩。因為你經歷了這種種磨難,比如自己找地方,自己蓋房子,找什么建筑隊,跟人怎么訂這些東西,能學到很多東西,這和澳洲那種一成不變的、很安逸的狀態完全是兩回事。
歐:但是你不覺得這樣的耗費會影響你的創作嗎?
關:當然會有一些影響,但從中也學到了很多新的經驗,可能會帶到我下一步創作之中去。盡管有諸多挑戰和不便,但也有很多方便的地方。好的地方,一是材料便宜,做作品也相對比較便宜,人工也便宜。比如雇人、雇助手都比較便宜,包括我用工作室也比在澳洲便宜。在澳洲,用這些錢不可能租一個像現在這么大的工作室。所以,還是有好的因素。另外,我有一幫過去的老朋友,經常在一塊聚。我們互相切磋,互相展覽,互相提攜。
歐:這種情況在澳洲沒有嗎?
關:在澳洲也有,但我覺得在澳洲沒有這么頻繁,我們一星期都聚幾次,一塊游泳,吃飯,聊天,切磋,等等。在那邊,基本上都是自己干自己的,然后定期展覽。這邊的話,只要你愿意,每天都能參加活動。所以我特別忙。
歐:你實際上情況是,你的全家都已經搬遷回來了。
關:嗯。
歐:你現在在澳洲和在中國的時間大概是怎樣分配的?是每年都不回去了,還是?
關:我每年都回去。現在,我在那邊仍然保持著工作室,還有家,還有車,全套的東西。
歐:但是個空巢。
關:對,都空了。助手在那住。
歐:哦,你還有助手。
關:對,助手現在住我那兒看房。我把車給他,他住我的房子里。我差不多一年回去三次吧。 歐:每次待多長時間?
關:回去待的時間都比較短,差不多是二比十吧,兩個月在那邊,十個月在這邊。因為我仍然沒有放棄在澳洲的展覽機會、市場等等,我在那邊已經比較根深蒂固了。所以在那邊我每年定期做兩次或一次個展,然后參加一些聯展,一些活動,還有什么講座啊,出版啊,等等,仍然很頻繁的。
澳洲華人藝術的另類
歐:雖然你剛才說的那個大項目后來流產,但你原來在澳洲的那些作品在這邊辦過個展沒有?我是說,拿回來辦。
關:我07年辦過一個,在北京辦的,那時我還沒回來。
歐:用的什么作品?
關:是我在澳洲做的作品。回來以后,沒在中國辦過個展,但我在澳洲辦了一次個展,在香港辦了一次。可能明年吧,要辦一次比較大型的個展。
歐:2007年的個展是第一次,是吧?
關:不是,之前有過三四次了吧。
歐:你這些以澳洲題材為主的作品在國內賣得怎么樣?反映怎么樣?他們看得懂嗎?
關:他們現在基本上把我看成一個澳洲背景的藝術家,因為我作品里有很強的澳洲符號和信息,比如像難民啊,移民啊,水啊,星座啊,地圖啊,完全是澳洲的那一套。
歐:還有土著啊,還有——
關:對。他們對我的作品怎么看,我也了解了一下。他們把我看成是比較另類的作品,比較新奇,沒見過,中國藝術家圈子里沒有人搞過像我這類的作品,也算是比較獨特吧,但不屬于他們主流。主流里是流行另一種符號。雖然我的畫和澳洲相關,但也包含中國元素,表現出某種另類的特色。
歐:他們主流里的“另一種符號”是指什么?就是這里為主流的東西。
關:比如說,就像F4(該詞指四位藝術家:張曉剛、岳敏君、王廣義和方力鈞——歐陽昱注),就是大頭啊,張著嘴笑啊,有種政治波普的性質。這是前幾年比較流行的,現在可能就很多樣了,因為跟國際上聯系很密切,這幾年中國藝術的發展也很快。有很多你也看不出有特別強的中國符號特色。現在也在轉變,跟世界接軌,等等。但我的作品還是比較獨特和另類的。
歐:雖然你說你比較獨特,但據我所知,還有一批到美國、到歐洲,比如美國的徐冰、蔡國強等等,這些人擺在一起,他們(中國觀眾)怎么看?因為這是八十年末以后出去的一大批,散居在世界各地。
關:把我放在海外集團里面看,我仍然算比較另類的。為什么另類?因為徐冰也好,谷文達也好,蔡國強也好,這些藝術家仍然還是用中國元素在做。比如,徐冰始終在用文字的東西,現在還是用。他在國外時,不管他做假英文書也好,天書也好,基本還是用中國文化里面很強的元素,如書法、文字等等。蔡國強用炸藥來炸,谷文達用燈籠,用中國燈籠做的裝置,等等。基本上,他們還是沿著中國符號在走。但我完全變成了一種澳洲化的東西,脫離了中國,雖然還有中國元素。一眼看去,還是中國藝術家的東西。我特別想強調的是,當時在澳洲,我就想讓澳洲觀眾了解我,我關注的也是在澳洲周邊發生的事情。非常澳化。所以,在“澳洲幫”藝術家里面,我也是澳化程度最高的,因為我表現的是他們周邊發生的事情。回到中國以后,感覺上仍然是比較另類和獨特的。
歐:那么,你這樣一種另類和獨特是否會影響你的銷售情況?是銷售更好,還是使它受到影響?
關:我發現,在澳洲的時候,因為我的作品不是很市場化和大眾化的,有很深的文化背景,涉及歷史、文化和政治因素,所以我的作品始終在小眾里面比較流行,就是精英層面和知識分子層面。收藏我作品的人都是有點修養、有點知識背景的人,這些人對我比較關注,不是那種大眾化的,如炸藥“嘩”的爆炸效果。你必須得有一定的深度,有一定文化背景,才能夠了解我的東西。
歐:那么,這個是針對西方所謂的白人精英,以及少數的華人精英。當這個被搬到中國語境下面后,中國的知識層面、精英層面能夠接受嗎?除了覺得你獨特以外。包括中國這些有錢買畫的人,他們是怎么看待這個東西?我還是在問銷售問題,是會讓他望而卻步,還是獨特到讓他購買欲望很強?
關:基本上,這里跟澳洲有點類似。就是,喜歡的人特別喜歡,不喜歡的就覺得有距離,比較難接受,很多人看不懂。所以,還是在一種小眾的范圍。喜歡的人就覺得好得不得了,追著你要收藏你的作品。但大眾看來,還是有一定難度,你必須給他們解釋。我覺得,受眾得有一個培養的過程。比如,我剛到澳洲的時候,他們對我的作品也是有種距離感,不太理解,但經過我十年、二十年的培養,逐漸就形成了一個群體,慢慢就比較了解了。所以我想,我在中國的轉身,估計也需要五年到十年的一個過程。
歐:對,得有個鋪墊。
關:也得有個鋪墊,慢慢讓大家能夠接受。
歐:據我所知,你在澳洲的培養和成長,還有一個方面,即藝術評論。
關:對。
歐:在這邊有沒有這個東西?
關:在這邊,現在開始有一些了。
歐:以中文寫的藝評?
關:但相對還是沒有在澳洲那邊多,因為我畢竟才剛回來,2008年4月回來,還不到兩年,差不多兩年吧。這兩年之間,我還要去一些其他地方,等等。 歐:我聽說,但我沒看到。當時中央臺給你做了個專訪是吧?
關:對。
歐:是多長時間?半個小時?
關:對,半個小時,放在10臺的人物介紹里面。
歐:是什么時候做的?
關:正好是在我回國前后做的。是這樣的,中央電視臺駐悉尼的一個記者——他們三年一換——這個記者,通過朋友介紹認識了我,對我的作品很感興趣,他本人也是個文化人。后來,追著我三年,就是連著拍了我三年的時間,有了很多素材。
歐:是在這邊和那邊都拍,還是只在澳洲拍?
關:主要是在澳洲拍。他好像是05、06和07這三年駐悉尼。所以包括了我一些大型活動,包括“另一種歷史”,還有給墨爾本做的那些大型壁畫——
歐:氣象局的那個。
關:對,對。還有些講座等等。他都抓拍了。
歐:錄像還是攝影?
關:電視。正好他結束了在澳洲的三年,就換崗了。他回來后,就把這些素材剪成了一個片子,剪成了個名人的欄目,在10臺播出了。10臺放了后,4臺又把它裁成兩集,他們有個欄目叫“世界華人”,又在那里面放了。所以,這正好在我回國前后,是個很好的鋪墊。很多人就知道了有這樣一個藝術家。
歐:好像我記得,去年還是前年,大使館搞了個“還鄉團”。那是個展覽,對嗎?
關:對對對。
歐: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你能不能講一下?你是在里面?
關:是的,我在里面,而且還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個澳洲的女策展人,叫凱瑟琳(Catherine Croll——歐陽昱注),她通過申請得到了一筆錢,最早是在悉尼做了個展覽,叫“從毛到現在”(From Mao to Now)。
歐:是90年還是91年?
關:不不不,是2008年。
歐:這么晚?
關:對,就這兩年的事。
歐:哦,原來有個“毛走向波普”(Mao Goes Pop)。
關:不是那個,那個是93年的。
歐:那就很早了。
關:對。這個是2008年的。
歐:你也在其中?
關:我沒在,因為我已經回來了。她找了我,但沒找到。很多人都參加了她的展覽。然后,去年,她經過重新安排,裁掉一些人,又找了些人,把這展覽又給弄回來了。
歐:她是個獨立策展人嗎?
關:獨立策展人。我幫了她,給她推薦了很多藝術家,像肖魯,就是開槍的那個。
歐:哦,就是原來的那個星星(畫展)的。
關:不是,她是中國第一次當代大展里面的。
歐:哦,那個女的,對著電話亭開槍的那個。
關:對對,她也在澳洲。她在澳洲待了八九年吧,但很早就回來了。她現在還是澳洲公民。她和唐宋是兩口子,但現在已經分開了。
歐:而且她本人也不搞了。
關:還搞,她現在還搞。
歐:還搞行為藝術嗎?
關:對,她搞了好多行為藝術等等。所以,我把她也推薦到這個展覽里了。還有我的幾個助手,像熹發(楊熹發——歐陽昱注)、金沙——
歐:金沙是策展人吧?
關:對,他不是這個展覽的策展人,而是“中間”(Midway)的,在臥龍崗。把這些人也給她介紹了,還給了她一些意見。所以,去年,搞了個“還鄉”的展覽。
歐:一共有多少人?
關:一共好像有40個人吧,差不多37個人。
歐:都是跟澳洲有關的?
關:基本上都是,像王志遠、熹發、金沙、郭健、鄧忠等等很多。
歐:鄧忠?他跟澳洲有關系嗎?
關:他現在還在澳洲,住在古爾本(Goulbourne)。他最早是搞繪畫的。后來退出了,搞動畫去了,然后又回國了,現在又搞當代雕塑。我把他也推薦了。
歐:“中間”好像有他?
關:“中間”沒有他。
歐:“中間”有幾個名字我很生疏。
關:沈少民。
歐:沈少民我知道。這次他也來了嗎?
關:對,“還鄉”里面有他。幾乎這些人都網羅進來了。
繪畫、文學與閱讀
歐:你剛才提到,你繪畫的題材涉及文化、歷史,甚至涉及天文地理。但是,你唯獨一點沒有提到,比如說文學,一點沒提到。文學,你的繪畫題材里面有涉及嗎?
關:其實,我那些繪畫里面有很重的文學色彩。有很多澳洲評論把我的作品稱為“敘事”(narrative),就是有情節的繪畫。
歐:敘事的。
關:是的,敘事的。我的繪畫里基本上都有故事。有故事,有情節,這就跟文學比較接近了。這是第一點。再有一點就是,我創作的來源和動機,有很多都是從文學里吸取營養。
歐:比如說?
關:比如說“另一種歷史”。在02年時,我偶爾看到了一篇文章,講的是席孟斯,英國的那個艦長,《1421》的作者。當時他的那本書還沒出來。
歐:孟席斯,Menzies。
關:對,孟席斯,Menzies。后來那本書出來了。我就找到了那本,讀了一遍。
歐:英文的?
關:對,先是英文的。后來又出了中文版翻譯。
歐:你把英文和中文版都看了?
關:對,都看了,后來主要是看中文版,當然我還讀了很多中國人寫的關于鄭和的資料。其中我記得有個作者叫祝勇,跟咱們年齡差不多,寫過很多其他的東西,像故宮等等。
歐:也就是你參考了這些相關的東西。
關:對,我就讀了他們這些,不能算文學小說,應該是歷史方面的東西。這就是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其中,我還讀了很多其他東西,因為我比較喜歡看書,看書比較雜。
歐:你看的書主要是哪些方面的?
關:有政治的,有歷史的,有文化方面的,等等。
歐:在你閱讀的種類里,小說、詩歌、散文、戲劇,你觸不觸及?
關:觸及啊,觸及。
歐:占的比重多少?
關:小說差不多能占百分之三四十吧。比如,最近我讀了很多,讀了《項塔蘭》(Shantaram),講一個罪犯逃跑的,一本很大眾化的流行小說。
歐:你看的是英文還是中文?
關:我看的都是中文的。
歐:這些都有中文譯本了?
關:都有。這是我最近讀的,很厚,這么厚,寫的是印度的一些傳奇,挺好玩的。去年年底,還看了一本小說,叫《傳信人》(The Messenger)。
歐:噢。The Messenger, by Zusak, Markus Zusak(《傳信人》,作者馬克斯·蘇薩克)。
關:對對對。那本也不錯,結構什么的都不錯。挺有意思的。
歐:你看的好像都屬于暢銷書類。那么,嚴肅的文學你觸不觸及?比如說,亞歷克西斯·賴特(Alexis Wright)的書,得了大獎的那本。
關:得獎的那本現在沒有翻譯。
歐:我是說,以前的。
關:基本上,我讀書的范圍都是翻譯的,因為我讀英文比較費勁。
歐:以前的有翻譯過,比如得大獎的《祖先游戲》這些。
關:那本我翻過,但沒有完全細讀。好像你給過我一本。
歐:對,我給過你一本,是臺灣版的。
關:我一般比較關注澳洲人寫的東西。我讀了《傳信人》,還讀了一本叫《香料傳奇》(Spice: The History of a Temptation,作者Jack Turner——歐陽昱注),是本歷史書,講的是發現香料,大航海,找胡椒之類的。
歐:我也翻譯過一本,是英國人寫的。
關:哦,是嗎?
歐:也是關于香料,香料的歷史。
關:我始終對航海和文化交流、互相交融比較感興趣。這些都是跟澳洲有關系的。所以我讀的書比較雜。
歐:詩歌方面呢?
關:詩歌方面相對讀得比較少,真讀得不多。我主要是讀一些歷史、文化方面的,還有小說。我覺得,流行小說也能給你一些新的啟發,如當代發生什么事情,或流行一種什么樣式,或大眾關注、喜歡什么,對我的創作都有些幫助。我還讀過一本,我的朋友夏兒寫的《望鶴蘭》。
歐:哦,那個,寫藝術家的。你覺得那本怎么樣?
關:我覺得文筆還行。我覺得還行,還能讀,讀著還挺順,一下就讀完了。而且里面寫的都是我(在現實中)知道的事。
歐:這么說,華人關于澳洲的作品你也看。
關:因為都是他們送給我的,我沒事就隨手翻一翻。夏兒送我的這本書,我隨手一翻,就整個兒讀下來了。
歐:夏兒這個人你認識?
關:她就是我們街坊嘛。
歐:北京人?
關:她不是北京人,在悉尼我們住一起。她先生是那個叫什么Simon的,中國人,名字叫史雙元,經常搞些文化交流項目。
歐:你是說墨爾本的那個?
關:不不,悉尼的,史雙元,在SBS老講些關于中國文化或其他東西的講座。史雙元和黃惟群,等等。
歐:哦,是他們一批的,文人。
關:我跟他們這些人關系都挺好。他們有些東西,我也讀一讀。還包括什么海鷗。
歐:劉海鷗。
關:對,劉海鷗,她不是出過一本叫——
歐:《她們沒有愛情》?
關:不,不是那個,她自己單本的,標題好像叫《海鷗飛翔》,就是些小雜文之類的。我讀了,也還行,都是我周邊,就是這段歷史發生的事。我就順著也都看下來了。而且,從今年六月開始,是中澳文化年,哦不,是澳中文化年。
歐:是中國定的還是澳洲定的?
關:澳洲定的。今年是澳中文化年,明年是中澳文化年。但它是從六月開始。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是澳中,后年的六月到再后年六月是中澳。我現在回來后,使館文化處,包括大使,就把我吸收到他們那個committee(委員會)里面了,算是個顧問吧,各個活動我都參與。我也積極地給他們提些建議什么的。我還特意把中國駐澳洲的文學家的email(電郵)都給了咱們的文化參贊,讓他們關注這個弱勢群體,因為他們畢竟寫的都是澳洲,但卻以中文的面目出現,在國內出版的。他很感興趣,想看看是否能做些事情,包括趙川之類的作家。澳中文化年分成幾大塊,其中有世界藝術。我前兩天剛開會,就這星期一,在使館搞了個簽字儀式,互換文本。堪培拉的museum(博物館),國家博物館,今年6月10號要舉行一個大型的原住民展覽,攬括了92件作品,這算是一個開幕項目的展覽。還有表演戲劇方面是一大塊,包括賈佩琳的《潘金蓮》。現在不叫《潘金蓮》,因為中國不同意,就改名叫《情怨》了,這名字不好。
歐:為什么不同意?這是她用英文寫的一個劇本是吧?
關:對,她用英文寫的,別人翻譯成了中文。也算是文化節的一個項目。
歐:為什么中國政府要把這題目刪掉?有什么原因嗎?
關:這我不太清楚。我只聽賈佩琳講,“潘金蓮”可能是太敏感了,容易讓人想到色情方面。所以改得稍微文雅一點,叫《情怨》。還有一些項目,比如舞蹈、表演和文學等等,還有個電影節。
歐:他們投入了多少?從錢的方面來說。
關:錢投入不是很多,可能一兩百萬吧。還得拉贊助,因為這是個很大的活動。有很多展覽,包括一個攝影展,牽涉到多媒體方面。但我主要在視覺藝術領域這塊給他們提建議,比如選一些藝術家,土著的陳設方式等等。回來以后,我的角色很自覺就變成了個跟澳洲關系密切的聯絡人,中澳文化之間的一個搭橋人。
歐:或者協調員,coordinator。
關:對。我就是這么個角色。他們一有展覽就來找我,給他們一點意見之類的。
歐:剛才談到閱讀,再補充一點。你的閱讀包不包括藝評,包不包括藝術理論方面的東西?
關:藝術理論方面,我基本上就是讀一些雜志,中國的幾個比較重要的雜志,比如《藝術當代》,一個比較嚴肅、學術性的雜志,經常有些對中國當代藝術的批評和評價,還有對具體藝術家,對世界潮流、亞洲身份之類的討論,都是比較嚴肅的。
歐:你覺得對你有幫助嗎?
關:當然還是有些幫助的。回來以后,我讀得比較雜。我最近讀的包括亞歷克西斯·賴特寫我的一篇文章,關于鄭和的。其實我跟她認識。這次來一見面,有本雜志翻譯了她新的那本書,叫什么什么海灣(Carpentaria,中文名《卡彭塔利亞灣》——歐陽昱注),翻譯是李什么。
歐:李堯,他送了我一本,那里面有個節選。
關:對,我看的就是節選,有點像史詩、寓言。她給我寫的那篇文章也是這種風格的。
近期藝術活動
歐:從你閱讀中國的藝評雜志來看,你覺得他們對澳洲的藝術關注嗎?還是著眼點主要放在歐美?
關:主要還是歐美。在整個世界大的藝術與文學格局里面,澳洲相對還是比較弱勢的一個角色。但是,中國人對澳洲的藝術、文化不是很了解,可能是澳洲地理、政治各方面的因素,它的位置感覺還是比較遙遠。而且(澳洲)經濟、國力各方面不像美國、歐洲那么強大,所以文藝跟這些角色都是相輔相成的。畢竟,澳洲很年輕,才200多年歷史,它的文化藝術方面還沒有一個獨特的、很清晰的面貌,不像美國,有什么“垮掉的一代”,在藝術領域有什么波普,抽象表現主義等等,已經形成了美國獨特的一些東西,中國比較容易接受。而你要說個澳洲的什么東西,幾乎沒有,不管是在文學還是在藝術里面,澳洲都沒有一個獨特的畫派或文學流派。但可能有幾個人,個別的人,像懷特,得過諾貝爾獎之后才開始受人關注。在視覺藝術領域,可能也就那么一兩個人,參加過國際大展后,中國人開始關注了。但整體來說,還是比較弱。但這里面有一點好,就是中國人對澳洲的感情,與歐美相比,相對近一些,這是我這些年觀察和體會到的。當我和朋友談到澳洲的時候,他們都有種友好的感覺,這可能和澳洲的角色有關。在中國還沒有和歐美建立良好關系時,澳洲仿佛是中間的一座橋梁。因為它既有西方的社會體制,給人的感覺又比較隨和。尤其是在霍克-基廷(Hawke-Keating)時期,我們和澳洲的關系很近。當時在澳洲有所謂的三年展,在昆士蘭,亞太當代藝術三年展(Asia-Pacific Triennial),影響很大。
歐:今年又有一個。
關:對,今年是第六屆了。
歐:今年你參加了嗎?
關:今年我沒參加。我參加過第二屆和第三屆。在90年代和2000年的前半段,影響比較大。但隨著事情的發展,現在亞洲的雙年展和三年展特別多,像什么光州啊,光中國就有好幾個,像上海、北京和廣州。然后,韓國還有好幾個。
歐:打斷一下,在光州,你是作為澳洲藝術家還是中國藝術家?
關:我是代表澳洲。一直代表澳洲。現在又有了很多雙年展和三年展,APT相比之下就比較弱了,但它一開始起到的帶頭作用還是很重要的。中國藝術界的圈子里對澳洲還是有種友好感情的。不是特別重視,但也不煩,就是覺得還挺好。就是這么一種狀態。
歐:你剛才談到了韓國的光州,我記得你最近又去了一趟古巴。你能否談談古巴是怎么回事?
關:古巴這個也比較有意思,我仍然是代表澳洲。
歐:是政府之間的行為嗎?
關:對,是政府之間的行為。我是代表澳大利亞去參加古巴的雙年展。
歐:哦,古巴也有雙年展?
關:對,古巴也有。而且是加勒比海很重要的一個展覽。
歐:已經持續多久了?
關:這是第十屆了。
歐:這是你第一次去參加,代表澳洲政府。
關:對。
歐:你一個人去還是帶了一批助手?
關:我帶了兩個助手,楊熹發和金沙。澳洲選中的藝術家可能有四個吧。
歐:華人只有你一個。
關:對。
歐:做什么呢?
關:我給他們做了個大型的繪畫裝置。
歐:叫什么名字?
關:叫《升起的海平線》,關注溫室效應,大氣變化,海島被淹等等,因為古巴本身就是個海島,面臨被淹沒的危險。所以是個帶有寓言和想象性的作品,包括影像、裝置和繪畫,一個綜合性的展示。
歐:你是做好了帶去還是直接現場做?
關:我2007年在坎貝爾頓(Campbelltown)美術館做了這樣一個。
歐:是不是我們那次在新南威爾士畫廊里,有茄子、沙之類的?
關:不,不是那個。那個是99年,這個是07年。
歐:是同樣的題目?
關:是同樣的題目,但作了些更改。因為環境不一樣,內容有些小的變化,但大的方面沒有變化。他們正好選中了我的作品,讓我重新再呈現一遍。
歐:這個再呈現是拿到那邊去再呈現?
關:到那邊現場畫。畫完,展覽完,就除掉了。 歐:你實際上現在根本就不動手畫了。你有兩個助手,等你有了方案,他們就照你的方案去做,是吧?你也參與其中。
關:我當然得參與其中。我現在是發展成一個團隊了。
歐:這個團隊多大?可以大到多大?
關:大可以有六個人。
歐:哦,平時常用的就是兩個。
關:對。沒有大項目的時候,就我一個人搞些方案設計。我接了一個大項目后,先是自己設計,把整個東西都想好了。然后,在實施的時候,我讓助手來幫我,因為太大了,我自己沒法做,沒那么多精力。
歐:好像你搞大項目是從氣象局開始的。
關:對,那是03年。
歐:從04年開始?
關:不是04年,準確說是從03年,我參加了一個柏林的澳大利亞當代藝術展,是澳洲和德國的一個文化互動交流項目。他們選中了我,那是第一次,我給他們做了個壁畫,在墻上畫。我做了一個《澳洲之行》,畫的是很多難民船,很多人游泳,沖向澳大利亞,當時正好發生了那個丹麥船的事件。
歐:“坦帕”(Tampa)號,挪威的那個。
關:對,是挪威的。是根據那個事件創作的一個項目。但我直到03年才開始做,當時有兩個助手幫我完成了那個項目。
歐:誰?
關:其中一個是我太太。
歐:哦,你太太也是藝術家。
關:是的。她是跟著我一塊去做的,在當地還找了一兩個助手。當時還不是很專業,想法還比較朦朧。但從04年氣象局的這個開始,我就固定了。當時我用了四個助手。從這開始就有助手了。04年和05年我做了好多大型壁畫。在墨爾本當代藝術中心(MOCA),就是有鐵皮的那地方,我做了個大型壁畫,叫《伊甸園》,和國內的有點像。緊接著在悉尼做了兩個,一個叫《大鼠國》,另一個好像叫《通緝令》。后來每年都會做兩三個,接著就是《另一種歷史》。我帶著四個助手,做了一個月,但之前的設計花了兩年多時間。
歐:古巴那個搞了多久?
關:前后十天吧。
歐:只有十天?那很緊張嘛。
關:對。
歐:那就是你去了以后馬上就干活了。
關:對,到了就干,讓他們事先都作好了準備,墻都蓋好了,底色也涂好了,我們三人到了就開始畫,畫了差不多一個多星期。
歐:古巴你全部跑了一趟還是怎樣?只在哈瓦那? 關:只在哈瓦那。
歐:其他地方都沒去?
關:沒有,時間太緊了,因為要干活。
歐:但你完了后還可以繼續待下去嘛。
關:對,但我們還有別的事情。
歐:哦,還有別的事。說句題外話,古巴是現在碩果僅存的第二個共產主義國家。古巴和中國現在對比怎么樣?
關:古巴有點像咱們中國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非常窮。商店里的貨架幾乎都是空的,看不見有什么商品。
歐:這是什么時候?
關:去年的三月,一年之前。特別的窮,餐館都很少。古巴人過得很窮。但他們人的狀態還不錯,很樸實,有點像咱們六七十年代。
歐:還是比較happy(快樂)。
關:是的,當然也有對政府不滿的人。總之,屬于比較滯后的社會狀況。
歐:電信的發展呢?比如說,你要發email(電郵)怎么樣呢?
關:也有,但很慢很不方便。手機也不太靈。哈哈哈哈哈哈。
歐:哈哈哈哈哈哈。
關:跟朝鮮差不多。
歐:但你沒去過朝鮮。
關:我沒去,但我通過讀書和想象,可能差不多。
歐:你是89年還是90年到的澳洲?
關:我89年先去了一趟。
歐:哦對,到塔斯馬尼亞。
關:是的。
個人經歷與創作理念
歐:現在從89到99,哦不,到2009,已經有二十年了。那么這二十年的移民歷程,實際上你是有點再移民的感覺,因為你又回來了。回來后,你和澳洲的關系基本上是10比2這樣的比例,兩個月在那,十個月在這。這二十年,從你作為藝術家的角度,能不能作一個概括?
關:我給自己也總結了一個說法。我在澳洲二十年,是我認識澳洲和澳洲人認識我這樣一個雙向的過程。在我的創作方面和被澳洲人認可的方面,大約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國階段。因為我這樣中國背景的人去了以后,不可能馬上變成澳洲人,要有個過程。這就是中國階段。第二階段是關注生態的階段。我94年回來后,感覺到一個大的對比,澳洲空氣很干凈,中國就是個大工地,亂哄哄的,所以我很自覺就關注生態。第三階段就是關注難民和移民的階段。第四階段就是關注澳洲的政治和歷史方面的階段。同時,在這四個階段,我有不同的命名。剛開始我去的時候,澳洲人管我叫中國藝術家。過了一段時間,在第二階段,給我取名是中國-澳大利亞藝術家。第三階段,是澳大利亞-中國藝術家。到了我臨回來之前的那會兒,基本都把我看成是澳洲藝術家了。這四個名稱正好吻合我四個階段的創作,第一時期是帶有中國背景的,第二時期關注生態,這有點澳洲特色了,逐漸在演變,然后關注移民和難民,這是個澳洲-中國的時期。最后,關注澳洲歷史等等,索性就以澳洲藝術家的身份參加很多國際大展,都把我看成是澳洲藝術家了。那天在使館的時候,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和咱們的大使在聊。范迪安就說,關偉在那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們把他看成是澳大利亞藝術家,但又是中國藝術家,結果大使說,我們把他看成是我們澳洲的藝術家。所以這里有種很微妙的關系在里頭。
歐:在這整個過程中,你跟美國的徐冰他們有點不同,他們這么多年一直都使用中國的材料,中國的主題,中國藝術主流的東西。但你是有意想與其脫節還是怎樣?因為你整個的走向是越來越澳化,越來越深入它那個文化里去。
關:對。
歐:在中間,你的題材上好像極少與中國發生聯系。是有意的嗎?
關:可以說是在有意和無意之間吧,也有這么個過程,涉及到我認識澳洲和如何認識澳洲。我剛到澳洲時,帶著我最早在中國的這批作品,如人體穴位、中國文字,中國符號很強的這些東西。我發現澳洲人接受起來比較難,雖然他們也很喜歡。畢竟,人性還是共通的。但還是覺得有些距離。作品有太強的中國文化背景,他們接受起來就有一定的難度。我當時就作了一個大的戰略判斷,我在澳洲能做什么。當時我一個人在塔斯馬尼亞,就在思考這個問題。我作了一個分析,我把澳洲看成一個大的實驗地。第一,澳洲跨兩大文化之間,亞洲和西方,你同時能看到兩大文化的面貌。然后,在兩者之間你能做什么呢?你能找到一個點,有個橫軸和一個縱軸。落到澳洲本土上,可以借鑒這兩大文化中有特色的、優點的東西。然后,(當你認識到之后)歸到表現澳洲的一些特色。當時我做了這樣一大判斷,這是我的角色,要往這個方向去發展。同時,我又結合自己的一些因素,給自己作了定位,即我的繪畫要追求三要素,第一是幽默,第二是要有知識背景,第三是智慧。這三點是我給自己找的一個創作框架。所謂幽默,我是指自己本人有滿族背景;包括老舍、王朔都有這個背景。
歐:王朔也是滿人?
關:對。他有個綽號叫完顏王,或完顏朔。對,他也是滿人。滿人從血液里講是八旗子弟,有種游手好閑的傳統,喜歡玩。包括我,受父親的影響很大。他喜歡唱京戲,對事情看得開,有種游樂人生的感覺。這是結合我本人。再有,我發現澳洲人也有種幽默性,對幽默的東西很感興趣,很容易接受。所以我想應該強調這一點。知識性這點和我喜歡看書,喜歡思考有關。我針對的觀眾是知識分子,受過高等教育的這些人,所以要有一定深度。除了看上去好看之外,還得有些知識信息在里頭。這是我考慮的第二點。第三點,所謂的智慧性,當時處在后現代、后殖民這樣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你了解的信息非常多,有時完全就在于你怎樣去選擇這些信息。比如,你要選一個伊斯蘭的圖像,你在電腦上或各種雜志畫冊上都能看到。但你怎樣把這些東西巧妙的組織起來,這就需要很高的智慧。你在選擇和表現的時候需要很強的智慧。知識、幽默和智慧:這三者是互相關聯的。我把自己定位以后,分析了澳洲的地理位置,我能做什么,又給自己定了這樣的三要素,后來——
歐:你說的定位,是你現在的總結,還是真的原來你就已經意識到了?
關:我原來就定下了。
歐:是什么時候?
關:是92年左右定的。
歐:哦,92年時你就想好了這個,然后就按照制定的路線走下去了?
關:對,非常清晰地往下走。當時我第二次去澳洲的時候,是我一個人去的。
歐:你說一個人,就是沒帶家人?
關:不是這意思。第一次我們去的時候,是通過Zhou Si的展覽介紹。
歐:是有政府資助的?
關:是的。是三個人去的。
歐:哪三個人?
關:我、林春巖和阿仙。我們一起到塔斯馬尼亞作了個短期的訪問,兩個月。
歐:兩個月就回來了?
關:對。兩個月訪問回來后,等到第二次的時候,因為我在那邊做得比較成功,教授比較賞識我。當時他給我的評語是,你是中國超現實主義第一人,評價非常高了。他在一篇文章里面寫到,我是“十億中的一個”,佼佼者。
歐:誰寫的?
關:杰夫·帕爾(Geoff Parr),當時塔斯馬尼亞藝術學院的校長和教授。我比較幸運的是,之后他又給我發了個邀請,給我申請到了一筆錢,有一萬塊。當時有三個人,一個是當代藝術館的副館長伯妮斯·墨菲(Bernice Murphy),還有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他們給澳大利亞藝術委員會寫了封信,特批了一萬塊錢,邀請我再度回到塔斯馬尼亞,錢就放在塔斯馬尼亞。所以我第二次回去的時候,就是我一個人,那兩個藝術家沒有去了。家屬也沒去,只身一人去的。作為單個的藝術家,只有一個人,不像三個人在的時候,還可以互相交流。
歐:當時你去的時候,像你這樣身份的中國藝術家很少吧?
關:很少。據我所知,以訪問藝術家身份去的,比較純粹點的,可以拿錢的,可能就我一人。其他可能有名義上這樣,實際上不是的。
歐:街頭賣藝的?
關:對,但官方邀請的、拿錢的就我一個。到了那兒后,就我一個人,要在那待一年。當時也沒想過要留在那兒。后來發生了一些事情,當時也是比較失落,就想到留在那兒。我本身不是難民或政治身份,我的身份是訪問學者。但在情緒上面,我想到,當時中國的環境很差,我很失落,對它各個方面很失望,所以我也有點想逃避,有一種流放的心態。
歐:你也有這樣的心態。
關:當然了,這是整個大環境的影響。所以,雖然不是實際上的難民,但卻是一種精神上的流放。
歐:正好我想起了一個詞。我們這一批,無論是文人還是藝術家,現在西方有個術語,叫做“天安門一代人”,或者“后天安門一代人”。
關:對,對。
歐:你對這個怎么看?你把自己歸入這一術語的范圍嗎?
關:其實我覺得,西方人認識中國,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標簽,其實實際個案都不太一樣。但他們認識中國,尤其是剛開放以后,西方認識中國,都是通過政治層面去認識的。比如說,最清晰的就是“毛走向波普”那個展覽,就是中國的政治波普、新的流行、通過毛來消費的政治符號等等,所以它起的名字也叫“毛走向波普”。雖然我參加了那個展覽,但我的作品在里面就跟政治沒什么關系。我當時解構的是西方的那套文化體系,我把西方的一些icon,像維納斯、杜尚的便壺,加以解構和嘲笑,玩弄幽默,跟“從毛到波普”沒什么關系。但他們這樣認識我,把我劃為“天安門一代”,我也沒辦法。其實也挺無奈的,他們總是從政治角度來認識你。這是他們的第一步。到了第二步,才發現你的作品里面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這是后話。但他們認識你的時候,必須把你放到一個大的框架之下,先整體有個面貌,再去一點一點認識你。我昨天還接到SBS給我發的一個邀請,要做一個采訪。
歐:是電視臺還是電臺?
關:電視臺。在92年給我做過一個采訪,和難民有關的,他們還把我劃入難民這一塊,其實我又不是難民。現在二十多年后,他們想重新做這么個項目,做三個人,唐宋、肖魯和我。他們給我發邀請,說若干年后,想把這節目再做一遍,看看這些人現在有些什么變化。他們想派個人過來做這事。所以他們還是有這個概念在那里。我在這方面就比較隨意吧。你這么認識的話,也可以,但我會給你解釋清楚,我有一種自己的認識,我有自己的特點。我跟那個有些關系,但又不是特別相關。
“多元互化”與文學發展
歐:我現在手上拿著你2010年澳大利亞文學周的東西。據你說,你去過兩次,雖然不是受邀,因為它是文學周。你作為一個藝術家,對文學還是很關注的,對吧?你去的時候,看到那里有其他的澳洲華人藝術家嗎?
關:有一些,因為現在我們回到澳洲以后(我認為他是想說中國——歐陽昱注),使館起到了一種聯絡的作用,成了和澳洲發生關系的平臺。所以,基本上使館有什么文化活動,它都會把有澳洲背景的藝術家和其他相關的人請過去,參加它的活動。尤其是我,我和大使關系不錯,因為他喜歡藝術。我和文化參贊關系也很好。
歐:現在的文化參贊是誰?
關:是個女的,叫喬(Jo)。
歐:是華人嗎?
關:不是。
歐:原來的那個是華人。
關:現在不是了,現在這個是澳洲人。
歐:喬(Jo)是吧?
關:不是,是吉爾(Jill),她中文講得很好,老公是個西安人。她也去過我那兒玩。很多中國藝術家都參與了,澳洲使館就像是個紐帶,把這些藝術家都聯絡在一起。只要有聚會或活動,大家都會去。像08年的時候,還有一個展覽,叫什么來著,是澳洲一個女的策劃的,叫歐美林。
歐:她是?
關:周思的前妻。
歐:我見過這個人。
關:英文名叫Madeline(瑪德琳)什么的。她其實不是策展人,但也在做這個事。她是為陸克文(Kevin Rudd)策劃的這么個展覽,陸給她開幕,是在08年。
歐:不是“還鄉團”那個?
關:不,在“還鄉團”之前,這個叫做“意縱天高”。
歐:這是誰取的名字?很怪嘛。
關:陶步思(Bruce Doar)起的名字。老陶。
歐:哦,Bruce Doar,Bruce Doar。
關:這個展覽就在使館里面舉辦的。
歐:我好像去過這個。
關:我這都有圖片,如果你明天去我那,我可以給你看,包括“還鄉”、“意縱天高”和“中間”,我都可以給你看看。
歐:“中間”我有。我到臥龍崗去看的時候買了一本。你覺得它這個文學節舉辦得怎樣?受眾多嗎?
關:范圍還是挺小的。但它舉辦了很多活動,因為它和大學有些交流。然后那兒還有個點,叫書蟲,那里有很多講座,主要是一幫老外在那,而且賣好多英文書。
歐:它不是面向中國的大眾。
關:對,主要是賣英文書。除非是那些外語學院的,或是對英文有一定了解的中國人才會去。
歐:有什么影響嗎?媒體怎么樣?
關:還是在圈子里面有一定影響,小圈子里面,對大眾的影響比較小。
歐:媒體呢?比如說各大報、電視臺、廣播電臺?有報道嗎?
關:有些報道,但不是大眾性質的,也是比較小眾的。他們還去了成都,和成都那邊有些交流什么的。
歐:哦,成都也有個書蟲。還有蘇州,三地都有。
關:不過,我問艾弗(Ivor Indyk),他們接觸了很多出版商,給他們推薦翻譯一些書。也有些接觸。但現在平面媒體,包括文學,普遍都已很邊緣化了,被電視、互聯網擠壓。讀書的人很少。詩歌就更邊緣了。你是搞這個的,肯定很熟悉,是不是?甭說文學,現在連報紙,都已經比較邊緣化了。現在大家基本都在互聯網上看,信息很快,節奏也快。
歐:你說的是中國的情況還是澳洲的?
關:這可能是一普遍現象。我有個朋友是搞平面媒體的,在報社工作。他覺得,現在平面廣告和平面報紙的發行量在逐漸縮減,不像過去那幾年影響大了,現在幾乎都被互聯網、手機短信這些所取代了。所以,現在討論文學,不光是澳洲,中國文學界也是面臨著很嚴峻的被邊緣化的問題。那天,在寫作節上,中國還去了一個作家,叫閻連科。我和他聊了幾句,他的感慨也是,真的嚴肅文學讀者很少。而且現在中國又很浮躁,很少有人能靜下心來踏踏實實地搞這個,幾乎都被商業所沖擊,去掙錢。哪有那種踏踏實實做學問的人?現在的人都浮躁得不得了。
歐:尤其是中國。
關:尤其是中國。關鍵是,在中國商業浪潮這個大背景的沖擊下,哪怕你是做學問的人,也會多少受到影響。因為你在和朋友聊天的話題里面,都是誰掙了多少錢,比如誰拍賣拍了多少錢,又在哪里買了一棟別墅。
歐:哈哈哈!
關:又換了什么車。幾乎都是跟經濟方面有關的事情。
歐:從這一方面來講,這20年,你應該還是不錯的吧?
關:哈哈哈,起碼還算中等吧,還能過。
歐:中產階級,中等偏上。
關:差不多是這么個狀況。
歐:20年來,你是澳華藝術家中的佼佼者,或是佼佼者之一。這20年中發生了一個大變遷,大轉移,一個文化大轉移。那么你對整個澳華藝術界怎么看?
關:這是個挺大的項目。我覺得,還是不要把它放在澳華的框架里,而是把它放在個人的框架里,因為我突出的,還是我個人的東西。但是,要是從整體上看,像剛才你提到的,“天安門一代”也好,“天安門前”、“天安門后”也好,別人給你定位的時候可能會把你放在澳華的圈子里,但我想突顯的還是我個人的東西。我在澳洲待了二十年,然后回到中國,我有意無意地想承擔一個角色。什么角色呢?就是有點像你說的澳華這樣一個角色,即作為一個使者,這是我獨有的背景。比如說,我是中國出生,在北京土生土長,在澳洲待了20年,現在又回中國了。有這種背景的人不是很多。我正想利用這種背景,在我的藝術中創造出比較獨特的東西來。前些日子,我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一個詞,叫“多元互化”。這好像是個新詞。
歐:多元互換?
關:多元互化。
歐:什么意思?
關:我的理解,它意思是,我們現在是多元文化,比如說在澳洲,有華人群體,有伊斯蘭群體,有不同國家的混合群體,大家都住在一起,互相之間有種文化融合。
歐:不是“多元文化”,而是“多元互化”。
關:對,強調的是后面那一點。
歐:是中國人提出的,還是西方人提出的?
關:我好像記得,作者是個英國學者(后來關偉通過電郵告我,是費爾南多·奧蒂斯[Fernando Ortiz],經本人查證,奧蒂斯提出了所謂的“transculturation”,這也許就是關偉所說的“多元互化”——歐陽昱注)。20多年前提出了這么個觀點,但被大家忽略了。
歐:英文是怎么說的?
關:我忘了。他寫過一本書,我記在另外一個本子上了。
歐:這個英國作者叫什么名字?
關:想不起來了,但“多元互化”強調的是后一點。互化之后,產生了新東西,創造了新東西,這個新東西在互化之中成長,形成了新的文化。過去,可能有兩種互化,比如基督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現在,這圈子越來越小,互化越來越大,可能會產生很多的網狀性的東西,打破后殖民的觀念,即中心-邊緣的結構,成為一種多元互化的狀態。
歐:無所謂誰是中心,誰是邊緣了。
關:對,和后殖民那種結構不同。我對這個很感興趣。加上我的角色具有兩種文化背景,就很自覺地去找這個,去研究這個,去表現這個。我最近在研究這種歷史。比如,我很關注傳教士。他們最早來到中國,通過基督教來影響中國人。他們通過詭計影響中國高層,試圖滲透中國老百姓,使基督教得以發展。
歐:這不僅限于澳洲了。
關:對,不僅是澳洲,包括整個西方文明。在中國,通過像利瑪竇(Matteo Ricci)這樣的傳教士,把中國的信息帶回西方。像布萊尼斯(無法找到此人,后來關偉說是普尼哥,一個在中國的波蘭傳教士,但無法找到他的英文名或波蘭文名。——歐陽昱注),像伏爾泰(Voltaire)都對中國特別感興趣。他們沒有來過中國,但他們把想象里中國的東西變成了法蘭西文化一部分,當時洛可可(Rococo)的一部分。反過來,洛可可又從法國回到了中國清代,變成了圓明園的一種精神。通過互化,產生出了很不一樣的東西。我現在就是對這種互化的東西特別感興趣。比如說,我研究地圖的演變,一開始他們想象東方怎樣,西方怎樣。現在,我自覺把自己的角色站在移民藝術家的背景上,不是狹義的中國到澳洲的移民。我把這種移民看成了城市和鄉村的移民。比如說,很多人跑到城市里來,這也是一種移民。當然你去海外,這是一種移民。包括在本國互相走動,這本身就是一種流動的影響。而且現在這種藝術家很多。如果你到中國某個藝術家群落里一看,不是這個拿了澳洲綠卡,就是那個持有美國護照或英國護照,現在有很多。因為這20年中國發展比較快,大部分海龜幾乎都回來了。還有一些像我這樣,兩邊來回跑。
歐:你剛才說的,大部分“海龜”回來了。長期生活在國外,那里政治氣候相對是比較寬容的。你回來以后,作為一個藝術家,會不會覺得在政治上有壓力或限制?比如說,剛才談到的,《潘金蓮》這個書名就被換掉了。會不會觸及這方面的東西?
關:相比20多年前,現在還是寬松、開放了很多。那個時期真是很壓抑,很緊張的。現在,只要你不威脅到這個政治體制,幾乎什么都可以做。在我整個發展過程中,雖然我關心一些政治,但我表現出的東西又是人文性質的,根本不會觸及到它的底線。其實說穿了,藝術的東西能跟政治抗衡嗎?根本不可能。它只能是一種慢慢的滲透。
歐:除非是那種搞口號的,根本就是為了推翻政府的。
關:其實說穿了,從根本上,文學藝術這些都不重要,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生的思考,是這類東西,精神方面的東西。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在中國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自由,愛做什么就做什么。當然,這里有種底線,比如像這次拆遷,你要是真讓我去天安門游行,我可能不會去。因為如果你去了,可能今后你的簽證會有問題。
歐:你現在的簽證是一年一次,還是?
關:一年多次往返。
歐:每年還要續簽一次,是吧?
關:對,就是說我每三個月要出去一趟。
歐:現在要求是這樣的?
關:對啊。你只能待90天。當然對我來說,我基本90天就得出去一次了,不一定去澳洲。比如去年,我去了臺灣、古巴等等。今年我又得去美國、波蘭等等。反正我出去一趟再回來就行了。
歐:不能申請一個中國的永久居留嗎(PR)?
關:沒有。現在中國好像還沒有。你指的是“特殊貢獻”那種是吧,即在中國待了若干年以后,對中國有特殊貢獻的?那樣可以申請,但卡得很嚴。
歐:哦,還有個技術上的問題。
關:對,沒有像澳洲那么自由。
歐:你現在回來以后有什么打算?藝術方面的。
關:一個打算就是我剛才跟你談的,關于“多元互化”。
歐:我是說具體的,比如你要搞大的裝置或繪畫,藝術上的。
關:具體的嘛,我可能明年在深圳的當代藝術中心會做一個大型的展覽。
歐:這是有資助的,還是自己干?
關:有些資助,但可能不會很多。
歐:來自澳洲?
關:本地美術館會有些資助。但都是非商業性的。這是我比較大的一個項目。今年嘛,我的發展會是一種多樣性的,不光是平面,我已經做了很多雕塑了。我還可能會做一些其他材料,比如說多媒體、照片,不光是純繪畫,還有一些裝置。這可能是今后我要發展的一個方向。
歐:多向度的。
關:對。
歐:那么,我的訪談基本上要結束了。最后一個問題。你剛才談到文學,因為多媒體、網絡的出現,使它處于一種萎縮、邊緣化的狀態。我們現在在做一個澳大利亞全球化的項目,它如何在中國、日本、印度這幾個國家推廣。就你個人作為藝術家的角度來看,你在這方面有什么建議和意見?即澳洲政府需要做什么工作,能夠促使它繁榮,尤其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
關:我覺得,像文化這種東西,該做必須還得做,做的方式有兩種。一種就是大眾化的,比如出版流行小說。另一種就是比較學術性的,像現在(中國)每年一次的作家節。我的意思是,這兩方面都需要去做,一個是大眾的,翻譯澳洲流行小說,等等,讓大眾都來了解澳洲當代文學。另一方面,學術性的也要做,提升它本身的檔次。其實我覺得,這種影響還是會有的,不管形勢怎樣,哪怕當代中國很浮躁,哪怕澳洲在世界文化中處于弱勢地位。但慢慢地發展,事情還是(會好的)。比如說,與20多年前相比,澳洲的特征就更不清楚,更模糊了。當時,我個人來說,我可能就知道一個人:懷特,根本不知道其他人。但是,通過一個懷特,哪怕只影響到一個人,這個人就會對澳洲產生很不一樣的想法。如果你影響到了一個比較重要的人,或是一個知識分子群體的話,就有可能帶動很多其他的人。從這些人開始慢慢地影響,有一個滲透的過程。需要時間,而且需要機遇,比如世界有個大的轉變。現在中國和澳洲的經濟又非常密切,像鐵礦石等等,澳洲在中國的貿易往來中占的比重越來越大。有很多人也更加關注澳洲的文學藝術。所以我建議,雙向都要去做。而且,我還有一個建議,要多關注一些中國在澳洲的作家,像夏兒、趙川,還有你,因為你沒有語言障礙,比較容易進入他們的領域,你可以用英文寫作。但是,大部分移民作家,他們不能用英文寫作,進入不了。能不能組織一些人,把他們在澳洲20年的經歷譯成英文,回到澳洲去,讓澳洲人了解這個群體發生的一些事情,我覺得這也挺有意義的。這等于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他們的影響都是在中國,因為他們的作品是在中國出版,讓中國人看的,沒有反饋到澳洲去。當時我還給他們介紹過,像黃惟群和艾弗,我把他倆約過來,讓他們見面。他不是有個叫《燙》(Heat)的雜志嗎?我想讓他們發表些東西。但后來,可能是翻譯的問題,最后也沒成。但我想,這個弱勢群體應該可以建議政府和他們坐下來談談,可能對澳洲文學也是比較有意義的一種影響。
歐:好,非常感謝你抽出寶貴時間到這來接受采訪。
關:我很高興。
歐:關偉,這篇采訪已經距今大約3年了,從那時到現在,你有一些什么新的動向和發展,能大致談一下嗎?
關:現在已經適應了悉尼,北京兩邊住的生活方式,除了在藝術表現形式上拓展了雕塑,陶瓷,多媒體,壁畫裝置,等等。還更多的參與了各種中澳文化交流活動。我覺得現在的身份不只是單單一個藝術家了,還肩負著中澳文化交流使者的使命了。
(責任編輯:黃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