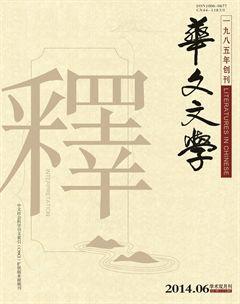訪問余光中先生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長大后,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
這首廣為流傳的詩作使詩人和散文家余光中的名字聞名世界。
余光中,一生從事著詩歌、散文、評論、翻譯“四度空間”的寫作,現已出版詩集、散文集、評論集、翻譯50多種,且在每一度空間里都成績斐然,出類拔萃。詩壇的桂冠、散文的重鎮、批評的睿智、優秀的翻譯,所有這一切怎能不讓人羨慕、驚嘆?2014年4月,余先生應邀至澳,成為澳門大學駐校作家,和澳門開始一個月的“蜜月”之旅。在“蜜月”開始之初,余先生以《旅行與文化》為大家奉獻了自己幾十年來的經驗心得,并舉辦了詩歌朗誦會和大家一起讀詩、品詩,共同感受詩歌的魅力。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余光中先生,特別就一些大家共同關心的話題采訪余先生。
張麗鳳(下文簡稱“張”):與您獲得的若干榮譽相比,您如何看待澳門大學授予的榮譽學位,以及如何看待澳門大學對您的評價?
余光中(下文簡稱“余”):這也是一份榮譽,是我第四次得到榮譽博士學位。最早一次是2003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距今已經10年了。而今再次得到澳門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這表示學術界對我的認可,也是一種鼓勵和榮譽。我的寫作仍然在繼續,并沒有枯竭。我和澳門大學之間也并不是毫無淵源,早在姚偉彬校長在任時,就來澳門大學演講過,當時演講的題目是《詩與音樂》。
在被授予博士榮譽學位時,澳門大學的評價多是溢美之詞。但是可能因為時間關系,頒發學位時,我的有些成績沒有充分展開。其實,除了詩歌,我還在散文方面著墨甚多,有十幾本散文集,我曾經說過詩與散文,等于雙目,兩者并存才可以呈現立體的世界,我經常說“雙目合,視乃得”,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詩歌是我最早涉獵的文類,而今我在翻譯、詩歌、散文、評論等各方面沒有偏廢。
張:對于社會上對您為“鄉愁”詩人的定位,您感受如何?是欣然接受還是有所保留?
余:對于“鄉愁”詩人的定位,一則是喜,一則遺憾。《鄉愁》寫的比較短,格律簡單,容易背誦,被選入教科書后,散播非常廣。中央電視臺編曲演唱,后來王洛賓、關牧村、羅大佑等十幾位譜曲演唱,使得“鄉愁”這個名片越來越被世人所矚目。但是就是這張名片,把臉給遮住了,即定位雖然也貼切,但是卻狹窄了些。比如后來我有很多寫環保的詩歌,卻難以涵蓋其中。
張:漢語新詩在世界文學格局中,如何獲得較高的地位,較廣泛的影響?您對漢語新詩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性如何理解?
余:現在漢語新詩在國際上的地位還不很高,也不普及。漢語詩歌在國際上的地位不是一定的。比如中國古典詩歌,就有漢學家們在研究,并列入到了中國文學的課程。漢語新詩就是“五四”以來的白話漢詩,發展了還不到100年的時間,100年放在文學史上來看是很短的。如今在英語霸權當道的現實條件下,中文作為世界三大語言之一,在世界上有三千萬的人使用,實際上還不算多,因此漢語的使用也談不上廣。隨著華文的傳播,可能漢語新詩會越來越被認識,傳播得也會更廣些。
至于諾貝爾文學獎,北島就曾錯過兩次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并不具有標準作用,其之所以備受矚目,是因為這個獎宣傳性大,是由瑞典王室舉辦,因而顯得更隆重,不像由政府舉辦的獎項,會鼓吹政治意義。即便是這樣,我認為這個獎仍然是“西方文學獎”,而不是“世界文學獎”。我們必須意識到漢語翻譯成英文是非常困難的,不像其它歐洲語系、拉丁語系等,相互轉換起來比較容易。泰戈爾之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很大一部份原因是他用英文寫作。所以我們對于諾貝爾文學獎不必太在意,不要一廂情愿地去提倡并將之作為唯一標準。
張:漢語新文學、漢語新詩是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提出的概念,它可以將現當代文學、臺港澳文學、海外華文文學一體化,不分中心邊緣。對此,您有怎樣的評價?
余:這種提法在教學、研究方面確實有較強的整合力,有利于消除中心和邊緣的界限,全面地把握研究狀況。但是我并不都認可,因為在習慣上,和漢語相對應的是回語、藏語等。不在中國使用的往往才稱為“華語”,而在國內日常生活中用則稱為“普通話”。“華語”不會產生政治聯想,華文則可以在全世界用。所以如果是在學術研究方面使用我沒有什么意見,并覺得這種提法很有道理,但是在日常使用中則不十分贊同。尤其是在新文學開創時期,胡適也只是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就沒有這樣使用。
張:您在創作、翻譯、評論方面都有卓著的成績,那么您對中文寫作最獨到的感觸是什么?對于初學者又有哪些建議?
余:中文是非常優美的文字,我比較看重舊小說介乎文言和白話之間的那份文辭之美,注重文字本身的美,而不刻意追求故事,是中文寫作時應該注意的問題。而對文學初寫者來說,剛寫詩歌時不要感嘆人生,不寫哲理,而寫個人的、家庭的情感。詩要由一個主題、思念、感情,靠具體的形象表達出來。比如曹植的《七步詩》,正是用看得見的具體的東西,把握看不見的情緒的最佳案例。意象和節奏是詩歌表達的兩大重點,學生不妨從鍛煉操縱意象開始。
在不知不覺中,陽臺上已有了夕陽的光影,一看時間才知和余先生的訪談已經有一個半多小時。在澳門,不管先生走到哪里,都會被人認出,并被請求簽名、合影以留念。由此可知,說先生享譽海內外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的確名副其實。當然,先生在詩歌、散文、翻譯、評論各個方面做出的成績難以論高低,鄉愁的詩歌寫作也并不能呈現詩人詩歌的全貌,但“鄉愁詩人”稱號的確被人們記住,因為那纏綿悱惻的《鄉愁》和《鄉愁四韻》觸到了所有海內外的游子的溫情。我們只希望像詩人自己期望的,能在關注他鄉愁詩的同時,看到他在詩歌中表現的更大的情懷及更廣闊的視野,也能留意到他在詩歌之外的文學成績。
(責任編輯:黃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