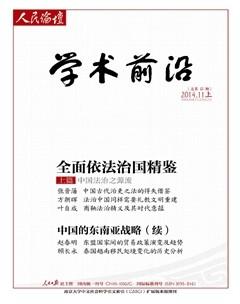中國古代治吏之法的得失借鑒
2014-12-26 04:18:59張晉藩楊靜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2014年21期
張晉藩+楊靜
【摘要】在發揮官吏才干與預防官吏貪邪的問題上,古代社會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古代治吏思想在漢朝儒法合流中完成了依禮治吏與依法治吏的融合并趨于定型,在德禮與刑罰并用的主張下倡導依法治吏。中國古代治吏之法嚴密周翔,使得依法治吏的基本環節有章可循。法律的權威與效能不僅在于制定,更在于施行。治吏貴在以法為尊。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要治民更要治官。健全官吏控制模式,建立長效激勵機制有利于保障吏治清明。
【關鍵詞】權力 ?明主治吏不治民 ? 法治 ?人治 ?依法治吏
【中圖分類號】D092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治國必先治吏。選賢任能,擇錄為官被中國歷朝歷代視為治國理政的關鍵。為了維護自身的政治與經濟利益,歷代統治者都比較重視吏治,以使江山萬世一系,國祚綿長。如何保證擔任公職的官吏克制自己的權力欲,不為權力所腐蝕,清正為官。如何保障官吏發揮治國理政的才能,嚴格執行國家的政策方針、法律制度,廉明為政?這些歷來都是當政者關心的問題,也是歷代思想家論著的焦點問題。
中國古代關于治吏的思想理論
對于國家而言,官吏是執掌兵刑錢谷等重要領域的重要工具。關于提高統治效能與建設清明吏治,歷代思想家與政治家多有論著,形成了一系列理論。吏治思想經歷了依禮治吏與依法治吏的論爭、交融與定型,在禮法并用、教化與刑責并重的主流思想下形成了依法治吏的吏治理論,“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觀點獲得了普遍的認同。……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