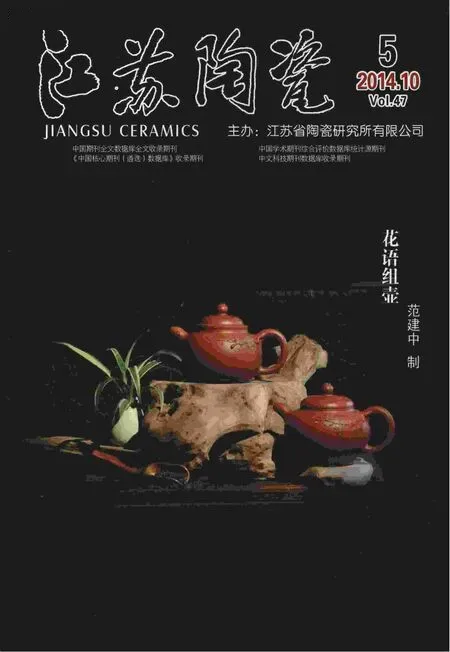偕自然共和諧,隨生活安喜樂——以“南瓜壺”為例淺談花器藝術內涵
何 震
(宜興 214221)
宜興紫砂聲揚海外,名承千古。早在春秋時期,越國大夫范蠡扶越滅吳之后,便偕西施歸隱于黃龍山麓的一個小村莊,并結合當地興旺的制陶業,加以研制改革,大力發展起制陶產業,被后世陶工尊為陶業祖師,稱為“陶朱公”、“造缸先師”。隨著時間的積淀,歷代各種文化藝術的逐漸滲透,紫砂業逐漸壯大,成為宜興地域一大標志性產業,并籍著各方文人愛好者的介入,逐漸成為一門別具一格的藝術形式。據資料顯示,及至明、清時期,宜興紫砂名家輩出,其產品暢銷國內外,日本也以紫砂為珍品而來中國學習制壺技術。除此之外,宜興紫砂茶壺更與中國茶葉同銷歐洲,成為歐洲制壺的藍本。宜興紫砂的發展成就,一時間蔚為壯觀。
紫砂作為飲茶器皿,不僅在保溫性、透氣性上堪稱上品,紫砂壺器本身的藝術性也是值得反復把玩和品味的。在此,就花器中典型的壺器類型——“南瓜壺”(見圖1),淺要談談宜興紫砂給人帶來的審美享受,進而一探紫砂壺器潛藏的深邃的藝術魅力和藝術價值。

圖1 南瓜壺
通俗的劃分,紫砂可分為“光器”和“花器”。光器通常簡單古樸、拙雅大方,譬如《詩經》里端然正宗的中原正聲、宗祀祭曲,顯得端莊高蹈,凜然不可侵犯。相比較而言,花器因其式樣繁復、品種多樣,且大多以農家生活、尋常景物入型,便更像是《詩經》里的“國風”,顯得平易隨和,更貼近日常生活,廣受普通大眾的喜愛。譬如供春的“樹癭壺”,表現了一個實實在在的自然物體;“風卷葵壺”,表現了一種特有的自然現象;“魚化龍壺”,給予人們一個美麗的傳說;“松竹梅壺”,則體現了人們高雅的追求。朱可心老人的“報春壺”,以“心”形為體,梅干為嘴,壺身嫩枝曲伸,梅花朵朵,更是一幅形象的報春圖。這些紫砂花器中的代表作,生動地再現了中華民族的生活畫卷,充分說明了傳統的紫砂花器深深地扎根于民間生活,是最貼近民族文化根源的一種存在。而“南瓜壺”便是中華民族文化中熱愛生活、崇尚自然這一思想意識的藝術體現。
從取型上看,“南瓜壺”的取型可謂是人民生活中最普遍尋常的事物之一。“南瓜壺”,歷史上又稱“東陵瓜壺”,據《史記·蕭相國世家》載:“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可見,南瓜很早以來就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幾乎隨處可見、并具有極高美譽的農作物;我國大部分地區都有栽種,不僅營養豐富、栽種簡單,而且無論蒸、煮、烹、炸,都鮮美可口,是人們日常餐桌上最尋常的食物之一。西方的萬圣節更是掏去其內部瓜囊,刻成人面形,在里面點蠟燭,制成詭秘的南瓜燈,作為裝飾品。故而,無論中外,南瓜都是人們生活中所喜聞樂見的物品。“南瓜壺”取型于南瓜,充分表明了制壺者對生活的洞察和熱愛。
其次,從壺器的制作工藝來看,制壺者大多以模擬南瓜為主,以藤葉變化為輔,充分地體現了他們對生活的尊重和對自然的崇尚。譬如這款“南瓜壺”,壺身圓融作筋紋狀,取南瓜之型,為八瓣依次圓弧起伏,別有韻味;壺把以南瓜藤條為狀,把藤絲擰成筋紋,下內收為把端,上外延成把梢,梢處收縮自然,為藤條枝頭狀;壺嘴以南瓜葉縮圈纏繞而成,葉枝垂落于壺身下方,葉圈皺褶隨意、虛實有致、紋理流暢、起伏有度;壺蓋與南瓜壺身儼然一體,蓋紐取南瓜柄曲折自然、意趣盎然。縱觀整壺,色澤古樸、虛實相間、雕鏤精致、形態逼真,極盡物之形態,堪稱是模擬自然、崇尚本真的優秀之作。
再次,從壺上銘文來看,也洋溢著濃濃的生活氣息。“生于棚,可以羹,制為壺,飲者盧”,取自于經典“瓜婁壺”。瓜婁本是一種葫蘆科圓形瓜類,除瓜可供食用外,瓜子及根可藥用,有寬胸潤肺、化痰清熱的作用。至于“盧”,便是指寫出《七碗茶歌》被譽為“茶仙”的盧仝。全銘寓意為來于自然,又可享于生活,甚至飲者可以成為像盧仝那樣的茶仙。這充分體現了古代士大夫及文人雅士退守田園,每日晨耕晚讀,沉浸于山水田園,盡情享受自然的生活情趣和精神追求。譬如歷史上有名的陶淵明,寧可要“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農家生活,也不愿“為五斗米折腰”的仕宦生涯。
佛教有云:“一花一世界,一鳥一天堂”,每一個看似拙樸簡單的事物里,細細品味,都蘊含著別樣的內涵和魅力。經典的“南瓜壺”里既包含著普通百姓日常生活里的隨緣喜樂,也包含了文人雅士們崇尚自然的生活情趣和自覺的文化追求。譬如早在清代,紫砂名家陳鳴遠便根據東陵瓜的典故制作了一把“南瓜壺”,并題銘“仿得東陵式,盛來雪乳香”。而從歷朝歷代歌詠南瓜的詩歌里也可得知:李嶠詩“欲知東陵味,青門五色瓜”;張炎詞“何如種瓜秫,帶一鋤,歸去隱東陵”。南瓜,常常傳達了一種寧靜悠遠的田園生活。
其實,無論是經典的“南瓜壺”,還是其他如“葵花棱壺”、“梅樁壺”、“束柴三友壺”,“風卷葵”、“魚化龍壺”等,大部分花器都秉承著中華民族對自然的崇尚和對生活的尊重,都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日常的生活習性和最渾厚的文化底蘊。鑒于此,深感作為新時代紫砂從業者的任重而道遠:如何更好地發掘出自然和生活中最具美感的事物和形象,并將之或形象、或抽象地整合到紫砂壺器的創造中,將是新一代紫砂人傾大力而為之的一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