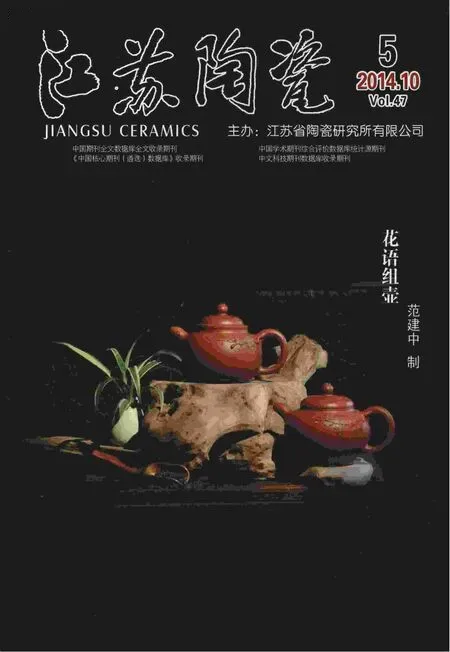淺析紫砂壺“竹鼎”的藝術魅力
李云宏
(宜興 214221)
日本文人奧玄寶在 《茗壺圖錄》一書中評價紫砂茗壺為“溫潤如君子,豪邁如丈夫,風流如詞客,麗嫻如佳人,葆光如隱士,瀟灑如少年,短小如侏儒,樸訥如仁人,飄逸如仙子,廉潔如高士,脫俗如衲子”,正是由于其兼具藝術、實用、人文等多重功能于一身,故而時至今日依然博得世人深愛篤好,是陶都宜興的一張金質“名片”,展現出不凡的藝術魅力。
紫砂壺的藝術魅力表現在諸多方面,變化多樣的造型,豐富精巧的裝飾,寓意深刻的文化內容,恰到好處的跨門類結合等,都是其藝術魅力的組成部分。回歸到不同的壺上,其表現的方式和力度均不盡相同,紫砂壺“竹鼎”(見圖1)以竹之形態及竹文化元素為創作題材,流露出大方端莊的美感和深刻的人文寓意,現以此壺為例,從竹節造型、陶刻裝飾、竹文化內涵等幾方面,分析該壺的藝術魅力。

圖1 竹鼎壺
紫砂陶藝造型豐富、變化無窮,自明代中期以來,歷代能工巧匠不懈創造,使紫砂壺器成為我國陶瓷美術中造型豐富、藝術性極高的一個品種。紫砂壺以造型作為最主要的載體,通過風格各異的形態,展現出紫砂文化深厚的淵源。目前,紫砂茗壺造型主要分為圓器、方器、筋紋器和花器幾大類,其維妙維肖、巧奪天工的風格特色,著實令人喜愛和贊嘆。“竹鼎壺”整體器型端莊穩重、比例協調、結構嚴謹,以竹子的形態為主,經藝術改進和變化,使之更為自然得體。壺身為一段竹節,兩條竹鼓線將壺肩、身筒、壺底巧妙地呈現于一體,身筒略微內收,更具內斂氣質,壺底微向外伸展蔓延,從而使整把壺真正達到穩健的效果;壺蓋切于壺口,子母線規整劃一、嚴絲合縫;立鈕置于蓋頂中央,形態似壺身微縮版,上下對應,風格一致,更顯整體感;壺嘴與壺把前呼后應,均設計成竹節狀,竹鼓線清晰自然,仿佛是由真實的竹子彎折而成,給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覺。從壺嘴處攀伸而出的一小節竹枝,更是靈動生趣,增添了整把壺的自然氣息,小竹枝彎折有力,彰顯著生機之態,一片片纖細的竹葉平貼于壺身一側,形成類似于淺浮雕的立體效果,飄逸之美呼之欲出。整把壺在造型上融合了圓器與花器的形態特征,既圓穩勻正,又施法自然、妙趣生動,滲透著絲絲竹韻,從中流露出山野竹林之趣味,頗具藝術魅力。
紫砂裝飾往往與造型相互配合,對表達主旨、升華意境能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陶刻便是最主要的裝飾技法之一。清代嘉慶年間,由“西泠八大家”之一的陳曼生與藝人楊彭年珠聯璧合,所創制的“曼生壺”便是紫砂技藝與翰墨結緣的精品,從它問世以后,一直備受世人所鐘愛,特別是書畫家愛之如珍寶,“字依壺傳、壺隨字貴”,使“曼生壺”身價倍增,迄今仍為收藏家千金難求的珍品。這把“竹鼎壺”上的陶刻裝飾同樣給人以眼前一亮的感覺,“雨洗娟娟凈,風吹細細香”十字揮灑自如,字體簡約雋永,風格獨特,其大小粗細看似隨意,實則對應情感,妙語若絲,字與字之間的比例,字與壺面的布局協調合理,呈現出匠心獨運的美感。該句語出詩人杜甫《嚴鄭公宅同詠竹》一詩,指雨后每片竹葉都纖柔美麗,風過帶來瑣碎的葉子芬芳,意境優雅,無疑帶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的聯想,將悠悠竹韻更好地帶入了壺中。整壺集造型和篆刻于一體,文切意遠、耐人尋味,使清雅素凈的紫砂茗壺平添幾分詩情畫意,形成獨特的文人壺風格,從而使整器超越了單純茶具的淺層意義,具有極豐富的文化內涵,令人回味深長。
紫砂壺藝是中國重要的工藝門類,它是隨著人們飲茶活動和陶瓷藝術發展到一定程度相結合的產物,可以說,紫砂藝術本身就是一部濃縮而生動的文化全書,因此,紫砂壺的文化性能歷來便備受人們重視,這也是提升整件作品藝術魅力的關鍵所在。竹子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具有廣泛的象征意義,“未出土時先有節,到凌云處尚虛心”的氣節與謙虛,梅、蘭、竹、菊“四君子”的高風亮節,松、竹、梅“歲寒三友”的堅貞友情等,竹文化飽含了中國文人的豐富情懷,是中國君子文化的象征。紫砂壺“竹鼎”無論在造型還是裝飾上,均充分與竹子這一意象結合,其由內而外均滲透著竹文化的深刻韻味,實現了意象與意境的完美搭配,使悠悠竹韻深入人心,展示出深厚的文化元素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