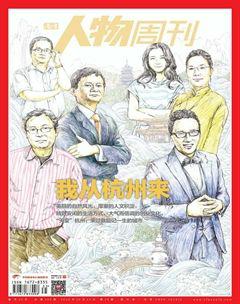李琳 隱匿浮華的自在
李琳到來的時候,沒人發現。雖然大家都在等她。
黑框眼鏡架在一張鄰家姐姐的臉上,長發馬尾攏起,單肩挎包看不出什么質地,灰黑的無肩T恤袖口耷拉在雙臂上,雙手順勢插在褲兜里,笑盈盈地與我們打招呼。
她的現身形式與她所創的服裝品牌——江南布衣之間,有耐看的契合,卻總有距離。她怎么不文藝?她怎么像個公司會計?想起身邊那些“布衣粉”,她們都溫婉踏實,不愿引人注目,可以在人群中與李琳歸到一類。
李琳不愛拋頭露面,每次面對媒體總是扭捏著說:“就是聊聊,別登。”退一步又說:“不拍照啦!”但她又總不善于拒絕。
好像在灰黑色調的掩蓋下,才能實現她的自在。對著鏡頭,她總是渾身不舒服,話語打結。任何重要場合都素顏,一旦黝黑嬌小的身軀躲進黑色保護殼——龐大的奔馳G550里,就淹沒在一片黑色中。此前,大概是她的mopar(編者注:克萊斯勒專屬改裝兼配件制造廠,負責汽車改裝)在杭州的馬路上顯得太特別,她曾換回低調的黑色大吉普。
這哪像一個20年品牌的創始人!你在心里質問,她的笑就化解了這種疑惑:“我喜歡這樣,我設計的第一件衣服也是因為我喜歡這樣穿,而商店里卻買不到。”這種不事經營的創業之心,竟然也能在20年里大行其道。
為自己的設計
“運氣好吧!”李琳反復感嘆運氣,“換成現在,也不過是一家有點風格的淘寶店。”
這是一個隨遇而安的老板,身上幾乎沒有半點“生意人”的痕跡,“這可能是因為我很少管經營的事”——經營大多由其丈夫管理。對江南布衣來說,她是設計師的核心。這從個意義上,她更像個藝術家,卻又沒有所謂“藝術家”的裝腔作勢。
關于穿衣打扮,李琳相信,“每個女孩子都有點自己的心得,我要問你,你肯定也能說出很多你適合穿什么,不適合穿什么,哪些東西你從來不碰,為什么?都這樣。”
李琳最初設計服裝時,“連上面的線我都不懂。”她選擇了對她來說最簡單的方法:圖案。李琳的同學朋友都記得,她做了無數“非常沒有技術含量的花型裙子”:一根橡皮筋勒在腰上,出門的時候一套就穿上了。只因為她小時就喜歡穿,直至我們見面時她依然穿著這樣的裙子,“就這樣,簡單、舒服。”
此后,從印花、設計風格,都是在圖案上下工夫。“比方說繡花會去少數民族地區學習,然后把它改良,但堅決不照搬。”
這位深愛黑色的女子,就像農民愛著土地一樣,深深依賴于黑色給她帶來的安全感,“其實我只是不穿花衣服。”這讓很多人都覺得她不懂穿衣。“其實我是個挺喜歡穿的人,但又不愿太招搖,我的朋友們可能覺得我不在乎穿,但其實我蠻喜歡。”
李琳被認為是環保主義者,但她常想起自己愛開大車的癖好,覺得愧對于此。“剛開始做服裝時,去廣州進面料,很多國產面料用的染料都有一種成分,用了這種染料,其實也便宜,但洗滌后對環境有影響,按德國或歐洲標準,出口是不合格的。不過,不用這個染料,色牢度上面會差一些。”李琳決定全部按歐洲標準執行。對面料,李琳苛求自然,原生態。
“我喜歡的東西是猛看不要太扎眼,但品質要非常好。”在李琳眼中,材料只有兩種:一種是越用越好看,一種是越用越難看。“不經時間的材料,都不是好材料。任何一樣東西經過時間越變越好看,那就是好材料,木頭就是這樣。”
李琳說起江南布衣一位德國設計師的父親,他穿來一件50年的襯衫,袖子已破,但整件襯衫的棉布看上去仍然細膩光潔。“那就是好材料!”看到好材料,李琳總是想拿來“為我所用”。
在服裝行業工作,李琳其實從開始到現在都是為了實現“什么都是自己的”這種占有欲:“都是為了我自己。”她上一次去倫敦看Anthony Gormley的工作室,“他做了很多雕塑鐵塊。”有人告訴李琳,他做的每一具雕塑都是他自己,他是把自己的人體掃描下來了。李琳覺得有意思,“你最了解的還是你自己,要揣測別人蠻難的。”她認定,應該也會有人跟她有同樣需求。
1995年底,李琳設計了第一件外套,接近黑色的灰,面料挺括,穿起來精神。衣服賣得很不錯,她還記得零售價是200元。
李琳開店幾年后,才掙下第一筆10萬元,那是她的第一桶金,她一攢夠就去歐洲旅行了。“開始做生意是沒有錢出來的,錢總是又不夠了,又不夠了……”

“健美褲時代”的異類
李琳是深度旅行愛好者,某種程度上,做生意是為了讓自己行走得更自在。她也在旅行中獲得很多學習機會。
“我有很多不同年齡、尤其是年紀很大的朋友,八九十歲的朋友中老外蠻多的。”這些人都是她在旅途中結識的。“這類人有個共同特點:年齡跟他們沒什么關系,每天還在自我學習。”
旅行是李琳從小就向往的事,真正意義上的旅行直到高中畢業才成行。“我媽帶我去了一趟北京、大連,這是第一次。”第一次就開啟了她旅行的癮。上大學后,只要有空就跑出去,“住同學學校的寢室,各種蹭。那時去南昌玩一趟,就花幾十塊錢。”
這樣的旅行給了李琳全新的人生體驗。“愛旅行的人一般來說都挺寬容,因為見到了各種不同,兼容度會比較好。”
去年,父親幫李琳算了下,一年中有170多天在外旅行。父親并不喜歡她到處亂跑,“他是個焦慮癥患者,最好看見你在眼前,每一天安安穩穩,他就高興了。”
父親是數學老師,為求穩妥,他希望女兒讀一個安穩的職業,出來還能當公務員。那時的李琳“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喜歡什么。比如每天一樣的生活。我爸還希望我當老師,可我不想像他那樣生活”。
“有的事情去做的時候,就知道不是永遠的未來,比如說考大學。”填寫大學志愿,父親要求在李琳填完后,由他加第一志愿:浙江大學化學系。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李琳在家哭了一天,她跟父親說:“我以后干的活,肯定跟化學沒關系。”
她想象不出這個專業跟自己有什么關系,“化學唯一讓人產生點浪漫聯想的,就是巫婆,煉金術。”
李琳當時熱愛的專業是生物,她對生命科學充滿好奇,她至今都是個植物狂熱愛好者,這最終讓她對衣物的面料有了專業見解。她發現:“小時候上過的每一門課都有用,連體育課都有用,當你扛個包要去趕車時,你就覺得跑800米也好有用。”
上了大學,李琳仍不死心,試圖轉系。但轉系的要求是:你得在系里特別特別出色,本專業學得特別優秀,才有機會轉。“那我顯然就不行,我根本不感興趣,所以后來就放棄了。”
讀著不愛的專業,李琳在靜聽內心的呼喚。那是健美褲流行的年代,全中國幾乎人手一條。李琳想:肯定有人和我一樣想穿得跟別人不一樣。
李琳想著自己要穿的衣服,卻買不到,只好四處去淘外貿尾貨,但出口單回來的都是男款。她就用自己的方法配,覺得好玩。“總之,同齡女孩穿的衣服都不是我想要的。”很多年后,同學想起李琳,都會記得她穿得松松垮垮卻與眾不同的樣子來。
1996年,江南布衣創立第三年,她接觸到了山本耀司,“他算是我的一個老師。”每次出國,只要有機會,李琳都會去看他的設計展。她欣賞這位日本設計師,他始終以一個概念貫穿作品,雖然線路很窄,用的顏色也很少,但每一年的作品發布都讓人關注。李琳說:“看他的東西,總感覺到和他的距離,無法超越。”
想象力實驗
將公司管理交與丈夫的李琳,如今往返于工廠和設計師團隊之間。她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小孩是你的老師。”李琳低頭沉思后說。孩子們每天、每一分鐘都在學東西,李琳不停被問:“媽媽這為什么,這是什么,那是什么……”孩子快速地學習,快速地表達,“如果半夜醒來看見你,他第一句話就是:媽媽我愛你!我覺得只有小孩才會這么直接地表達自己。”
孩子也時刻提醒李琳,不要去教化他人。她試圖像大多數年輕媽媽一樣去打扮女兒,但她買不到想給女兒穿的衣服,這促使她開始設計童裝。于是,有了江南布衣的童裝。
待到童裝上市的時候,李琳發現兩歲的女兒開始決定自己要穿什么,孩童的眼睛看不進灰暗的衣服,“她總是更愛色彩鮮艷的,帶有卡通的。”有時為了照顧她的感受時,女兒才會主動說:“媽媽我今天穿了你做的衣服。”理解這一過程,李琳花了點時間。
一次,李琳跟朋友一起打保齡球,認識了兩位中國美術學院的藝術家:耿建翌和張培力。他們很快成為打開李琳視野的重要啟蒙老師。“我的審美是他們倆培養的。”
“他們的對話讓我覺得很有意思,比如說他們聊電影、聊藝術,因為培力做影像,他推薦了好多枯燥的電影,包括伯格曼的,我跟他說我都看得睡著了。他們說,你還太年輕。”十年時間里,李琳跟著他們瘋狂看電影。他們聊天說起一些關于藝術和藝術家的看法,“讓我發現了一個充滿魅力的世界。”
與他們聊天,他們講到有意思處,李琳起初是陌生的,但她回去找書來讀。就這樣李琳在90年代中期讀了很多世界美術史的書,這讓她受益頗深。“他們其實可以做很富有的藝術家,但他們都不在意,我覺得那種品質特別稀罕,有時候甚至感覺到靈魂的高貴。”跟他們打交道的過程中,李琳覺得人真不該在意財富,“他們的很多樂趣完全是另一個層面的,那才有意思。”
此后,以公益的形式,李琳支持這兩位交往二十多年的藝術家朋友辦了“想象力學實驗室”,這也成了江南布衣的藝術中心,希望讓藝術接地氣。“有想象力的人未必是一個專門的藝術家,如果年輕人有想法,沒有人支持,很多東西就消失了。”
這些年,想象力學實驗室贊助了不少年輕人的展覽,以及一些藝術家的創作項目。其中,杭州音樂人李劍紅就是受益人,“我們支持他們一年的生活費,這樣他們可以專心做音樂。”
杭州勞斯萊斯俱樂部的一場藝術講座上,李琳作為嘉賓受邀,她是講座中兩位中國美術學院老師的朋友。
我們的豐田雅力士跟隨她的奔馳G550一路駛入排列著勞斯萊斯的停車場,難免遭遇迎賓小姐的冷眼,李琳從大奔馳上蹦下來的時候,看我們的眼神竟有些憐愛。她歡快地一一介紹,仿佛戲謔地配合一場表演。
在她對兩位老師的藝術設計發表意見時,陸續有幾輛勞斯萊斯在門口停駐,車上相繼下來數位濃妝艷抹、低胸禮服出席的女孩。她們嬌媚地相互打招呼,在會場中央坐下來討論衣著,偶爾嬌嗔,看起來對藝術和李琳的發言并不感興趣。盛妝的她們與黑鏡框、黑T恤、黑膚色的李琳相映成趣。
“受歡迎時,就要擔心了”
人物周刊: 20年里,很多服裝品牌出現又消失,但江南布衣一直都在,剛開始會給我們耳目一新,但后面這種款、型越來越多,雷同也越來越多,怎么來避免?
李琳:這個你沒法避免,服裝行業里頭有一句話,我覺得也算是自我安慰,有人學你說明你成功了。
人物周刊:你在旅途中有過哪些讓自己受益的經歷?
李琳:旅行有很多,主要是看,看展覽也好,博物館也好,肯定是很寶貴的經歷。另外是跟人聊天。
我小時候英語特別不好,大學四級考了三次才過,因為我老覺得那跟我沒什么關系,然后也沒什么學語言的氛圍,后來出國旅行,碰到一些人非常有趣。那個時候我痛恨二手笑聲,因為我得帶個翻譯,人家哈哈一場都笑完了,跟我說什么意思,我就笑第二場。所以就學英語。
人物周刊:這些經歷對你的設計靈感有幫助嗎?
李琳:那肯定很多。我就記得1990年代的時候,我們這里還會覺得穿西裝、再穿雙旅游鞋是件很奇怪的事,但是在那里你會見到一個人就那樣穿,穿得非常好看,那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突然的改變。就會覺得哪有那么多框框,只是自己不會弄而已。
人物周刊:我怎么覺得你創業過程跟玩一樣。(笑)
李琳:我們有很多東西確實都是玩出來的,有時候大家在一起瞎鬧時,發現這樣設計不錯,那是最好玩的。
人物周刊:總有壓力呀,來自哪里?
李琳:我不太有。以前公司年年增長都很快,我經常跟他們說,應該要有危機感。有的款式,原來我一直覺得蠻超前的,人家老覺得你太前衛了,他不買的。當突然變得很受歡迎時,就意味著你已經變成主流了,這時候就要擔心了。
人物周刊:很多人做東西就是要讓大眾接受,為什么你不是?
李琳:我不是刻意要做一個東西讓大眾不接受。但我就覺得,當你的東西太受歡迎時,是要問一下自己,還有什么領先的地方嗎?如果都沒有,品牌就要擔心了。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杭州這座城市的氣質?“江南布衣”最初的設計有受到城市氣質的影響嗎?
李琳:杭州是座溫暖而積極的城市。至于個人設計,我不太相信地域說,我的愛好也比較龐雜。
人物周刊:作為土生土長的杭州人,你的城市地域風格明顯嗎?
李琳:我是杭州人,雖然后來游歷了很多地方,但還是挺喜歡周圍的杭州朋友和同學的。但總體上說,人的個性應該和教育、閱讀、旅行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