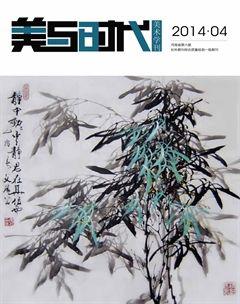凱綏·珂勒惠支對(duì)中國(guó)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的影響
摘要:凱綏·珂勒惠支是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版畫(huà)家,其作品反映了無(wú)產(chǎn)階級(jí)的生活和斗爭(zhēng),最早由魯迅引進(jìn)中國(guó),其作品在創(chuàng)作思想內(nèi)容及表現(xiàn)技法上,深深地影響了20世紀(jì)30年代的進(jìn)步木刻青年,間接地推動(dòng)了中國(guó)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的發(fā)展。中國(guó)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可以說(shuō)是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與蘇聯(lián)現(xiàn)實(shí)主義結(jié)合的產(chǎn)物。作品流露出的那份對(duì)生活在戰(zhàn)亂年代生活困頓民眾的深切同情,及反壓迫反侵略的抗?fàn)幘瘢鼓究虜[脫了傳統(tǒng)的附屬狀態(tài)。雖技藝提高尚有空間,但作品滿(mǎn)是純粹的激情與史詩(shī)般的品格,所彰顯的那份生命的力量,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關(guān)鍵詞:魯迅 珂勒惠支 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 版畫(huà) 功能性
一、魯迅與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起源及發(fā)展
1927年國(guó)民黨發(fā)動(dòng)“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打擊國(guó)民黨“左派”人士及共產(chǎn)黨,使中國(guó)大革命遭受了極大打擊。隨之而來(lái)的是日本于1931年發(fā)動(dòng)了“九·一八”事變,揭開(kāi)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東方戰(zhàn)場(chǎng)的序幕。錯(cuò)綜復(fù)雜且異常尖銳動(dòng)蕩的階級(jí)斗爭(zhēng)與民族斗爭(zhēng)的時(shí)代背景,孕育了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的興起與發(fā)展,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作為20世紀(jì)30年代的中國(guó)左翼文藝運(yùn)動(dòng)的一個(gè)組成部分,也因其“左”的傾向,給了敵人鎮(zhèn)壓的口實(shí),直接導(dǎo)致了其后所經(jīng)歷了沉重的打擊及殘酷的迫害。魯迅以革命的眼光分析道:木刻“是正合于現(xiàn)代中國(guó)的一種藝術(shù)”[1]。“當(dāng)革命時(shí),版畫(huà)之用最廣,極匆忙,頃刻能辦。”[2]魯迅認(rèn)為“木刻本身就是大眾的藝術(shù)”,30年代以前的中國(guó)木刻版畫(huà),其主要還是處于一種文化附屬狀態(tài)。主要為佛經(jīng)、佛畫(huà)、書(shū)籍、戲曲、小說(shuō)插圖,年畫(huà)等,偶有畫(huà)譜、箋譜,內(nèi)容多數(shù)通俗易懂。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的版畫(huà)主要以黑白版畫(huà)為主,相較于國(guó)畫(huà)、油畫(huà),其操作較為簡(jiǎn)便少耗費(fèi),復(fù)數(shù)性特點(diǎn)又可一版多印,利于流傳普及。在物質(zhì)嚴(yán)重匱乏的戰(zhàn)亂年代,魯迅選擇用木刻服務(wù)革命事業(yè)具有極大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礙于此前的中國(guó)“創(chuàng)作版畫(huà)”空白的局面,魯迅通過(guò)翻譯進(jìn)步藝術(shù)理論、編印畫(huà)集、復(fù)印畫(huà)冊(cè)、舉辦版畫(huà)展覽等方式,以供青年借鑒,參觀學(xué)習(xí)之。其先后翻譯了《近代美術(shù)史潮論》、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shù)論》、《文藝與批評(píng)》,普列漢諾夫的《藝術(shù)論》,日本廚川白村(Kuriyagawa Hakuson)的《出了象牙之塔》、《苦悶的象征》等;并編印出版畫(huà)冊(cè)及技法理論書(shū)籍有《近代木刻選集》、《新俄畫(huà)選》、《士敏土之圖》、《一個(gè)人的受難》、《引玉集》、《蘇聯(lián)版畫(huà)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huà)選集》、《死魂靈一百圖》、《木刻創(chuàng)作法》、《北平箋譜》等等。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木刻創(chuàng)作法》一書(shū),是我國(guó)第一本指導(dǎo)木刻創(chuàng)作的書(shū),在那個(gè)資訊有限的年代,具有火種般的意義。
除在上海多次成功舉辦版畫(huà)展覽外,更是于1931年8月于上海主辦“木刻講習(xí)會(huì)”,并邀請(qǐng)其友人內(nèi)山完造之弟內(nèi)山嘉吉講授木刻。此后我國(guó)版畫(huà)界將這一天作為中國(guó)開(kāi)始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的紀(jì)念日。這一系列的舉措,直接催生了一批進(jìn)步木刻社團(tuán):(1)1929年由杭州國(guó)立藝專(zhuān)進(jìn)步學(xué)生組織的“一八藝社”,1932年被國(guó)民黨當(dāng)局解散;(2)1931年由木刻講習(xí)會(huì)成員鐘步清和鄧啟凡發(fā)起組織的MK木刻研究會(huì);(3)同為1931年木刻講習(xí)會(huì)成員江豐、陳鐵耕、黃山定、倪煥之、鐘步清、苗勃然及一八藝社的胡一川、于海等發(fā)起的現(xiàn)代木刻研究會(huì);(4)1932年的春地美術(shù)研究所,由詩(shī)人艾青命名;(5)野風(fēng)畫(huà)會(huì);(6)上海木刻研究會(huì);(7)野穗木刻社;(8)無(wú)名木刻社等。這些木刻社團(tuán)主要以編印創(chuàng)作木刻作品及舉辦展覽來(lái)開(kāi)展革命活動(dòng),期間魯迅不僅參觀青年木刻家舉行的木刻展覽,更是通過(guò)書(shū)信等,鼓勵(lì)青年木刻家們從事版畫(huà)創(chuàng)作,并對(duì)其作品進(jìn)行剖析后給予指導(dǎo)性的意見(jiàn)。雖然這些木刻社團(tuán)歷時(shí)不長(zhǎng),但正是由于他們的辛勤探索,極大地推動(dòng)了中國(guó)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的發(fā)展。
二、凱綏·珂勒惠支作品在中國(guó)
魯迅積極引進(jìn)歐洲版畫(huà),特別是蘇聯(lián)的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格作品與德國(guó)的表現(xiàn)主義傾向的作品,這二者的選擇,是非常具有藝術(shù)戰(zhàn)略眼光的。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內(nèi)憂(yōu)外患,進(jìn)步木刻青年們渴望將手中的刻刀用于宣傳革命抗?fàn)幘瘢呋パa(bǔ)的關(guān)系,讓木刻青年在創(chuàng)作中,用表現(xiàn)主義的夸張、抒情等手法去表現(xiàn)客觀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使作品更具視覺(jué)沖擊力及情感上的震撼力。
魯迅有選擇性地引進(jìn)并推廣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尤以珂勒惠支為甚。并于1932年6月4日-5日,在上海瀛寰圖書(shū)公司舉辦“德國(guó)作家版畫(huà)展”,共展出作品約50幅。并在此次展覽對(duì)西方表現(xiàn)主義作了簡(jiǎn)要介紹:“例如亞爾啟本珂(Archipenko),珂珂式卡(O.Kokoschka),法寧該爾(L.Feininger),沛西斯坦因(M.Pechstein),都是只要知道一點(diǎn)現(xiàn)代藝術(shù)的人,都很熟識(shí)的人物。”[3]1933年10月14日-15日,在上海千愛(ài)里40號(hào)舉辦“德俄版畫(huà)展覽會(huì)”,共展出作品66幅。兩次展覽均有珂勒惠支的版畫(huà)作品。珂勒惠支是位悲情的母親,她的兒子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西線(xiàn)陣亡,因其與丈夫生活在貧民區(qū),了解普通人民的貧困境遇。因此她的作品主要反映普通人民的貧苦生活,如實(shí)地反映了生活在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德國(guó)底層人民的可悲生活。她的作品以尖銳的形式揭露了戰(zhàn)爭(zhēng)的殘酷,滿(mǎn)含悲傷與凄涼,以期喚醒民眾的斗爭(zhēng)精神。戰(zhàn)爭(zhēng)、犧牲、饑餓、痛苦、悲傷、婦女與兒童這些在珂勒惠支的版畫(huà)作品中是常出現(xiàn)的題材,恰恰也與當(dāng)時(shí)魯迅最為關(guān)切的中國(guó)社會(huì)問(wèn)題相契合。
1931年的9月,魯迅將珂勒惠支的版畫(huà)作品《犧牲》刊于《北斗》雜志上,用以表達(dá)對(duì)國(guó)民黨反動(dòng)派殺害革命戰(zhàn)士的深切悼念。在《凱綏·珂勒惠支版畫(huà)選集》序目中,魯迅更是指出珂勒惠支的作品是“她以深廣的慈母之愛(ài),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斗爭(zhēng);所取的題材大抵是困苦,饑餓,流離,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號(hào),掙扎,聯(lián)合和奮起。”[4]珂勒惠支的作品重視強(qiáng)烈的主觀感受,從感情及精神上吸引觀者的注目,流露出對(duì)生活在社會(huì)下層民眾的關(guān)懷,及人道主義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宣傳與教化的作用。而這些與當(dāng)時(shí)魯迅渴望將文藝用于革命斗爭(zhēng)的觀念是完全契合的。然而與珂勒惠支的作品在中國(guó)得到推崇相反的是,隨著1934年希特勒任德國(guó)元首,帶有社會(huì)主義反戰(zhàn)思想的珂勒惠支被取消普魯士學(xué)院院士的榮譽(yù),作品也被禁止參加展覽,直至1945年4月22日卒于德累斯頓。
三、凱綏·珂勒惠支對(duì)中國(guó)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的影響
魯迅一方面積極向木刻青年介紹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作品,供其觀摩習(xí)之。讓進(jìn)步木刻青年們“采用外國(guó)良規(guī),加以發(fā)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富是一條路。”[5]這時(shí)期作品帶有明顯表現(xiàn)主義傾向的木刻家有胡一川、李樺、劉侖、鄭野夫、賴(lài)少麒等。胡一川所作《到前線(xiàn)去》,作品黑白對(duì)比強(qiáng)烈,刀法粗獷有力,生動(dòng)地表現(xiàn)了“一·二八”事件后民眾的憤怒與反抗侵略的激情。又如李樺創(chuàng)作的《怒吼吧中國(guó)》,作品采用象征手法,刀法利落,完美地詮釋了中華民族受欺凌后,已然覺(jué)醒,決心反抗的精神力量。兩幅作品均帶有豪放的表現(xiàn)主義特征。另一方面他還主張“擇取中國(guó)的遺產(chǎn),融合新機(jī),使將來(lái)的作品別開(kāi)生面也是一條路。”[6]勸誡木刻青年要立足本土文化情境,鼓勵(lì)外出寫(xiě)生,打好造型基礎(chǔ),注意觀察生活,注重畫(huà)面內(nèi)容的真實(shí)性表達(dá),不以“怪”炫目,以提高木刻本身的藝術(shù)水平。同時(shí)他還提倡藝術(shù)是為大眾服務(wù)的。魯迅于1936年10月8日與青年木刻家陳煙橋、曹白、林夫、黃新波及吳渤座談時(shí)提出:“刻木刻最要緊的是素描基礎(chǔ)打得好!……藝術(shù)應(yīng)該真實(shí),作者故意把對(duì)象歪曲,是不應(yīng)該的。故對(duì)任何事物,必要觀察準(zhǔn)確,透徹,才好下筆;農(nóng)民是醇厚的,假若偏要把他們涂上滿(mǎn)面血污,那是矯揉造作,與事實(shí)不符。”
如李樺的《怒潮》系列組畫(huà),以強(qiáng)烈的黑白對(duì)比、細(xì)致的敘事性情節(jié)描繪、極富表現(xiàn)力的人物造型刻畫(huà),將生活在那個(gè)苦難時(shí)代的大眾的精神面貌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作品將表現(xiàn)主義的表現(xiàn)性與敘事性相結(jié)合,帶有濃厚的社會(huì)批判性,完美地詮釋了木刻的“中體西用”。總的來(lái)說(shuō),通過(guò)魯迅的大力倡導(dǎo),進(jìn)步木刻青年們汲取了凱綏·珂勒惠支作品的養(yǎng)分,并融合了本土社會(huì)的實(shí)情,打破了傳統(tǒng)木刻程式化的畫(huà)面構(gòu)架,將陰刻與陽(yáng)刻相結(jié)合,有組織地布局畫(huà)面黑白對(duì)比關(guān)系,創(chuàng)造了新的現(xiàn)代版畫(huà)的雛形,奠定了中國(guó)現(xiàn)代版畫(huà)的發(fā)展基礎(chǔ)。
結(jié) 語(yǔ)
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的木刻作品,徹底擺脫了中國(guó)繪畫(huà)史上傳統(tǒng)的山水花鳥(niǎo)等題材,轉(zhuǎn)而將普通大眾的生活百態(tài)作為藝術(shù)表現(xiàn)的對(duì)象。表現(xiàn)手法上,引進(jìn)外來(lái)木刻工具與表現(xiàn)技法,并融合應(yīng)用于自身創(chuàng)作,打破了傳統(tǒng)版畫(huà)以線(xiàn)塑造人物形象的程式化表現(xiàn)手法,代之以黑白對(duì)比強(qiáng)烈的視覺(jué)效果,以夸張、抒情等表現(xiàn)手法直面“赤裸”的現(xiàn)實(shí),強(qiáng)調(diào)作品本身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特別是作品流露出的那份對(duì)生活在戰(zhàn)亂年代生活困頓民眾的深切同情,及反壓迫反侵略的抗?fàn)幘瘢鼓究虜[脫了傳統(tǒng)的附屬狀態(tài)。其帶來(lái)的不僅是新的創(chuàng)作思想跟表現(xiàn)技法,更是一種全新的現(xiàn)代藝術(shù)觀,揭開(kāi)了中國(guó)現(xiàn)代版畫(huà)的序幕。因其所處的特殊時(shí)代,作品所帶有的社會(huì)主義抗?fàn)幩枷胧菢O為濃厚的,以致其作品的功能性體現(xiàn)大于藝術(shù)性表達(dá)。在技法和風(fēng)格上不難看出其深受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及蘇聯(lián)革命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影響,雖技藝提高尚有空間,但作品滿(mǎn)是純粹的激情與史詩(shī)般的品格,所彰顯的那份生命的力量,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注釋?zhuān)?/p>
[1]魯迅.木刻創(chuàng)作法·序.見(jiàn):白危編譯.木刻創(chuàng)作法.上海:上海書(shū)店出版社,1937
[2]魯迅.新俄畫(huà)選·小引.朝花社,1930
[3]引自:魯迅.集外集拾遺(補(bǔ)編).介紹德國(guó)作家版畫(huà)展.見(jiàn)《魯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322頁(yè)
[4]引自:[德]凱綏·珂勒惠支著,魯迅編.凱綏·珂勒惠支版畫(huà)選集.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1956:序目,8頁(yè)
[5][6]魯迅.木刻紀(jì)程·小引.見(jiàn):魯迅.為了忘卻的紀(jì)念.魯迅雜文3.北京線(xiàn)裝書(shū)局,2009::13頁(yè)
參考文獻(xiàn):
[1] 丁景唐,王觀泉.魯迅與凱綏·珂勒惠支[J].山東師范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78(06)
[2] 李允經(jīng).論魯迅對(duì)中國(guó)新興木刻運(yùn)動(dòng)的偉大貢獻(xiàn)[J].昆明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1983(03)
[3] 齊鳳閣.超越與裂變——20世紀(jì)中國(guó)版畫(huà)論評(píng)[M].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6
[4] 李允經(jīng).中國(guó)現(xiàn)代版畫(huà)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5] 王伯敏.中國(guó)版畫(huà)通史[M].石家莊:河北美術(shù)出版社,2002
作者簡(jiǎn)介:
楊佩,蘇州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